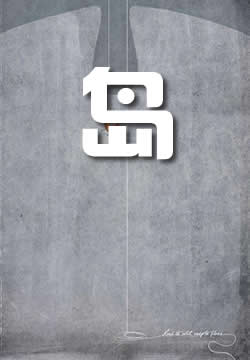(1917年)
自幼我就有个习惯,为了振作精神时不时地躲到别的世界里去。人家总是费心找我,过些时候就公布我失踪了,等到我重新出现时,听着对我本人和我失踪状况的所谓科学分析,那真是一桩乐事。我所做的只是合乎我本性的事,是将来大多数人都能做的事,而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却认为我表现的是一种魔鬼附身的现象,也有人认为那是种特异功能。
总之,我跑掉已经好一阵子了。因为战争延续了两三年,现时对我没有多少吸引力,于是我躲了起来,到别处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我按照习惯离开我们生活的层面,到其他层面做客去了。有一段时间我跑到遥远的过去,匆匆穿行于各个国家、各个时代,见到我们熟知的种种事,比如判人死刑、钉人十字架、来往做生意、世界的进步、世界的改善,等等,对这些我都不甚满意,于是回到宇宙里去待了一段日子。
当我回来时,时间已到了1920年,令我非常失望的是,各个民族仍然和以前一样,愚蠢而顽固地在战争中对垒着。除了几处边界移动,几个古老文化区域被精心破坏,地球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改变。
关于平等一事地球上进步很大。就我所知,至少欧洲各国看起来完全一样,连参战国和中立国之间的区别也消失了。自从在一万五千米至两万米高空上的无人驾驶气球可以在飞行中机械地向地面的平民百姓射击,靠国界保卫国土已成空想,不过人们仍然严守国界。这种空中的乱洒四射面积很大,所以只要不射击到自己的领土,发射气球的人都非常满意,他们也不管有多少炸弹掉到中立国甚或结盟国的国土上去。
事实上这是军事上惟一的进步,战争总算清楚地以这一点表明了它的意义。世界分成两大阵营,谁都想要消灭对方,因为双方都以解放被压迫者、消除暴力以及建立永久性的和平为己任。大家都反对不能持久的和平,如果不能够永远拥有和平,那就宁愿永远拥有战争。气球在高空之上毫无顾忌地对正义者与不义者撒炸药,这种行径完全符合战争的意义。不过,战争还像以前那样以重要但不充足的手段进行着。军队和技术人员那点儿想像力也还发明了少数一些摧毁性的武器,那位发明气球丢炸弹的老兄可说是最后一位了,因为自从有了这种武器,理论工作者、幻想家、诗人和爱梦想的人对战争越来越没兴趣。战争全由军队和技术人员来控制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进步。军队以惊人的毅力到处对垒,虽然因为物质缺乏,对军人的表彰只有奖状一张,却见不到哪儿的士气有多少减弱的现象。
我的房子被炸坏了一部分,不过在里面睡觉还是可以的。可是屋里又冷又不舒服,满地沙土,墙上都是潮湿的斑痕,我不愿久留,就出去散步了。
我在城里的几条巷子转来转去,这些地方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最主要是见不到任何店铺。街上死气沉沉。我没走多久,就有个帽子上钉着个铁皮号码的人走到我面前,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散步。他说,您有许可吗?我不懂他在说什么,大家争执了几句,不得要领,他就叫我跟他到最近的官府机构去。
我们来到一条街道,那儿的房子都挂着白色牌子,上面写着数字和机构名称。
有一面牌子写着“无工作的平民”,上面的号码是“2487b4”。我们就进入这栋房子。里面的办公室、等候室、走廊和一般的官方机构没有分别,有一股纸张、湿衣服和官僚的气味。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他们就把我带到72号房,在那儿审问我。
一个官员站在我面前打量着我。他很严厉地问:“您不会立正吗?”我说:“不会。”他问:“为什么不会?”我胆怯地回答说:“因为我没学过。”
“您因没有许可擅自散步而被捕,您承认吗?”
“是的,”我说,“确是这样。我不清楚有关规定。您知道,我病了很长时间——”
他摇摇手不让我说话。“您得受处分,现在罚您三天走路时不能穿鞋。把鞋子脱下!”
我脱下鞋子。
“了不得!”那位官员惊叫起来,“了不得,您居然穿着皮鞋!这鞋从哪儿来的?您不是疯了吧?”
“精神上我大概不太健康,这我自己无法判断。鞋子是我以前买的。”
“嗯,您难道不知道凡是皮做的东西平民是严格禁止使用的?——这鞋子被没收了,您不能带走。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吧!”
天啊,我没身份证。
“一年来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那位官员叹了一口气,叫进一个警察。“把这人带到194处8号房去!”
我光着脚被他赶着穿过几条街,进入另一处机关的房子,我们穿过几条走廊,呼吸着纸张和无望的气味,然后我被推进一间办公室,由另一个官员来审问。这是位穿着制服的官员。
“您没有身份证就上街。罚款两千古尔登。我这就给您开收据。”
“请原谅,”我畏缩地说,“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您能不能把我关上几天而不罚款?”
他大笑起来。
“关起来?您真好玩,您是怎么想的?您以为我们有兴趣连您的饭都管? ——不,亲爱的,如果您不能付这点钱,那么您就逃不过最严厉的处分。我得暂时没收您的生存证!请把您的生存证拿出来!”
我没有。
现在这位官员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叫来两位同事,和他们小声说着什么,好几次指向我,大家用恐惧和十分惊奇的目光看着我。然后他让人先把我带到拘留室,他们自己还得商量如何处置我。
拘留室里头有好些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门前有个军人看守。我注意到,除了没有鞋子,我的衣着远比这里所有的人都好。他们让我坐下,有点儿敬重的意思。有个个儿矮小样子畏缩的人立刻挤到我身旁,他小心翼翼弯着腰在我耳边小声说:“您听着!我有桩好生意跟您做。我家里有棵甜菜!一个完整无可挑剔的甜菜!差不多有三公斤重。您可以要。您给多少钱?”
他把耳朵贴近我嘴边,我小声说:“您自己给个价吧!您要多少钱?”
他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那就给一百一十五古尔登吧!”
我摇摇头就陷入沉思之中。
我看出,我离开太久了,已经无法重新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如果能得到鞋子或袜子,出多少钱我也愿意,因为刚才光脚在湿漉漉的街上走,脚已经冷得不行了。可是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是穿着鞋子的。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把我带到285处19f号房去。警察这一次跟着我进房间。他站到我和官员之间。这位官员看起来职位很高。
“您使自己陷入相当糟糕的境地,”他开始说,“您没有生存许可证就到了这个城市。您大概知道,这会被处以最严厉的处罚。”
我微微弯了一下腰。
“对不起,”我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完全明白自己应付不了这情况,也明白我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您难道不能判我死刑?如果您这么做,我将非常感激!”
这位高官的目光与我相遇,非常温和。
“我理解,”他温和地说,“可是如果这样,最后每个人都可能这样要求的!无论如何,事先您还得买张死亡卡。您有这钱吗?一张卡四千古尔登。”
“我没有这么多钱,不过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很希望这样就能换取到死亡。”
他微笑了一下,样子很奇怪。
“我很乐意相信,您并非第一个这么要求的人。可是,要死不是那么容易的。您属于国家,亲爱的,您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国家的。——我刚看到,您登记的名字是埃米尔·辛克莱。您或许就是作家辛克莱?”
“是的,我就是。”
“啊,我太高兴了。希望能为您效劳。警察,您可以走了。”
警察走了,官员伸出手同我握手。“您的书我读了,非常感兴趣,”他很亲切地说,“我愿意尽力帮助您。——不过,请告诉我,您怎会落到这地步的?”
“是呀,我跑掉了一阵子。我逃到宇宙中去了,走了大概有两三年吧,说实在的,我还半信半疑地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过,您能帮我弄张死亡卡吗?如果您能够帮这个忙,我将感激不尽。”
“或许能够办得成。不过您得先有张生存许可证。没有生存许可证什么事都办不成。我给您写张条子,您到127处去,有我做保证人,他们会给您开一张临时证明的,不过,有效期只有两天。”
“哦,那已经足够了!”
“就这样吧!办完了请您再回到我这儿来。”
我和他握了握手。
“还有件事!”我轻声地说,“我可不可以再提个问题?您可以想像,我对目前的情况是多么不了解。”
“请说,请说。”
“嗯,——我主要想知道,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人们怎么生活得下去。大家忍受得了吗?”
“噢,没问题。您作为平民,又没有证件,情况自然特别糟。现在老百姓已经很少了,大家不是军人就是官员。因此大多数人过得都还可以,有不少人还生活得很好呢。至于物资的匮乏大家也都逐渐习惯了。当土豆逐渐缺乏,人们得吃柴粥时——现在的柴粥加了一点柏油,味道好多了——每个人都以为过不下去了。而日子还是照样在过。每样事都如此。”
“我懂,”我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有一事我没法完全弄明白。请告诉我,全世界费这么大力气到底是为了什么?各种匮乏、各种规定、让上千种机构和官员——这是用来保护什么?维持什么呢?”
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
“这难道是个问题!”他摇着头喊了起来,“您知道,现在在打仗,全世界都在打仗!我们维持的就是这个,为它我们订立法律,我们作出牺牲。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做出这些努力和工作,战场上的军队一星期也维持不下去——那可是不能忍受的事!”
“是的,”我慢慢地说,“这可说也是一种想法,也就是说战争是大好事,应当作出这么多牺牲来维持住它!不过——请允许我提个稀罕的问题——您为什么如此高估战争呢?值得为它做这么多吗?战争到底是不是好事呢?”
带着可怜我的神情,他耸了耸肩膀,他看出我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
“亲爱的辛克莱先生,”他说,“您变得一点都不谙世事了。不过,您只要走上一条街,和一个人说说话,稍微用心想一想,然后问问自己:我们还拥有什么?我们的生活由什么构成的?那么您一定会说:战争是我们仍然拥有的惟一的东西!享乐、个人的产业、名利、爱情、精神劳动等等,什么都没有了。惟有依靠战争,世界上才能够保有像秩序、法律、思想、精神这样的东西。——您难道就真的不懂?”
是的,现在我明白了,我非常感谢这位先生。
然后我就走了,机械地把那封介绍信放进口袋里。我不打算用这信了,我一点也不想再麻烦任何一个机构了。在我重又被人发现、被人审问之前,我让星辰的祝福进入我心,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让我的身体消失在树荫下,继续我先前的漫游,再也不想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