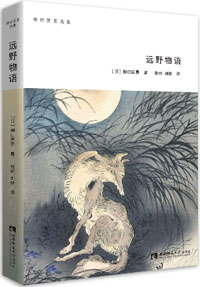引言
旅行家对于日本所记录的最初印象,大半都是快乐的印象。果然,在日本不能感情用事而作辨诉的天性中,必定也有些缺少的事情,或者极其粗暴的事情。那辨作的本身,却就是解决一个问题的秘钥;那个问题则便是一个民族及其文明的性格。
我自己对于日本的最初印象,——在春光明媚中所看见的日本,——不消说也是和一般人的经验大概相同的。我特别记得的是目睹之后的惊奇与喜乐。惊奇与喜乐是永不会消灭的:就是现在,我已经在此作客十四年了,一遇着什么机会,他们还将常要重新的活动起来。可是这些感情的理由是难于捉摸的,——或者至少是难于猜测的;因为我还不能说我已很熟知日本。……好久以前我那最相知最亲爱的日本朋友,在他死前不久之时告诉我:“再过四五年,当你觉得你完全不能了解日本人的时候,那末你将开始知道他们一些了。”等到我那位朋友的预言实现之后,——等到发觉我完全不能了解日本人之后,——我觉得我格外有资格来尝试写这篇论文了。
最初令人觉着的,就是日本事物表面上的奇异,会(至少在某种人的心目中)发生一种描摹不出的古怪的震惊,——一种只有看到了完全陌生的事物,才会领略得到的荒谬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是在古怪的小街道上走,遍是古怪的小百姓,穿着式样非常别致的衣服和木屐;你看了竟辨不出男女来。房屋的建筑和布置都是和你所有的经验不熟的;你在店中看到了陈列着的许多东西,你竟一些也猜想不出它们的用途和意义来,你定要发呆。来源想像不出的食料;形式和谜语一般的器具;什么神秘信仰的莫名其妙的记号;牵涉着神仙或鬼怪故事的奇异面具和玩物:还有垂着大耳,发着笑容,许多古怪的佛像,——所有这些东西,你信步所之的走着,你便可以见识到;虽然你也必须注意电杆和打字机,电灯和缝衣机,不论何处,在字号和悬物上面,在走过的人的背脊上面,你将注意到奇妙的中国字;这些文字的离奇如巫术,却成了景物的适宜点缀品。
绸缎店
日本人的和服一般是用绸缎做成的,特别是女性的和服,式样和花式更是精美,一件和服造价不低。图中的母女俩正在细细挑选布料。
和这个奇幻的世界相处得稍久些,你最初见面时所引起的奇异感觉,是决不会减少什么的。你还是要注意到他们体力动作的离奇,——他们的工作,竟是用西方相反的方法做成的。工具的形状都很古怪,施用的方法也很特别:铁匠蹲在铁砧边,执了铁锥敲打着,西方的铁匠,如果没有长时期的练习,是不会这样工作的;木匠施用他那奇形的刨子和锯子,则拉而不推。时常以左作右,以右作左;开锁和关锁的方向,总必向着我们以为是错误的那一边旋转着。洛威尔君(mr.percival lowell)仔细的注意过,日本人的说话,写字,读书,方向都是向后的,——这些“不过是他们所有相反之处的起码事情”。对于向后写字的习惯,是有沿革清楚的理由的;极好的日本书法,能将日本画家为什么只用推笔而不用拖笔的所以然,很明白的解释出来。不过为什么日本女子只将针眼套线头,而不将线头穿针眼呢?或者在数百件相反的动作者中,这件最特别的事情,是受了日本剑术的影响。剑士用两手攻击敌人的时候,不是将剑刃抽向自己来,而是挫向前面去的。他用它的用意,和别的亚洲人一样,的确不是劈,而是锉;不过有了推的动作,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抽的动作以为攻击。……这些和另外许多陌生的动作,不能不使人想,他们在体力上,和我们没有什么大关系,他们简直是另外一个行星上的人类,——想他们在解剖学上和我们有些不同。然而这些不同之处,并不怎样看得出;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反之处,大概不是为了他们的经验完全和我们的无关,却是他们的经验,在进化方面,要比我们的幼稚些。
梳妆盒
日本的漆器也相当精致,豪门新娘所用的梳妆盒也是一件艺术品。
可是他们的经验并不是可以小看的。它的扩大非但能惊人,而且还能悦人。工艺上的仔细琢磨,意想的轻灵美妙,用最少物质,而得到最好结果的能力,用最简工具而达到机械目的的成就,以错综为美的理会,不论何物的美式佳趣,调铅敷粉,颜色和谐的感觉,——所有这种种事情必能立刻使你相信,我们西方还有许多东西,不但在美术的和趣味的这些事上,并且在经济的和利用的这些事上,必须要向这个古文明学习一下。你看到了那些可惊的磁器,那些可羡的刺绣,那些漆器和象牙器和铜器的奇妙,使你在陌生的道途上发生想像的,决不是野蛮的幻想。决不是:这些都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这文明,在它自己的限度中,已达到非常精美的地步,只有一个美术家才能判断它的制作,——这文明,谁要说它是不完善的,谁只好将三千年前的希腊文明也当作不完善。
台风过后的神户港
台风过后,港口到处都是漂浮着的木头,工人正在忙着清理现场。
不过这世界里面的奇异,——心理学上的奇异,——比了看得见的和表面上的,还要十分可惊呢。等你知道没有一个西方的成人能够完全学会日本话之后,你就可以猜疑到种种奇异之事了。东方与西方,人类天性的根本部分——人类天性情感上的根据——是很相同的:日本孩子和欧洲孩子,在心智上的差别大都潜伏着看不出来。可是在他们长大时,差别也随着快快的发展着,扩张着,等到他们成了人,那差别就数说不尽了。日本人心智组织的全部开放,和西方人心理的发展完全不同:思想的表现是有规则的,而情绪的表现则流入了迷幻莫测的道途上。这些人民的观念并不是我们的观念;他们的情感也不是我们的情感;他们的伦理生活,在我们看来,只是还没有思索过或早已忘却了的。思想和情绪所结合成的宗教。将他们平常的辞句中不论那一句翻成西方言语,就毫无意义;而将最简单的英文句法用入了日本文字中,则没有读过欧洲文字的人,便难于懂得。即使你能将一部日本字典中的字都学会,你仍旧一些也不能懂得他们的说话,除非你也已经学会和日本人一般的思想方法,——那就是说,向后想,倒过来想,翻过来想,向亚利安(aryan)人种习惯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想。学会欧洲言语的经验,所能帮助你学会日本言语的地方,正如它能帮助你学会火星居民的言语一样。谁要想像一个日本人那样的应用日本话,就除非重新投胎过,除非彻头彻尾,将他的心思完全改造过。只有这样是可能的,就是要一个父母是欧洲人,自己出生在日本,从小就学会日本话的人,长大来才会保留牢,那种使他的心智关系,得以和任何日本环境的关系互相适合的天然知识。确实有一个名叫勃拉克(black)的英国人,是出生在日本的;他便能精通两方面的语言,他以说故事为业,赚得了许多钱。不过这是例外的事情。……至于文学的文字,要想能够精通,那末并不是认识几个中国字便可算数的。我们很可以说,不论那一个西方人,总不能将他面前的文学书翻译出来——当然本地的学者能作这样的工作的,也是为数甚少;——虽然有若干欧洲人,在这种翻译事业上可以值得我们的崇敬,可是他们的工作,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是决不能出以问世的。
正像日本表面上的奇异已证明是充满美丽的一样,它里面的奇异却也自有它的魔力,——是在民众普通生活中反映出的伦理的魔力。那种生活的动人之处,照一个平常人看来,因并不包含什么心理学上的变化,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来观察:只要有洛威尔君那样科学的心思,便立刻可以理会到这问题的究竟。天资稍差的外国人,而有自然的同情心的,只会觉得高兴与惶惑,对于那些动心的社会状况,就要想用他自己,在世界另一面的快乐生活的经验,来加以解释。我们可以设想他,居然有幸运,可以在内地旧式的镇市中,住上六七个月或者一年。从他的旅居开始,他一定便能感觉到他四周的和爱与喜乐。在他们众人的往来间,和他们众人与他自己的往来间,他将要找得不断的安适,熟习和善性,这些情形,除了此地以外,除非是在特别范围的友谊中,才会遇得到。每一个人都用快乐的面孔和高兴的言语,向每一个人问候着;面上时常带着微笑;每天最平凡的生活,为了这样的客气,立刻就变得诚朴而纯洁;觉得这竟是直接从心底里流露出来,而不是任何教训所能造成的。在任何状态之下,表面上的高兴总不会停止:不管发生了什么困难,——暴风或火灾,大水或地震,——笑容和问候声,柔和的询问和使人快乐的志愿,都不断的在使事实美丽起来。在这样的光明中,宗教也不会带什么暗影来:他们在诸佛和诸神之前祈祷时,总是微笑着;庙中的空地,便是儿童的游戏场;公众的大庙宇——是宴乐之场而非庄严之地——里面,设立着跳舞的平台。家庭方面,似乎不论那一处都带着温柔;决没有看得见的吵闹,决没有大声的粗暴,决没有眼泪与责骂。残暴之事,即使是对于畜类,也是不会有的:上街去的农人,时常傍着他们的牛或马走着,为他们这些不开口的伴侣分任重担,既不用鞭策,也不用刺击。推车或挽车的人,遇到了一条懒狗或者一头笨鸡,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地位,也总是绕道避开,而不直撞上去。……你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中,住得很久,决不会有什么事情使你的经验发生不快。
我所说的这些情形,当然现在正在消灭着;不过在最冷僻的地方,却还可以找得出来。我曾经住过几处地方,在那里几百年来从没有发生过窃案,——在那里明治时代所新建的牢狱,一直空着无用处,——在那里百姓将他们的大门,夜间和日间一般的开着。这些事实,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很习惯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也许要说他们对你这位外国人的客气,不过是官厅命令的结果;但是他们自己相互的和好,你将何以解释呢?当你觉得他们没有暴厉,没有粗卤,没有奸诈,没有犯法,而知道他们这种社会状况数百年来如一日的时候,你就免不掉要相信,你已经进入一个在道德上较高的人类住着的领土了。所有这些彬彬有礼,坦白诚实,言动和爱可亲,你当然会明白,乃是由完全的善心所指使出来的行为。至于使你满意的简朴,也决不是野蛮的简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受过教育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怎样写得好,说得好,怎样作诗,怎样为人客气;不论何处都是干净而趣味盎然,室内也都是光明而纯洁;每天热浴的习惯,更是普遍。每一种往来都有博爱心统治着,每一种动作都有本份指使着,每一种事物都有艺术调度着,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中,你如何会不着迷呢?你不能不被这些情形所鼓舞而高兴,或者也不能不当你听见他们被人斥为“异教徒”时,而勃然大怒起来。按着你自己里面博爱心的程度,这些良善的子民,就能毫不费力的使你快乐。对于这个环境所有的感觉,就只是恬静的幸福:这很像一个梦的感觉,在这个梦里,他们给我们的问候,恰正是我们所喜欢的问候,和我们说的话,恰正是我们所喜欢听的话,为我们作的事,恰正是我们所喜欢的事,——他们在完全安适的空间中,静默的移动着,在蒸汽一般的光明中沐浴着。是的——这些神仙中人所能给你如睡眠一般的温柔福气,决不是小小的时间。不论何时,只要你和他们相处得长久些,你的知足心就会和那梦境的幸福,融洽无间。你将永不忘却这个梦,——永不;可它到后来将要升起来,好像春天的烟雾,在灿烂的上午,笼成了非常可爱的日本景色。你一定是快乐的,因为你已完全进入了仙境,——进入了一个不是,而且永不能是你自己的世界。你已经脱离了你自己的世纪,——经过了无穷的已经没有的时间,——进入了一个已为人所忘却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已经消灭的年光,——回到了和伊及或尼尼微(nineveh)差不多邃古的国家。那就是事物上美丽与奇异的秘密,——给人震惊的秘密,——他们和他们的事物,所有小巧玲珑,富有魔力的秘密。幸运的凡夫!时间的潮流已为你倒流过来了!不过你要记得,凡此种种,都是妖术,——你已经落在死人的迷幻中,——所有的光明和颜色和声音,最后都将褪谢到空洞和寂寞之中去。
日本女子沐浴
日本人每天都有洗热水澡的习惯,女性一般是几家集在一起浇水轮流洗。
至少,我们中总有若干人,时常要想在希腊文化的美丽世界中,住上几个月。这种心愿,只为了和希腊艺术与思想的动人之处,初有了接触,在能够想象这古文明的真情况之前,便果然的来了。不过倘然这个心愿是能够实现的,我们却又要觉得我们自己和那些情况不适合了,——并不是全为了和环境熟习的困难,乃是为了要和这三千年以前的人民有一样的感觉,那就格外的为难。虽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已有了不少的希腊研究,我们还是不能了解希腊古生活的许多事情;例如厄狄帕斯(edipus)的大悲剧中,所有的情感和情绪,现代人的心思是不能确实的感觉得到的。现在我们对于希腊文明的知识,的确要比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宗进步得多。在法国革命的时代,曾有人想,在法国恢复希腊共和国的种种事情,并且照着斯巴达制度来教育儿童,都是可能的。现在我们都已知道了,在罗马人征服之前,古代许多城市中,都有专制政体统治着,由现代文明发展出来的人心,到底是不能在它们里面找得到什么幸福的。倘然古代希腊生活果然能复活的,我们也决不能和它相处,——也决不能成为它的一部分,——除非我们能够改变了我们心理的同意性。不过为了那看得见它而发生的愉快,——或者为了那在哥林多(corinth)参观一个祭礼,或参观全希腊人游戏运动,而发生的喜乐,我们还有多少不赞成呢?……
可是,能够看见希腊已死文明的复兴,——能够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克洛托那(crotona)城里闲步一会,——能够在提奥克立塔(theocritus)的叙拉古(syracuse)地方漫游几时,——比了能够确实研究日本生活的机会,并不可以算为什么特权。的确的,从进化的观点看来,这不能算是一个特权,——因为日本现在所给予我们的种种活景,比了那艺术和文学为我们所熟习的任何希腊时代,都要古远些,在心理学上也格外要和我们不同些。
一个没有我们那样发展,而在理智上和我们绝对不同的文明,在不论何种情形中,我们总不能就当它是卑劣的,读者大概总能懂得这个道理,而不用特别提起罢。达到顶点的希腊文明,是代表着一种早期的社会进化的;可是从它里面发展出来的艺术,仍旧在将至高无上的美的理想,供给我们。所以现在这个更古老的日本老文明,也是保守着一种美的与道德的文化总数,值得我们的惊奇与称美。只有浅薄的心思——极浅薄的心思——才会将这种文化的最佳处,当作卑劣的。须知日本文明是很特别的,或者竟不是西方所能望其项背的,因为它在它那简单的本土基础之上,铺上了许多层外国文化的景色,造成了一种极尽错综变化的奇象。这种外国文化中,大部分是中国的,对于这些研究的真相,只有间接的关系。特殊而又可惊的事实,乃是它虽然有这许多涂抹在它的上面,而民族的和他们社会的原来性格,却仍旧是能令人认得出来的。日本的奇妙,并不在乎伊所穿着的许多借贷衣服中,——正像古代的公主,要穿上十二件颜色和性质都是不同的衣服,一件一件的套着,在颈项间,衣袖边,裙边,将五光十色的衣缘显示出来;——不错的,真正的奇妙,乃是穿衣服者。因为衣服的趣味,在形式和颜色的美丽中,比了在可以作为观念的用意中,要少得许多,——可以作为观念的用意,是代表着爱憎的心思的。至于日本古文明的最高趣味,则藏在它所表现的民族性格中,——那性格,经过了明治时代的种种变更,还是依然无恙着。
《源氏物语》插图
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由女作家紫式部于十一世纪初创作。
“提示”这个动词,或者要比“表现”好些,因为这种民族性格是只可以预先知道,而不可以加以承认的。我们对于它的理会,也许得了种族由来的一定知识,可以有一些帮助;可是这样的知识,我们现在还是得不到。人种学家都说,日本民族是由许多民族的混合而形成的,而主要的份子便是蒙古利亚种;可是这种主要份子的式样,却又有极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痩长而带些女性的;另一种则是肥短而强有力的。有人知道,中国份子和高丽份子,在若干区域中,也是有的;一大部分虾夷血统的混入,也是免不了的事实。究竟有没有马来(malay)或波利尼西亚(polynesia)的份子在里面,现在也还不能确定。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放胆确定的,乃是——这个民族,也和其他良好民族一样,是一个混合的民族;原来联合拢来组成它的各民族,已经搀和在一起,在长久的社会教训之下,发展成一个性格一致的式样了。这个性格,虽然在它若干的状态中,可以立刻的认识出来,却给了我们许多极其难以解释的哑谜。
可是,要格外的了解它,已经成为一件要事了。日本已经进入了竞争的奋斗中;任何民族在那斗争中的价值,有赖于性格,正和有赖于武力一般。我们可以知道若干日本性格,倘使我们能够确定了那造成它的种种情形的性质,——民族道德经验的一般重大事实。我们应该在国民许多信仰的历史中,和由宗教而来,为宗教所发展,许多社会创制的历史中,找得这些事实的表现或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