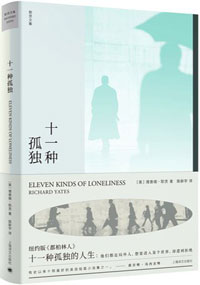英国是幽默之乡。她尤其推崇个人权利,且经常把这种个人权利推到与公共秩序相提并论的极限。
我担心英国人生性好斗、咄咄逼人,与他国人很难和谐共处。要知世界太小,一山难容二虎。
英国人拥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使得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创大业;同时,他们又拥有一种小虚荣,每个人总喜欢在别人面前显露两手。
英国是幽默之乡[1]。她尤其推崇个人权利,且经常把这种个人权利推到与公共秩序相提并论的极限。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以至于成了这个种族的一种技艺,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比方在一块农民拒绝变卖的土地上,即便国王也休想涉足。哪怕立遗嘱之人要把其财产留给一只狗或一座破房子,政府也不得干涉他的这种荒谬之举。每个英国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有时可以把这种方式发挥到极致。并且他的同胞会对他施以顽固的同情,这几乎成了规律法规、法官和骑兵卫队用来支持克伦普先生的狂思妄想的一种工具。无论多么荒唐怪诞的念头,英国人总会千方百计地借助金钱或法律手段使其名留千古。英国公民无所不能,丝毫不逊于罗马公民。安乐乡先生对此了如指掌。那些财大气粗之人所谓的自由,无非就是能让他们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作恶多端也是为了感受那份自由,还铁了心要把它坚持到底。
英国的国土很小,这使得国人容易团结一致,对国家充满挚爱。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权力和表现满怀信心,而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他们讨厌外国人。曾在英国久居的斯维登堡注意到:“英国人都很相似,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跟本国人结交密友,却很少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们看待外国人,就像从宫殿的顶层用望远镜遥望城外居住或游荡的人一样。”早在1500年,一位威尼斯旅游者曾在《英国的关系》书中写道:“英国人非常爱自己和他们拥有的每件东西,他们认为除了自己,没有别人,除了英国,没有别的世界。每当看到一位英俊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貌似英国人,并为他不是英国人而感到惋惜;当他们与一位外国人分享一顿美味佳肴时,他们会问:在其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东西。”当他对某种东西表示赞同时,他就会脱口而出“太像英国的了!”或当他要对你表示恭维时,就会说:“我还以为你是个英国人呢。”如进行天性对比,法国就是一块黑板,英国的特性就是用粉笔在上面描绘自己的特色。在提及法国时,英国人脸上这种傲慢的神情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我猜想在美洲、欧洲或亚洲具有英国血统的人都在窃喜自己不是法国人。据说,柯勒律治先生在一次公众演讲结束时,在众人面前感激上帝,因为他成功地自始至终没有使用一个法语单词。英国人的自视甚高,致使他们在上流社会与陌生人谈话时,那些怠慢或贬低自己的日常用语,都被他们曲解为这是对英国优点所展示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敬意;当纽约人或宾夕法尼亚人谦虚诚恳地感叹一个新国家的圆木小屋或野蛮未开发等缺陷时,立即会招来旁人的众多同情,这使他们惊诧不已,因为他们坚持认定英国之外的整个世界就是一堆废墟。
英国的殖民版图——日不落帝国
英国人自视甚高,有时甚至狂妄自大,但他们确实曾经以一个小小岛国的力量征服了世界,成为显赫一时的“日不落帝国”。色块部分为1871年极盛时“日不落帝国”的疆域,手伸五大洲。大英帝国的实质是英国本土、一些大片殖民地和众多沿海的殖民点的集合。
英国人的这种局限同样妨碍其外交政策。他们牢牢地守护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和行为习惯,祈求上帝保佑!硬生生地把本国的规章、条款插入印度、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国的喉咙,不仅如此,而且还把“沃坪”(wapping)[2]地方的税收强加给维也纳国会,用沉重的税收蹂躏着其他所有民族。卡塔姆勋爵主张自由,没有代表就不要交税,——因为那是英国的法律。可是在美利坚他们连一个鞋钉也不敢做,只能在英国购买钉子——这也是英国的法律;美国独立导致英国的商业重造,这一事实使所有人震惊不小。
简言之,我担心英国人生性好斗、咄咄逼人,与他国人很难和谐共处。要知世界太小,一山难容二虎。
除了这种民族性外,还有一点不能视而不见,那就是这个岛国的人们每日膜拜古老的挪威布拉吉神(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中,布拉吉神以他的能言善辩和气宇轩昂而著称)。英国人拥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使得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创大业;同时,他们又拥有一种小虚荣,每个人总喜欢在别人面前显露两手。因此,聚会时,他们人人都自命清高,对别人不屑一顾,毫不掩饰自己的身段、容貌、衣装、社会关系乃至出生地的任何一种缺陷,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每个特点都值得向你推荐。即便他们当中或有人秃顶,或有人长着一头红发或一头青发,或有人是罗圈腿,或有人疤痕累累,或有人大腹便便,或声音刺耳难听,而他总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这里面必潜藏着时髦之处,所以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恰到好处。
然而上帝自有安排。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这一点点过分的自恋正是他们的力量源泉和历史机密。正因为此,每一个人敢于展示真实自我,敢于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蔑视躲躲闪闪、缩头缩尾的猥琐习气,鼓励坦率、英勇和刚毅的作风。因此,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表现最佳,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一个人的缺点对其本人与对其他人都是同等重要。如果他轻视这些缺点,别人同样也会轻视它们。正因如此,我们从中找到一种简便的性格测试方法,因为一个脆弱的人很容易被烦恼击毁,而坚韧的人不会。我记得在西部某个城市,有一位精明的政客曾告诉过我,他知道有好几个政治家的成功源自其所谓的缺点。另外,伊利诺斯州的前州长曾告诉过我:“如果一个人知道些什么,他会坐在角落里缄口不言;相反,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会像一只无知的孔雀,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到处去碰运气。”
当然,有时“吹牛”也有好处,它会使你不知不觉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3]。千方百计地迎合他,让他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然后促使他坚持到底。然而教养使得这些见多识广的英国人逃脱了这种可笑至极的自娱自满,相反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路易十六的神态和气质在这位君王身上表现得恰到好处,假若换作另一个人就会变得荒唐可笑。英国姓名的威望证实了这种特定自信的含义,这在法国人或比利时人的姓名中是没有的。不论怎样,在英国特性这方面,英国人持有一种十分自由的怪异论调。
英国人的家居社交
英国人有些自命清高和“吹牛”的习气,在家庭社交中总会有人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
一位英国女士在莱茵河上听到一位德国人把她们一行人称作外国人时,惊呼道:“不对,我们不是外国人,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在伦敦,你每天都可以听到法国人和英国人争吵的故事。他们双方都不愿决斗,但他们的同伴唆使他们去决斗,最后争吵双方达成协定:在黑暗中用手枪进行单挑,把蜡烛熄灭了,那英国人为了确保不错伤他人,便点燃炉火,然后让那个法国人趴下。英国人对外国人没有好奇心,即使别人乐意自愿提供任何信息,他们只是“哦,哦”来敷衍了事。致使别人认为:尽管他愿提供任何帮助,英国人也会死于无知。的确,英国人的这种狂妄自负是漫无边际的,尽管他们当中有些聪明之人也在力求谦虚一些。
在英国,各个阶层都有这种“吹牛”的习惯。从《泰晤士报》的编辑到政客和诗人,从华兹华斯、卡莱尔、穆勒、西德尼·史密斯到伊顿公学的学生都是如此。在最为严肃庄重的政治经济学中、或在哲学文论中、或在科学书籍中,这种牢固国民性的坦诚抒发真令你瞠目结舌。在一本关于谷物的小册子里,一位非常和蔼又多才多艺的先生写道:“根据贝克莱主教的观点,即便英国已被万仞高的铜墙所包围,她仍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地方,这正如她无论在物质上或自由上、在美德上或在科学上,都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英国人厌恶美国的社会结构,但他们在贸易、工业、公共教育和人民宪章运动方面却尽可能向美国学习[4]。美国是经济学家的天堂,是坚持引用毁灭原则的大好特例。而一旦直接提及美国人时,这个岛上的居民就会忘记他们的哲学,只记住那些可笑的奇闻轶事。
但是,像所有的狭隘主义者一样,这种幼稚的爱国主义也要付出代价。英国人对待自己的殖民地毫不心软,他们用手腕和强力来统治,公正有余,仁慈不足,一旦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是不会博得他所依靠的人的好感的。
一个国家、一个省或一个城镇如果缺乏自己宏伟的特色,随意挖掘一点粗糙的地方特色也是有利无弊的。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附属的次要的特色当成宝贝。居民个性往往胜过民族特性。在形而上学的世界里,没有一堵能把希腊、英国、西班牙的科学隔离开来的墙。伊索、蒙田、塞万提斯和萨迪都是世界之子,闻名于世的人物。他们在饭桌上或在大学里挥动着自己的旗帜,就是把消防队里无聊的喧闹引入文雅的礼貌圈来。大自然和命运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荒唐之举。当我们趾高气扬行走时,大自然会绊我们一跤;关于民族自豪感,历史上有着不胜枚举的事例。
卡帕多西亚的乔治,出生在西里西亚的埃皮法尼亚,他是一个低贱的寄生虫。当他搞到一份给部队提供熏肉的赚钱合同时,这个无赖和叛徒居然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借此发了一笔横财。不仅如此,他积攒了一些钱,信奉了阿里乌教,收藏了一些典籍,并被这一小宗派推到了亚历山大的主教之位。公元361年,尤里安来了之后,乔治被判入狱,还有一伙暴徒劫狱未果,最后乔治被处以极刑,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可笑的是,这十足的无赖居然很快变成了英国的圣徒乔治——骑士的保护神、胜利和文明的象征以及现代社会最优秀民族的骄傲。
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崇尚直言不讳的英国人竟然为一个骗子歌功颂德。无独有偶,美洲新世界的运气也同样不佳——广袤的美国也被冠以骗子之名。塞维利亚的一个泡菜贩子亚美利戈·韦斯普奇于1499年给奥赫达当副官,他的最高海军军衔是在一个从未出过海的探险队中担任帆缆军士长,可他却努力做到了在这个谎言充斥的世界里替代哥伦布,用他那虚伪的名字命名了半个地球。这样做,我们谁也不能指责他。我们都缺乏创业者,那虚假的泡菜贩子不过是虚假的咸肉贩子的后裔。[5]
* * *
[1] 在伊丽莎白时代“幽默家”的意义就是感受幽默与奇想。在英格兰旅行时所写的记事中,爱默生先生从卡莱尔博士的《自传》中做了如下的引用:“英格兰的幽默家比任何国家都多,因为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享受自由,生活富足,而我认为自由和财富就是幽默家诞生的温床。”
[2] 沃坪(wapping),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地区,过去通常在这里绞死海盗。——译者注
[3] 爱默生在1848年记事本中记录了下面一段话:“在这一点上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人们直话直说。只要千方百计地取悦他们,不要老是打量他的外表,他会毫无城府地告诉你他应该去做什么,把他的话全部套出来,缠住他不放,死死地缠住这个法国人。他是宇宙的解放者,他是人类文明中最文明的人,身处黑暗深渊中的各国人民,看到法国就看到了希望,而暴君们看到法国就看到了绝望。这是最优秀的人类!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呼唤。这就是法国的使命。法国绝不会像波兰、匈牙利、土耳其那样让任何人和任何国家受苦,更不会干扰本国的媒体或人们的言论自由。我要记下这些话,请你白纸黑字签名作证吧。你一定不会犹豫的!”
“嗯,可这是在英国,我记得英国人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能瞎吹的——英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并且一言九鼎。就这些,我们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巴:英格兰才是自由的避难所;英国的媒体是欧洲的共同心声,是受压迫者的庇护所,是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中坚力量。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在关键时刻看她如何付诸行动。”
[4] 在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后,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贫民阶层于1839年掀起了一场骚动甚至暴乱,这就是“人民宪章”运动。宪章运动提出六点要求:广泛的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年度会议制,平均选举权,议员选举不受财产限制和有偿服务。这些要求大多数都实现了。一些宪章者的游行队伍被政府军队冲散,主要策划者或被捕入狱,或被流放海外。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发生在爱默生旅英期间,这使他警惕有余,因为那时的法国也正在爆发革命。
1848年3月9日:“我参加了霍尔伯恩州(holburn)国民大厦(national hall)的宪章会议。我们听取了参加完法兰西共和国庆典的代表团的报告。讲台上的男男女女正唱着《马赛曲》,下面的群众一起合唱,然后又唱起了《吉伦特派之歌》(girondins)。大会的领导板着脸维持秩序,语言得体,但是会上的人们似乎热情激昂,叫喊着‘每人一张票,每人一把滑膛枪’。”
爱默生的评论是“尽管英格兰政府在废除《谷物法》后打稳了根基,但她还是有点头重脚轻”。
[5] 爱默生采用了吉朋给他的圣·乔治(st.george)的记述。权衡不同的编年史,我们发现真正的圣·乔治似乎不是文中所讲述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城的乔治·阿里乌,而是在两代人以前死去的另一个乔治。
据说40年前,也就是公元361年,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把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pple)市的一个教堂赐给了遇刺殉难的乔治·阿里乌。优西比乌斯(eusebius)指出,圣·乔治出身高贵,举止端庄,人们十分地敬重他。他公开撕毁戴克里先大帝(emperor diocletian)的反基督教法令,而戴克里先大帝当时就在城里。他“在残酷的刑罚面前,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直到他的灵魂飞向天国”。有人说这位圣人一连被折磨了10天,竟复活过来,真是奇迹。
在现代人看来,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遭遇比圣·乔治的遭遇要好得多。尽管他说他在1497年参加了“新世界”航行,可能有假,但他的确参加了远达南美的一两次海上探险,有资料显示,一个《美国百科全书》的编者曾说,事实证明韦斯普奇并不想从哥伦布那里抢走发现新大陆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