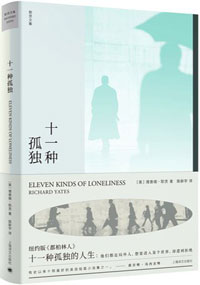由于设计简单,保存完好,巨石阵看起来还是那样新,好像是最近才完工,在未来的一千年里,人类将感谢这一时代为他们留下了准确的历史。我们徜徉在巨石阵的石林之中,反复地看着这些奇特的石头,一次又一次倍感新鲜,古老的斯芬克斯把我们民族的细微差别抛到九霄云外。对于这些灵性的石头来说,我们两个参拜者都是一样的熟悉和亲近。
这些石块是聪明的大象或磨齿兽从外地运来的,并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这只有灵长类动物才知道怎样制作这么精巧的榫头和榫眼,知道怎样磨光石头的表面。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们都选择了这片乡野中非同寻常的历史古迹,并成为1800年来诗人们的吟诵对象。
我跟朋友卡莱尔先生说好,在我离开英国前我们一同去参观一下附近的巨石阵,那地方我们俩都没去过。历史遗迹和好友相伴的双重因素,使我的这次旅行非常愉快。和英国新生代的、一个可能对当代学术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一起游览英国最古老的宗教遗址简直就是一种极致的享受了。我很乐于将这次游历经过稍加总结,以便和这个我高度评价的、对理论认识有着敏锐洞察力和强烈责任感的天才就英国的各个方面做一些合理的探讨和交流。7月7日星期五,我们登上了往西南方向去的列车,途经汉普郡,来到了索尔斯堡(salisbury),然后再坐马车去阿迈斯堡(amesbury)。宜人的天气和游伴丰富的汉普郡乡土知识——他通常每年夏季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使旅程不再漫长。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美国游客以及他们在伦敦的常去之地。他们会花些时间去看一看收藏在那里的艺术品,因为这些东西在美国根本看不到;他们还会去参观科技馆和博物馆,因为眼下它们是伦敦的吸引力所在。但我的这位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艺术和“高雅艺术”是他哲学思想的最高目标。“是呀,肯斯特(kunst)(德语——译者注)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而歌德和席勒在此方面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他认为老歌德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他后期的作品里,改换了语气。人们一旦开始谈及艺术、建筑和古迹,它们就变得一无是处。卡莱尔希望能悄无声息地把大英博物馆馆藏资料查阅一遍,他认为诚恳的人是多看少说的。在这些日子里,他认为只要查阅完他急切需要的部分资料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建筑师了。他说:“我可以给像你一样的死人们和像你抱着的死目标建造一口棺材,但你永远得不到装饰。”对于科学,他甚至更加排斥。他把萨默塞特郡议院的科学家与孔子相提并论。曾有7岁小童项橐问孔子:“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孔子回答说:“我只关心我身边的事物。”项橐又问:“你有多少根眉毛?”孔子回答说:“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索尔斯堡平原上的巨石阵
索尔斯堡平原上的巨石阵,是现存的巨石阵中规模最大的。它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约建于公元前4000—2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
说到美国人,卡莱尔抱怨说他们不喜欢英国人的冷漠态度和排外思想,他们宁愿跑到法国去,和那里的乡下人交朋结友、嬉戏娱乐,而不愿呆在伦敦做一个绅士,学习英国人博大精深的文化。
我告诉卡莱尔,我很容易感到困惑,也习惯于欣然接受英国人的一切要求。对于这种意识和精神,我在英国随处可见各种例证,并且它们都是成功的。我喜欢这个民族,他们秀外慧中,无所不有,无所不能;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等我回到马萨诸塞,这种意识和精神就会烟消云散,因为美国的地理环境必然使我感觉到:我们有着巨大的地理优势,英语民族的中心应在美国而不在英国。同根同源,但英国再伟大的技术和举措也不能和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作长期的竞争,而且这个资源枯竭的古老岛国,总有一天会像其他的父母一样,不得不承认,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显得强大。然而,无论如何,英国人绝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一观点。
我们在索尔斯堡下了火车,然后登上了前往阿迈斯堡的马车,途经老塞勒姆。那是一座光秃秃、没有树木的山丘,曾经出过两个国会议员,而现在连一个小茅棚都没有了。我们到达阿迈斯堡后,在“乔治客栈”住了下来。吃过晚饭后,我们步行来到了索尔斯堡平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宽阔的草地上,看不见一户人家,惟独巨石阵,像一群棕褐色皮肤的小矮人耸立在广袤的田野里——巨石柱和土墩——也有点像绿色的浮雕或几垛干草堆,山顶上的古庙更是显得威严无比。远远近近,几个牧羊人和羊群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个行商赶着马车沿着大路前行。这拥挤的海岛上,宽阔的草原和远古的庙宇交相辉映,这似乎得益于英伦民族对教会世界和历史发祥地的崇敬。巨石阵是一个环状柱廊,直径不到100英尺,里三层外三层。我们先绕着石头走一阵,然后翻越上去,欣赏它们的奇形怪貌和排列布阵。我们在乱石头间找到一个避风处,卡莱尔点着了一根香烟。看到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建筑——两块竖立的石头架起一块横躺的石块,好像就是这个星球地表上最恒久的东西,远甚于后来所有的教堂和历史。这些石块、这些土堆——纯粹是土丘(巨石阵周围三英里的地方就有160个)很像特洛伊平原上的土墩一样,在给达达尼尔海峡上的过往水手叙述着荷马的史诗和阿喀琉斯的荣耀。在巨石阵上,毛莨、荨麻生机盎然,而生长在四周的百里香、雏菊、绣线菊、一枝黄花、蓟和地毯草争奇斗艳。在我们的上空,云雀正婉转歌唱——这时我的朋友说:“云雀是去年孵出来的,而这里的清风却刮了几千年。”我一边数,一边用脚步测量这些巨大无比的石块,很快就对它了如指掌。现在一共有94块石头,过去可能有160块。庙呈圆形、没有顶,所在位置依石而定的——这里的门和阿伯堡(abury)的一样,都是对着正东方,“就像所有的古老山洞庙宇的大门一样”。这些石头是怎么弄到这里来的?因为这些“砂岩漂砾”,或德鲁伊特砂岩,在邻近地区是找不到的。就如我在书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祭祀石”是这一带惟一耐火的东西,它们一定是从150英里以外的地方搬运过来的。
举行祭祀的想象图
1815年绘制的一幅有关德鲁伊教团在巨石阵举行祭祀的想象图。
几乎在每一块石头上面,我们都发现了矿物学家留下的锤子和凿子的痕迹。巨石阵上内圈里的19块小石头是花岗岩。我刚从塞德威克(sedgwick)教授的剑桥陈列大懒兽和柱牙象博物馆来,所以容易认出这些石块是聪明的大象或磨齿兽从外地运来的,并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这只有灵长类动物才知道怎样制作这么精巧的榫头和榫眼,知道怎样磨光石头的表面。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们都选择了这片乡野中非同寻常的历史古迹,并成为1800年来诗人们的吟诵对象。我们对这一遗迹再做一些深入了解也为时未晚。一些勤奋的“同辈”或莱亚德(layard)将以英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坚韧,从这一块接一块的石头中穷尽整个历史。它在选择对象时异想天开,把自己的巨石阵和“野牛合唱队”[1]留于荒野,而它自己却去打开金字塔,发掘了尼尼微(nineveh)。由于设计简单,保存完好,巨石阵看起来还是那样新,好像是最近才完工,在未来的一千年里,人类将感谢这一时代为他们留下了准确的历史。我们徜徉在巨石阵的石林之中,反复地看着这些奇特的石头,一次又一次倍感新鲜,古老的斯芬克斯把我们民族的细微差别抛到九霄云外。对于这些灵性的石头来说,我们两个参拜者都是一样的熟悉和亲近。我的哲学家冷静而温和,在这静谧的命运殿堂里,卡莱尔脱口说道:“我走到哪里就把柏树栽到哪里,如果我在寻找痛苦,那么我就不能走错路。”仍然依稀可见的祭祀斑点,灰色的马路以及天然的排序,使他想起了岁月的流逝和宗教的更迭。古代的英格兰给卡莱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近几年里,除了《圣徒传》之外,他几乎没看过什么书。这53卷《圣徒传》现收藏在伦敦图书馆里,他从那里看到了英国历史。正如他所读到的,他能在那里看见圣徒伊奥那(iona)坐在那里,面对大家伏案疾书。正如他们的大寺院和大教堂所见证的那样,《圣徒传》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时代里人们都相信上帝,相信灵魂不朽,而现在,甚至连清教主义也一去不复返了。伦敦也成了异教的伦敦。他认为在英国曾生活过比它的任何作家都要伟大的人物,但现实中当那些作家出现时,那些伟人早已销声匿迹了。
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这个石墩,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来。当我们往回走到离小客栈还有两英里时,下起了一场小雨。虽然天有点晚,但那里的男女老少都在屋外抢收他们摊晒的干草。在英格兰的雨季里,这种草长得非常繁茂,着色也很深。在客栈里,老板只给我们上了一杯奶茶。当我们再叫时,女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三杯。我的朋友颇有些生气,因为他一向对英国客栈的声誉称赞有加。第二天早上,我们乘上一辆轻便马车——这是我们能够搞到的惟一的一辆车子——前往威尔顿。我邀请了地方文物收藏家布朗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巨石阵。在去巨石阵的路上,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些“天文石”和“祭祀石”的有关知识。到巨石阵后,我站在最后一块石头上,他指着那块挺直的、似乎有点倾斜的石头说是“天文石”。他要我注意那块石头的顶部与天际连成一线。“是的。”太好了。现在,正是夏至日,太阳刚好从那块石头的顶部升起。在阿伯里的德鲁特伊庙,也有一块天文石,其位置正与此相同。
在沉寂的传说里,这种与科学的关联性给人一种重要的探究线索,但我们还是要问一问大石头们这一问题:难道像蒙默思郡的杰弗雷(geoffrey)所讲述的,这是亚瑟王的谋臣莫林(merlin)用魔法从爱尔兰的基拉罗斯(killaraus)搬运过来“巨人之舞”,权当亚瑟王首领(uther pendragon)给被亨吉斯特(hengist)屠杀的英国贵族们所立的纪念碑吗?或者就如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对詹姆斯国王所解释的那样,它是古罗马人制作的工艺品?或者正如戴维斯(davies)在《塞尔特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它在设计上和风格上都与东印度的太阳神庙完全一致?在所有的作者中,司徒柯莱(stukeley)[2]可谓首屈一指。这位英雄般的古文物学家,深深地迷上了巨石阵遗址上的完美几何,把巨石阵同世界最古老的遗迹和宗教联系起来,他是满怀民族之精神,才没有说“上帝是按照巨石阵的图形创造了世界”。他发现索尔斯堡平原上横跨高地的那条“大道”,犹如地球仪上的一条纬线,而巨石阵的子午线正好从“大道”的正中央穿过。但理论的关键所在是:德鲁伊特祭司们有磁石,并以此来确定方位,他们在阿迈斯堡(amesbury)的巨石阵或者其他地方,确定的基本方位虽然和正东与正西有一点偏离,但这符合罗盘的磁差原理。在别的地方只要稍微变动一下正东或正西方向,整个磁盘的方向都会发生变化。德鲁伊特祭司是腓尼基人,磁石的名字就叫做赫拉克勒斯石(lapis heracleus),赫拉克勒斯又是腓尼基人的神。在传奇故事里,赫拉克勒斯驾着一叶小舟划向太阳,太阳神赐给他一个金杯,他用这个金杯渡过了大海。这是什么?不就是那个罗盘吗?在这个金杯或这叶小舟里把磁石放在水上漂浮,便指向北方,这也许是罗盘的最初形式,后来才把指针安装在上面的。但科学就是奥秘,就像不列颠岛是腓尼基人的秘密一样,他们严守磁盘的秘密,直到后来在与提尔人(tyrian)的贸易过程中才泄漏出去。伊阿宋(jason)的金羊毛就是这个磁盘——一块小小的天然磁石,被轻易地认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磁石,因而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一个海洋民族壮士们的贪婪和野心,他们组成了一支支海上远征队,梦想得到这块智慧的石头。从此便产生了许多有关“阿尔戈”号的神奇传说。他们的名字也十分巧合。太阳神(apollodorus)使艾格尼斯(magnes)成为娶了奈伊斯(nais)的风神(aeolus)的儿子。根据这些启示,司徒柯莱把这宏伟壮观的柱廊融进历史的长河中去,并根据罗盘的已知磁差向后推算,大胆地提出这座庙宇始建于公元前406年。
处理或搬运这么大的石块是有很大困难的,这些事情每天在各个城市里都在进行,除了借助马力,别无他法。一年前,在波士顿的波多因广场(bowdoin square),我碰巧看见人们在打造地基,旁边有几个爱尔兰助手,他们正用一台普通的转臂起吊机搬运一块与巨石阵里最大的石块不相上下的花岗岩。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工匠,也并不认为自己在做着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想一千年前就有这么聪明的工匠了。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巨石阵是怎么建造的,而后来又是怎样被遗忘的呢?半小时后,我们便坐上马车越过高地朝威尔顿进发。一路上,卡莱尔咒骂着这片领地上的领主们,说要给他一点苦头尝尝,因为他们把这大片土地圈成了可恶的牧羊场,而千千万万的英国人却在挨饿和失业。但我后来听说开垦这片土地也不经济,因为这里只长一种作物,作物收完后,这片土地就被损毁了。
建造巨石阵的三期工程之一——一期工程
建造巨石阵的三期工程之二——二期工程
建造巨石阵的三期工程之三——三期工程图a、b
建造巨石阵的三期工程之三——三期工程图c
我们来到了威尔顿的威尔顿庄园,这是彭布罗克伯爵的著名宫邸。那里曾是莎士比亚和马辛杰(massinger)很熟悉的一座庄园,菲利普·悉德尼爵士在写《阿卡狄亚》(arcadia)时常住在这里,他还和布鲁克(lord brooke)伯爵在这里畅谈过。布鲁克(lord brooke)伯爵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诗人,他叫人在他死后的墓碑上刻“菲利普·悉德尼的朋友福尔克·格雷维里·布鲁克爵士(fulke greville,lord brooke)在此安息”。现在,威尔顿庄园是彭布罗克伯爵的私产,由他的弟弟悉德尼·赫伯特先生住着,它被看作是英国庄园中最豪华的标志。我的朋友带着一封赫伯特先生写给管家的信,所以管家把我们领进了庄园。豪华客厅为长方体,高30英尺,宽30英尺,长60英尺,毗邻的房子则为正方体,高、宽、长各为30英尺。虽然房间里和那间长长的藏书室里保存着家族人员许多精美的画像(包括凡·戴克vandyke和其他人的画像),还有一些精美的图片以及摆放在四合院回廊里的各式古董和现代雕像——卡莱尔手拿着目录,边看边赞美不已,然而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窗外美丽的草坪,上面栽有英格兰最美的雪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迷人的地方。我们走出去到庄园里漫步。我们从伊尼戈·琼斯所建的小桥上走过,下面的小溪连园丁也叫不出名来。我们一边看着鹿群,一边爬上一座饰有雕塑的避暑凉亭,凉亭建在一座小山上,后面是一片森林。从凉亭下来我们走进一座意大利式的花园。我们又来到了装饰有法式半身像的一座法式凉亭,然后我们回到了屋里。这时,我们发现,客厅里已经为我们摆好了一桌的面包、肉、桃子、葡萄和白酒。
离开威尔顿庄园,我们乘一辆公共马车去索尔斯堡。那座600年前修建的大教堂,如今焕发着一股新奇的现代气息。它的尖塔是全英国最高的。不知为什么,考文垂一座不知名的教堂给我的印象更深刻一些,那座教堂高300英尺,像一株毛芯花一样轻盈,没有一点教堂气息。索尔斯堡被看作是英格兰哥特艺术的顶峰,好比去掉了装饰的扶壁,使大厦的两侧暴露无遗。教堂的中殿放着一架风琴,像一张屏风一样把东西隔开。不知为什么,现实的建筑总是满足不了视线对线条长度的要求,艺术的规则是柱廊越长就越美,越给人一种无限的美感。教堂的中殿一般很少需要用一个屏风来把它分隔开来。
我们信步走进教堂,里面的唱诗班正在进行着礼拜仪式。我们听到了里面的琴声,我的朋友说音乐不错,但少了点宗教的虔诚,有点儿像一个僧人正气喘吁吁地对着美貌天后唠叨。由于卡莱尔不太愿意,我们没去观赏唱诗班,而是去参观了本地的另一座教堂,然后返回客栈。我们坐火车经过了克拉伦登猎场(clarendon park),尽管卡莱尔特别想看一看“克拉伦登法”(decrees of clarendon)的诞生地,但除了一片森林的边缘外,几乎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在毕晓普斯托克(bishopstoke)下了车,找到赫尔普斯先生,他把我们接上他的马车,带我们到了他在毕晓普沃尔塞姆(bishops waltham)的家中[3]。
星期日那天,下着大雨,我们呆在家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的朋友就英国的发展前景询问我:美国人是不是持有一些高见呢?这个问题让我很为难。我想我既没有参与过领导决议也没有参加过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内阁大臣,更不是能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的思维简单而纯粹,我说:“当然有的。但持有那些观点的人都是我不应该讲给你们英国人听的梦幻狂,你们英国人听起来也会感到十分荒谬——然而它又千真万确。”于是我开始讲述非政府、不抵抗运动的信条,并等待他的反驳和嘲弄,可他还算坚持听了下去。我说,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在哪个国家有人敢于如此地坚持这一真理,然而我十分清楚,惟有这种勇气促使我敬畏和佩服。我经常看到暴力革命者的悲惨下场——有些伟人也都是暴力主义者——但只要上帝还活着,结局就是这样。以暴制暴很难,爱和正义才能完成彻底的革命。我猜想卡莱尔对我的过去略有耳闻,所以坚持说我对在英国实现非暴力可能性持有的显明的荒谬观点与绅士们如出一辙。这正如我们在伦敦或波士顿吃到羊排和菠菜时,我们心里也许会用塔列(talleyrand)的话说:“monsineur,je n’en vois la ne’cessite。”[4]由于我说起话来像个圣徒,开餐时卡莱尔不肯从我前面走过——“他太坏了”。我背靠墙站着一动不动,主人灵机一动上来给我们解了围,他边说“最坏的人先走”边走过去,然后卡莱尔跟在他后面,我走在最后[5]。
索尔斯堡大教堂
这是美国著名画家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的画作。这座建筑在绿色草坪上的大教堂,是一座纯粹的英国教堂建筑,美丽壮观非凡。
那天整个下午,我们在去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路上,主人和我们形影不离。朋友问了许多问题,诸如美国的自然景观、森林、房子——譬如我自己的住房。要圆满回答这些问题还真不容易。我想,在美国大地,自然的沉睡、繁盛的发展、模糊的意识,让大半美国人如痴如醉,这必然产生某种悲哀,就像夜间看到的沐浴在露珠和雨水之中的沼泽地和森林里繁茂的植被,令人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在这广袤的、未被开垦的土地上,在高高的阿勒格尼(alleghany)牧场里,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很久以前被赶出英国幸福家园的伟大母亲仍然在沉睡着、咕哝着、隐藏着。在英国,我对此感触颇深。这里人人温文尔雅,六点整装进餐。因此,我尽量用些牵强的理由把朋友们搪塞过去。
就要到温彻斯特城时,我们在圣十字教堂前下了车,把这里古香古色的文物粗略看了一遍后,我们要了一块面包和一份鲜啤酒。因为教堂创建人亨利·德·布洛伊斯(henry de blois)在1136年就规定:每个来到大门口的人都要赏赐这两样东西。看守教堂的那对老夫妇给了我们两份。他们说,每天都有几十人来到这里喝啤酒。这种延续了700年的好客和热情并没能阻止卡莱尔对一年收取二千英镑的牧师破口大骂,他说那笔钱本来就是给穷人的,而他施舍的这些小恩小惠无非就是几块面包和几口啤酒。
站在大教堂里,我醉心于它的宏伟。教堂长556英尺、宽250英尺,为英国教堂之首。在我参观过的所有教堂中,除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和约克教堂,我想我最喜欢的就是它了。卡努特国王(canute)就葬于此地。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和撒克逊族国王们也是在此加冕,死后又葬于此地。后来,威廉·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也葬在他自己的教堂。这座教堂十分古老。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了老教堂撒克逊和诺尔曼风格的拱顶,它们的上面又修建了现代的拱门。这些地下室有一部分建于1400年或1500年前。莎朗·特纳(sharon turner)在他的《益格鲁·撒克逊史》中说道:“阿尔弗烈德葬在威斯敏斯特寺,葬在他自己创建的教堂里。但他的后人,从亨利一世开始,就搬到了市北边的休德(hude)牧场的新教堂,并葬于高高的祭坛下面。这座教堂毁于‘宗教改革’,只留下阿尔弗烈德的遗体,他现在正躺在新教堂下面,或者说是埋在老教堂的废墟上。”威廉·威克姆的陵园向我们开放。卡莱尔抓住斜着的大理石雕像的手臂,深情地拍了拍它们,他十分敬重这位修建温莎堡、大教堂、学校和牛津新学院的伟人。黄昏时,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教堂,和主人道别后,登上了前往伦敦的火车。
* * *
[1] choir gaur或cr gawr的意思是巨人的圆形广场或庙宇,只是英国人给巨石阵取的名字。它源于史前撒克逊人所指的“高悬在天上的石头”。
[2] 司徒柯莱(stukeley)对巨石阵曾做过如下描绘:“巨石阵与一条林荫道及马路相连。这条林荫道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从入口处呈直线一直延伸594码,然后分成两条岔道,分别通往一排山冈和马路,——一条人工修筑的平坦土路。这条路长3036码,宽110码,从巨石阵往东北方向有半英里的路程,一些坑坑洼洼显示它的分界线。”
[3] 爱默生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这样说到毕晓普沃尔塞姆:“一个人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机智聪明、无所不知的人,他们心想事成,博学多才。只要他们决定做的事绝无半途而废之理。我昨天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名字也奇特,叫亚瑟·赫尔普斯。”
[4] “mais,monseigaeur,il faut que j’existe.”——作者原注。这两句都是法语。正文的意思是:“先生,我看没必要。”脚注的意思是:“但是,殿下,我必须活下去。”
[5] 既然他们相聚在一起,他们也一天天地成了好朋友。两年后,卡莱尔遗憾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当我们用现实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时,我就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也知道(你自己可能也知道)地下几里深处的岩层在哪里接合;那两颗可怜的心是团结一致的。”幸好他们彼此分离,在他们的余生中也彼此记得“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个兄弟在为我活着,而且至死不渝”!——摘自《卡莱尔——爱默生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