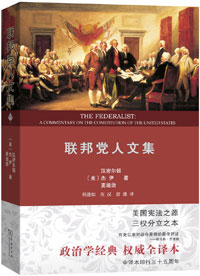夜里的窗子,黑魆魆地向黑暗里探望,在这静止的状态里,潜伏着不祥的隐秘。
方凳上放着一盏没有玻璃罩的洋铁灯,油烟好像黑丧服似的,急促地摆动着,向顶棚直冒。满屋都是烟味。地板上铺着一幅怪地毯,上边记着无数的符号、线条,绿色的、蓝色的斑点,黑色的曲线——这是一大幅高加索地图。
指挥员们解了皮带,穿着衬衣,光着脚,谨慎小心地在地图上爬着。有的吸烟,当心怕烟灰落到地图上;有的目不转睛地瞅着,在地图上爬着。郭如鹤紧闭着牙关,蹲着,用亮晶晶的刺人的小眼睛,向旁边张望,他脸上流露出自己的主张。一切都沉没在蓝色的烟雾里。
白天忘记了的充满着威胁的河水声,现在一分钟也不停地从黑洞洞的窗子里传进来。
虽然这所房子和邻近房子的居民都迁了,可是仍然从那儿传来小心的低低的说话声:
“咱们一定会死在这里:连一道战斗命令也没有执行。你们难道没看见吗?……”
“对战士们没法办。”
“这样他们都会窝窝囊囊死光——都会叫哥萨克杀光。”
“不打雷,乡下佬是不会祷告的。”
“怎么还没打雷,周围都像火灾一样烧起来了。”
“哦,去吧,告诉他们去吧。”
“可是我说——应当占领诺沃露西斯克,到那儿待一下再说。”
“关于诺沃露西斯克,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位穿着干净衬衣、束着皮带、脸刮得光光的人说,“我有史戈尼克同志的一份情报。那边是一塌糊涂:那里有德国人、土耳其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沙皇军官团,也有咱们的革命委员会。大家都尽在开会,没完没了地讨论,从这个会场跑到那个会场,制订了千千万万的挽救计划——这些全是无聊的空文。把部队开到那里去,就是要叫它完全瓦解。”
在那不停的河水声里,清楚地传来了一声枪响。这枪声是很远的,可是夜里的窗子用它那潜隐的死寂和黑暗,却即刻告诉说:“瞧……开始了……”
大家都满心紧张地倾听着,可是表面上却都使劲吸烟,用手指在地图上继续指画着,仔细进行研究。
可是指来指去反正一个样:左边是走不通的蔚蓝的大海;右边和上边,斑斑点点地散布着好多含着敌意的村镇的名称;下面向南去,是发着栗色的、遮断去路的不能通行的高山——简直是死路一条。
好像庞大的游民的屯营一样,扎在这地图上画着黑线的弯弯曲曲的河边。河水声时时传到这漆黑的窗子里。地图上绘的山谷中、芦苇中、森林中、草原上、田庄和村镇里,到处都密集着哥萨克。到现在为止,叛乱的村镇和田庄,总算对对付付地分别镇压下去了,可是现在全库班都野火燎原似的叛乱起来。苏维埃政权到处都被搞垮了;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人物,在各田庄、各村镇里,全被杀光了,好像坟院上的十字架一样,到处都立着绞刑架:绞杀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外乡的布尔什维克,可是也有哥萨克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尸体都吊在绞刑架上摇摆着。往哪退呢?哪里有救星呢?
“当然,到吉荷列次去,从那里到圣十字去,再从那里到俄罗斯去。”
“真聪明——到圣十字去!没有子弹,没有炮弹,你怎么能通过叛乱了的全库班到那里呢?”
“可是我说,到咱们的主力军那里去吧……”
“可是这主力军在哪里呢?你得到了紧急消息吗?那你就告诉咱们吧。”
“我是说去占领诺沃露西斯克,在那里等着俄罗斯派援军吧。”
他们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每个人的话后边,却都藏着话:
“要是把一切事都交给我,我一定会定出顶好的计划,而且会把大家都救出来的……”
远远的枪声,带着不祥的预兆又响起来,把夜间的河水声都遮住了;稍停了一会儿,又响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忽然一阵排枪声——就又沉寂了。
大家都转过头去,对着那死沉沉的黑窗子。
不是在墙外附近什么地方,就是在楼顶上,公鸡叫了起来。
“卜利合吉科同志,”郭如鹤开口说,“到那里看看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位年青、漂亮、脸上微微有点麻子、身个不高的库班哥萨克,穿着紧身小棉袄,光着脚,谨慎小心地出去了。
“可是我说……”
“对不起,同志,这绝对不许可……”一位脸刮得光光的人,平心静气地站着,对他们一点都不客气地把话打断了:这些都是出身农民、箍桶匠、细木匠、理发匠的战士,在战场上提升成军官的,而他却是一位受过军事教育的老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来调动部队,这就是叫去送死:这不是部队,而是乌合之众。必须改编。此外,成千成万的难民的马车,完全把手脚都捆住了。一定要他们离开部队——让他们随便走吧,或者回家去;部队应当完全自由,无牵无挂。下命令吧:‘在村内停留两天,以便改编……’”
他说着,可是话内却藏着话:
“我有广博的学识,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军事学有深刻的历史研究,——为什么叫他领导而不叫我领导呢?群众是盲目的,群众永远……”
“你想怎么办呢?”郭如鹤用那锈铁一般的声音说,“每个战士的父母妻子都在辎重车上,难道叫他把他们丢下不管吗?如果咱们坐在这里等待——那只有被敌人杀光了。咱们应当走,走,走!咱们走着改编着。应当赶快从城边过去,不停顿地沿着海边走。到了杜阿卜塞,从那里沿着公路,翻过大岭,同咱们的主力军会合起来。他们走得不远。可是这里每天都被死亡包围着。”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计划是最好不过的,别人的却是一点没用。
郭如鹤站起来,瘤子在抽动着,灰钢似的光泽,从那小小的眼缝里射出来,说:
“明天出发……天亮出发。”
但是他心里想:“都不会听命令的,狗东西!……”
大家都不乐意地沉默着,可是在这沉默的后面却藏着下面的话:
“对傻子是讲不清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