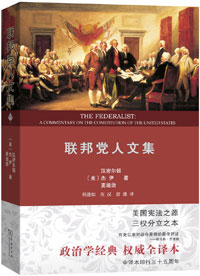森林上边,山谷上边,是重重叠叠的岩峰。一阵微风吹来,即刻感到凉爽,可是下边的公路上——却是暑热、苍蝇、灰尘。
公路窄得像走廊一样,从那里通过——两边被石岩紧紧夹着。被水冲刷出来的树根,从岩上垂下来。每逢转弯的地方,前前后后的东西都看不见了。简直不能转身,也不能回头。浩浩荡荡的人流,川流不息地在这走廊里向一个方向奔流。山岩把大海遮住了。
停止前进了。人马车辆都停止前进了。长久地、疲倦地停着,后来又行动起来,又停住了。谁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而且什么也望不见——尽是马车,可是那边是转角和峭壁;顶上是一线蓝天。
细细的声音:
“妈——妈,酸苹果!……”
另一辆马车上:
“妈——妈!……”
第三辆马车上:
“你别作声!到哪弄呢?……山跟墙一样陡,能爬上去吗?你瞧,这山不是跟墙一样陡吗?”
孩子们不听,哭着,后来拼命叫起来:
“妈——妈!……给我玉米!……给我酸苹果……酸苹果!……玉——米——米……给我呀!……”
母亲们火起来,母狼一样,眼里闪着光,野头野脑地四面张望着,打着孩子。
“别作声!你们真该死。你们死了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于是恶狠狠地无力地流着眼泪,哭起来。
远远地响起了低沉的枪声。谁也不听,谁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停下来。走动了,又停下来。
“妈妈,玉米!……”
母亲们仍然怒气冲冲地只想把每个人的咽喉都咬断,互相骂着,在车里乱找着。从马车里找出一根嫩玉米秆,痛苦地嚼了好久,尽力嚼着,牙根都嚼出血了;后来伏到孩子的贪婪地张着的小嘴上,用温暖的舌头喂进去。孩子噙住想往下吞,渣滓刺着咽喉,呛着,咳嗽着,吐出来,叫着。
“不——吃!我不——吃!”
母亲们怒气冲冲地打起来。
“你要什么呢?”
孩子们擦着脸上肮脏的眼泪,硬吞了下去。
郭如鹤咬紧牙关,从岩后用望远镜望着敌人的阵地。指挥员们聚在一起,也用望远镜望着;战士们眯缝起眼睛望着,并不比望远镜差。
转弯那边的山峡开阔了。从这宽阔的咽喉似的山峡望去,是蔚蓝的远山。重岩上的稠密的大片森林,把重岩遮起来。重岩顶部是燧石质的,岩顶有四丈高的垂直悬岩——那儿是敌人的战壕。十六门大炮,贪婪地窥视着通到走廊的公路。要是部队从岩门一出来,大炮和机枪一齐干起来——全是死路一条;战士们即刻就会涌向岩后去。郭如鹤很清楚——这儿连鸟雀也飞不过去呢。部队没有地方展开,只有这一条公路,这是死路。他望着下边远处发白的小城,望着碧蓝的海湾和海湾上黑魆魆的格鲁吉亚轮船。应当生个新办法——什么办法呢?应该找别的门路——可是什么门路呢?于是他跪下去,伏到遍地灰尘的公路上铺的地图上,在地图上爬着,研究那些极小的曲折、褶纹和山径。
“郭如鹤同志!”
郭如鹤抬起头来。两个人醉醺醺地站着。
“坏东西!……可赶上喝够了……”
可是他却不作声地望着他们。
“是这么回事,郭如鹤同志,这条路咱们是跳不过去的,格鲁吉亚人要把咱们完全干光的。我们刚去侦察过……自告奋勇去的。”
郭如鹤依然目不转睛地望着:
“呼一口气给我闻闻。别往肚里吸气,向我吐一口气。不晓得为着这要犯枪决罪吗?”
“实在话,这树林里有鬼气——我们时时刻刻在树林里走,于是把鬼气就吸到肚里了。”
“难道这里会有小酒铺吗,怎么呢!”另一个长着狡猾而且快活的乌克兰人的眼睛,插嘴说,“树林里光有树木,别的什么也没有。”
“你说正经事吧。”
“是这么回事,郭如鹤同志,我们同他一起,我们说的都是正经话:或是我们大家都死在这公路上,或是都落到哥萨克人手里活受罪吧。可是都不愿死,也不愿落到哥萨克手里。那怎么好呢?忽然望见树那边有一个小酒铺。我们爬到跟前——四个格鲁吉亚人在喝酒,吃烤羊肉;当然,格鲁吉亚人都喝醉了。鼻子一闻,真想喝呀,真想喝,没有力气。他们有手枪呢。我们一跳出去,把两个用枪打死了:‘站着,别挪地方!你们被包围了,妈妈的!……举起手来!’……这些家伙呆了——没有想到。我们又干掉一个,把剩下这个绑起来。把掌柜的可吓死了。啊,我们老实说吧,我们把格鲁吉亚人吃剩下的烤羊肉都吃光了,那肉该是付过钱的——他们领的兵饷可不少啊,至于酒的话,连嘴唇也没有挨,因为你下过命令呢。”
另一个人晃荡了一下,向郭如鹤走近了一步,打着嗝说:
“让那该咒的酒去他妈的吧……我要闻过它一下,叫我的脸都歪成鬼脸,叫我的肚子肠子都翻出来……”
“说正经事吧。”
“我们把打死的格鲁吉亚人,拉到树林里,把武器取下来,怕走漏消息,就把另一个格鲁吉亚人和掌柜的带来了。还碰着五个老百姓,带着女人和姑娘们——都是本地人,是这城边的人,是咱们俄罗斯人。他们住在这城边,可是格鲁吉亚人是亚洲人,黑皮肤,同咱们人不一样,很喜欢白种女人。他们把一切都扔了跑到咱们这里来,他们说,顺着小路可以绕过城走呢。他们说一路都是深沟、森林、石岩、小沟。难是难,不过可以过去。要是照直冲,他们说是不可能的。他们对一切小路,就好像自己的五个指头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啊,难,的确难得很,一句话,难得要命,可是总是能过得去的。”
“他们在哪里?”
“在这里。”
营长走到跟前。
“郭如鹤同志,刚才我们到了海边,那里不管怎样都过不去:海岸是悬岩,一直伸到水里。”
“水很深吗?”
“岩跟前截腰深,有些地方齐脖子深,有些地方把头都淹住了。”
“怎么呢,”一个满身褴褛的战士,手里拿着步枪,注意听着说,“淹住头有什么呢……海里有从山上滚下来的乱石堆,好像兔子一样,可以从石尖上跳呢。”
报告、指示、说明,有时还有意料不到的、聪明的、出色的计划,都从四面八方给郭如鹤送来——总的情况都非常清楚了。
把指挥员都召集起来。他咬紧牙关,突出的头盖下,是一双洞悉一切的锐利的眼睛。
“同志们,这样吧,所有三个骑兵连都绕着城市前进。绕道走是很难的:顺着小路、森林、石岩、山峡,而且是夜间;可是不管怎样都要完成任务。”
“糟了……连一匹马也回不来的……”这些话虽然没有从口里说出来,可是都藏在眼睛里。
“有五个带路人——是俄国人,是本地居民。都受过格鲁吉亚人的害。他们的家属在咱们这里。对带路人已经宣布过——要他们的家属担保。绕到后方,冲到城里……”
他凝视着山峡里朦胧的夜色,沉默了一会儿,简洁地抡了一句:
“把他们全部消灭!”
骑兵们雄赳赳地把毛皮帽子往后脑上好好一戴:
“一定完成任务,郭如鹤同志。”于是都勇猛地上了马。
郭如鹤说:
“步兵团……郝洛莫夫同志,你的一团人从石岩上下去,跳过石尖,到码头上去。黎明时向轮船冲去,把全部轮船夺来,不要开枪。”
于是稍停了一下,又抡了一句:
“把他们全部消灭!”
“要是格鲁吉亚人往海上派一个射击手,会把全团人从石头尖上一个个消灭……”
可是都一齐大声说:
“服从命令,郭如鹤同志。”
“两团人准备从正面冲。”
远山顶上的红光,逐渐消失了:呈现出一片单调的深蓝色。黑夜笼罩了山峡。
“我带着这两团人。”
在黑暗的沉寂里,在一切人面前,都留着这样的痕迹:繁茂的森林,森林后边是燧石质的陡坡,上边是孤零零的垂直的峭壁,就像闭着眼睛的死神一般……停一会儿,这痕迹就消失了。夜在山峡里爬着。郭如鹤登到岩石上。下边是光着脚,浑身褴褛的一片模糊的行列,无数尖尖的枪刺,密密麻麻地排列在那里。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郭如鹤——解决生死问题的机密在他手里呢:他担负着指示出路,从绝境里指示出路的责任,大家都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呢。
千百只渴望的眼睛,盯着郭如鹤,他觉得自己是未知的生死机密的主宰者,他说道:
“同志们!咱们没有出路了:或者都战死在这里,或者是叫哥萨克从后边把咱们杀光。简直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子弹,没有炮弹,咱们要赤手空拳去占领,可是敌人那里却有十六门大炮对着咱们呢。不过,如果大家能万众一心……”他沉默了一下,铁脸成了石头一样,用那不像人的粗野声音喊起来,大家都觉得一阵心寒:“如果能万众一心冲上去,就可以打开一条生路!”
他所说的话,不待他说,每个战士也都知道,可是当他用那怪声音喊出来的时候,一种意外的新奇,使大家吃了一惊,于是战士们都喊道:
“万众一心!!不是咱们打出去,就都战死在这里!”
闪闪石岩的斑点消失了。不论是重岩、岩石,还是森林,什么也都看不见了。走远了的最后一些马屁股也消失了。战士们互相牵着破衣服,下到海滩上,好似小石头一样,散布在那儿,这些也望不见了。两团人的最后的行列,也消失在黑压压的森林里,森林上边是那闭着眼睛的死神一般的垂直的悬岩。
辎重车在庞大的夜的沉寂里,静静地停着:没有营火,没有说话声,也没有欢笑声,孩子们带着饿得凹陷的小脸,无声地躺着。
沉寂。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