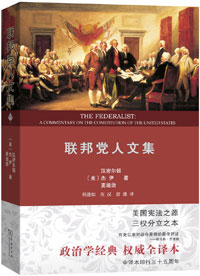衣服褴褛、满身灰尘、被火药烧灼了的行列,都皱着眉头,鼓着全力,带着沉重的脚步声,迈着阔步,密集地前进着。眉下的小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目不转睛地盯住那暑热的、抖颤的、荒凉的、草原的边极。
匆忙的炮车,发出沉重的隆隆的响声。马匹在尘雾里急躁地摆着头……炮兵们盯着遥远的蔚蓝的地平线。
辎重车在巨大的、片刻不停的隆隆声里,无穷无尽地行进着。孤单单的母亲们,跟着别人的马车走着,脚把路上的灰尘匆匆地扬起来。永世哭不出泪的眼睛,在发黑的脸上闪着干巴巴的光芒,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辽远的草原上的同样蔚蓝的地平线。
受了大家这样匆忙影响的伤员们,也在前进。有的腿上裹着肮脏的纱布跛行着。有的抬起肩膀,大步移着拐杖。有的用瘦骨嶙峋的手,精疲力尽地抓住马车边——可是都同样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蔚蓝的远极。
千万只焦灼的眼睛,紧张地盯着前方:——那里——是幸福,那里——是苦难和疲劳的终局。
故乡的库班的太阳蒸晒着。
不管是歌声、说话声,也不管是留声机声,都听不见了。急促地腾起的尘雾里,无穷无尽的吱吱声、沉重的马蹄声、部队的笨重的低沉的脚步声、惊慌的大群的苍蝇——这一切,这连绵数十俄里的一切,就像奔腾的急流,向那充满诱惑的、蔚蓝的、神秘的远极奔流着。眼看就要满心欢喜地惊叹起来:咱们的!
可是,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走过多少集镇、乡村、田庄、屯子——总是那一个样:蔚蓝的远极,总是越走越向前推移,依然是神秘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极。不管你走过多少地方,到处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
“到过了,走了。前天还在的,可是都急急忙忙,乱忙了一阵子,就又动身走了。”
是的,是到过了。这不是拴马桩,到处都撒着马料,到处都是马粪;可是现在呢——空空如也。
这儿是炮兵驻扎过的地方,这是熄灭了的营火的灰烬和沉重的炮车轮,从村后往大路上拐弯的辙印。
路旁尖塔形的老白杨,被擦破了皮,深深的伤痕发着白色——这是辎重车轴挂破的。
大家都说,一切都是为了刚过去的人们,为了他们,这些人才在德国军舰上射出的开花弹下前进,才同格鲁吉亚人奋战,为了他们,这些人才把孩子扔在山峡里,才同哥萨克人死战——可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蔚蓝的远极,尽管向前推移。依旧是匆匆的马蹄声、辎重车的急促的吱吱声、慌张追赶的黑压压的大群苍蝇、无边无际的毫不停息的脚步声,灰尘也勉强跟上去,在千千万万的人流上旋卷着,盯着草原边极的千万人的眼睛里,依旧流露着不灭的希望。
憔悴的郭如鹤——皮肤像炭一样——愁眉不展地坐在车上,同大家一样,眯缝得窄窄的灰眼睛,日夜都盯着远远的地平线。这对于他,也是神秘的、莫名其妙的、不能忘怀的东西。他咬紧牙关。
就这样精疲力尽,日复一日地走过一镇又一镇,走过一村又一村。
哥萨克女人,恭恭敬敬地迎接他们,她们那温存的眼睛里却含着憎恨。当他们走过的时候,都惊奇地从后边望着:一个人也不杀,也不抢,不过这都是些可恨的野兽啊。
宿营时,给郭如鹤送来报告说:尽都是那样的——前边的哥萨克部队,一枪不发地退到两旁,让出路来。不管白天黑夜,这支部队连一次袭击也没遇到。后卫队也没遇到袭击,部队一过,就又从后边把道路封锁起来了。
“好!……可叫他们领教了……”郭如鹤说着,脸上的筋纹在抽动。
他下命令说:
“派骑兵到所有辎重队和部队去,叫他们一点都不要耽误。不让他们停留。走、走!宿营不能超过三小时……”
于是辎重车又使劲吱吱响起来,疲乏的马匹拉着绳索,大炮沉重地匆匆地隆隆响着。于是不管在尘土飞扬的暑热的正午,不管在繁星闪烁的黑夜,也不管在尚未睡醒的晨曦里,在库班草原上,都是一片沉重的、经久不息的隆隆声。
向郭如鹤报告道:
“马都倒毙了,部队里有人掉队了。”
可是他咬着牙说:
“把大车丢掉。东西放到别的车上。注意掉队的人,帮助他们。加快速度,走、走!”
千万只眼睛,又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收割后的发黄的草原的远极。各村镇、各田庄上的哥萨克女人,依旧怀着憎恨,温存地说:
“到过了,走了——昨天到过的。”
都发愁地望着——是的,尽是这样的:冷了的营火,散落的草料、马粪。
忽然间,在所有辎重队和部队里,在妇女和孩子中间,都传说着:
“把桥梁炸了……一过去随后就把桥炸了……”
连老太婆郭必诺的眼里也含着惊慌,用干嘴唇低声说:
“把桥都破坏了。一过去,随后就把桥破坏了。”
战士们发硬的手里握着枪,也用低沉的声音说:
“把桥炸了……避开咱们把桥炸了……”
于是,当先头部队走到小河、小溪、断岩或沼泽地方时,都看见:露着破坏了的桥板;被破坏了的桥桩,像发黑的牙齿立在那儿——路断了,弥漫着一片失望。
可是,郭如鹤把眉头一皱,命令道:
“把桥修复,设法渡过去。编一个特别队,要很敏捷的人,带着斧子。叫他们骑马到前边去,同前锋在一起。到居民家里收集木柱、木板、梁木等等,运到先头部队去!”
斧子响起来,白木片在阳光下闪闪飞舞。于是,千千万万的人群、无穷无尽的辎重车、沉重的炮兵,都又沿着那一条线似的、摇摆的、吱吱发响的桥板通过,马匹谨慎小心地用鼻子呼呼出着气,战战兢兢地斜着眼睛,望着两旁的水。
人流无穷无尽地奔腾着,所有的眼睛,都依旧盯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把天与地隔开来的地平线。
郭如鹤召集了指挥员们,面上的筋纹抽动着、沉着地说:
“同志们,咱们的主力军拼命离开咱们走了……”
都愁眉不展地回答他说:
“咱们一点儿也不明白。”
“一过去就把桥毁了。这样咱们长久是受不了的,马成几十匹地倒毙了。人也精疲力尽了,掉队了,可是掉队的人,要被哥萨克杀掉的。现在咱对哥萨克给了教训,他们怕了,躲开了,将军们都把自己的队伍带走,把路让出来了。可是咱们总是在铁的重围里,如果要这样长久下去,反正会把咱们搞毁的——子弹不多、炮弹又少。要设法冲出去呢。”
他眯缝得很细的锐利的眼睛望了一下。大家都默然不语。
这时郭如鹤一字一板地说着,把话从牙缝里挤出来:
“应当冲出去。要是派骑兵队去——咱们的马不好,经不起赶,哥萨克会把他们杀光的,那时哥萨克壮起胆子来,就会从四面八方向咱进攻。要想别的办法。要冲出去,给咱的主力军送消息。”
又是默然不语。郭如鹤说:
“谁愿报奋勇去?”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
“赛利万诺夫同志,带两个战士,坐上汽车快动身吧!不管怎样都要冲出去。到那里就告诉他们说:这是咱们。他们干吗尽管跑呢?叫咱们送命吗,怎么呢?”
一小时后,在斜阳照着的司令部房子跟前,停着一辆汽车。两架机枪从上边窥视着:一架在前,一架在后。司机同一般司机一样,穿着油污的军便服,口里噙着纸烟,一个人聚精会神地在汽车跟前乱忙了一阵,把车子检查完了;赛利万诺夫和两个面貌年轻的、无忧无虑的战士,眼里却有些紧张。
汽车呜呜地叫了两声,开走了,兜着圈子,扬着灰尘,向前驶去,越变越小,终于缩成一个小点消失了。
可是无尽的人群、无尽的辎重、无尽的马匹,都在流着,一点也不知道关于汽车的事,都不停息地阴沉沉地流着,有的怀着希望,有的带着失望的神情,盯着遥远的蔚蓝的远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