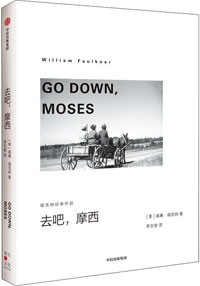自从阿亨托拉图穆胜利以后,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尤里安从蛮族手里解放了高卢。
早春的时候,他在琉提喜阿越冬的住宅里收到皇帝的一封重要信函,这是御前司书大臣德岑西乌斯亲自送来的。
在高卢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使君士坦提乌斯大受屈辱,对他的虚荣心是一次新的打击:这个毛孩子,这只“多嘴多舌的喜鹊”“身穿紫袍的猴子”,可笑的“小小胜利者”,让宫廷里那帮爱讥笑人的人大为恼火的是,他竟然变成了真正的威武的胜利者。
君士坦提乌斯很羡慕尤里安,与此同时,他自己在亚细亚各行省跟波斯人打仗却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
他瘦了,失眠,吃饭没有胃口。他犯了两次黄疸病。御医们非常惊惶。
有时夜里失眠,他睁着眼睛躺在豪华的卧榻上,床头立着君士坦丁大帝的神圣神幡——“拉伯龙”旗,他想道:
“欧萨维亚欺骗了我。假如不是她,我便会实行保罗和墨耳枯里乌斯的建议,把这个毛孩子,弗拉维乌斯家族的小蛇勒死。蠢货!自己把他在怀里暖和过来了。有谁知道呢,也许欧萨维亚是他的情妇吧!”
迟到的嫉妒使他的羡慕更加无法忍受:他已经不能向欧萨维亚进行报复了——她死了;第二房妻子法乌斯蒂娜是个愚蠢的美丽的小姑娘,他没有把她看在眼里。
君士坦提乌斯在黑暗中抓住自己稀疏的头发——理发师每天早晨都精心地给打成发卷,——流出了恶毒的眼泪。
他不是保卫了教会吗,不是关心铲除异端邪说吗?他不是建造和装修了教堂吗?不是每天早晨、每天晚上都按规定进行祈祷和跪拜吗?可是结果如何?得到了什么样的奖赏?这位人间的主宰平生第一次对天上的主宰发起怒来。祈祷词停留在他的嘴边上。
为了哪怕稍稍消除自己的羡慕,他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往帝国的各大城市分送缠着月桂叶的捷报,通报上帝赏赐给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胜利,捷报在广场上宣读。根据这些捷报可以判断出,四次渡过莱茵河的并不是尤里安,而是君士坦提乌斯,尽管他这时正在世界的另一端与波斯的战事中不光彩地遭到了失败;并不是尤里安,而是君士坦提乌斯在阿亨托拉图穆负了伤,但俘虏了克诺多玛国王;并不是尤里安,而是君士坦提乌斯穿越沼泽和密林,开辟道路,围困城堡,忍饥挨饿,冒着酷暑,比普通士兵更劳累,比他们睡眠更少。这些缠着月桂叶的捷报甚至连尤里安的名字都没有提,仿佛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副帝。民众欢呼的高卢的胜利者是君士坦提乌斯,所有的教堂里,神甫、主教、宗主教主持祈祷仪式,为皇帝祈求福寿安康,感激上帝赐给君士坦提乌斯对蛮族的胜利。
可是羡慕之情并没有消除,照旧啃食着皇帝的心。
于是他决定把军团的精华部分从尤里安手里夺过来,不知不觉地使他失掉力量,就像当年加卢斯那样,把他吸引到自己的罗网之中,然后给这个被解除了武装的人以最后的打击。
为此目的,经验丰富的大臣、御前司书德岑西乌斯奉派前来琉提喜阿,他应该立即从副帝的军队中抽调辅助军团——赫鲁利人军团、巴塔维人军团、威猛军团、克尔特人军团——派往亚细亚,由皇帝指挥;此外,他还得从每个军团挑选三百名最勇敢的军士。统兵官欣图拉接到命令之后,把挑选出来的盾牌兵和异族兵丁编在一起,亲自担任其首领并且率领他们去晋见皇帝。
尤里安警告德岑西乌斯,指出了由蛮族组成的军团有发生暴动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宁肯死也不愿意离开家乡。德岑西乌斯对这些警告毫不理睬,刮得光光的狡猾的蜡黄的脸仍然保持着不慌不忙的傲视一切的表情,表现出十足的长官气魄。
一座把琉提喜阿岛与河岸连接起来的木桥附近,有很长一排建筑物,这是主要兵营。
军队里的骚乱从早晨就开始扩大。只是由于尤里安建立的严格军纪还能遏制住士兵。
赫鲁利人军团和威猛军团第一批几个大队夜间就开始行动了。他们的弟兄,克尔特人军团和巴塔维人军团也准备启程。
欣图拉突然听到抱怨声,便用非常自信的声音下达了命令。一个不驯服的士兵被皮鞭抽得已经半死。德岑西乌斯耳朵上夹着一支笔,手里拿着文件,到处乱窜。
黄昏时分,天空阴暗,院子里和大路上停着许多带篷的大轱辘车,这是用来拉士兵的妻子儿女的。女人们一边哭诉着一边跟故乡告别。有人把双手伸向密林和荒原;有人趴在地上,哀号着亲吻土地,把土地叫作自己的母亲,悲哀地说,他们的骸骨将烂在异国他乡;有人沉浸在默默的痛苦之中,用破布包上一包故乡的泥留作纪念。一条狗瘦得露出了肋骨,舔着涂在车轴上的油脂。它突然走到一旁,把头伸进尘土里,嗥叫起来。大家都把脸背过去,身体颤抖着。一个军士气愤地向狗踢了一脚。狗夹起尾巴,尖声叫着向田野跑去,在那里停下来之后,叫得更响了,同时也更加凄惨了。这拖着长声的吠叫在阴沉沉的黄昏奇异的寂静中让人毛骨悚然。
萨尔马特人阿拉加里属于应该离开北方的那些人之列,他与自己忠诚的朋友斯特隆比克告别。
“大叔,亲爱的,你把我抛给谁呀!……”斯特隆比克哼哼唧唧地说,一边吃着士兵的面汤。这是阿拉加里让给他的,他因为痛苦而咽不下去。斯特隆比克的泪水滴到面汤里,可是照旧贪婪地吃着。
“呶,闭嘴,傻瓜,”阿拉加里安慰他,根据自己的习惯,尖声尖气地骂着,同时又表现出一片柔情,“女人们的号叫已经够受的了,还得加上你一份!……最好还是你详细对我说说——你就是那里的人——那里树林子什么样,橡树多还是白桦树多?”
“你说什么,大叔?上帝保佑你!那里哪儿有树林子?净是沙子和石头!”
“什么?人要想躲躲阳光可到哪里去呀?”
“无处可躲,大叔。一句话,处处是荒原、炎热——打个比喻说吧——像是在石板上。没有水。”
“怎么没有水?那好,可有啤酒吧?”
“什么啤酒!从来没听说过啤酒。”
“你撒谎!”
“大叔,你要是在整个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哪管能够找到一杯啤酒或者蜂蜜,就让我瞎了眼睛!”
“我说,老弟,不好哇!天气炎热,还没有水,没有啤酒,没有蜂蜜。要把我们赶到天边去,就像把牲口赶到屠宰场去一样。”
“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大叔,那是很偏僻的地方。”
斯特隆比克哼唧得更加凄惨了。
这时从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两个朋友从兵营里跑出去。
一群士兵通过一座浮桥向琉提喜阿岛跑来。叫喊声越来越近了。兵营里笼罩着惊惶不安。军士们来到大路上,集聚在一起,又吵又叫,把命令、威胁和百人长的殴打完全抛到脑后了。
“出了什么事?”一个老兵问道,他拿着一捆干树枝朝士兵厨房走去。
“听说又有二十个人挨了打。”
“什么二十个——是一百!”
“所有的人都轮换着挨打——这是命令!”
突然,一个穿着被撕得稀破烂的衣服的士兵,脸色苍白,他疯狂地跑进人群,大声喊起来:
“快跑哇,快到宫里去!他们把尤里安给杀了!”
这番话像是火星掉到干草堆里了。早就点燃的暴动的火焰不可遏制地旺盛起来。人的脸变成了兽性的。任何人都没有弄明白任何情况,任何人都不听任何人的话。大家却异口同声地狂叫着:
“坏人在什么地方?”
“打死这个狗日的!”
“把谁打死?”
“君士坦提乌斯的使臣!”
“皇帝滚蛋!”
“喂,你们这些胆小鬼,把这样一个首领给出卖了!”
最先碰上的两个百人长,尽管没有任何过错,却被打倒在地上,人们上去用脚踩,想要把他们撕成碎片。血溅了出来,士兵们看见血,更加疯狂了。
一群人拥过木桥,朝着兵营而来,越来越近。突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叫喊,人们听得清清楚楚:
“光荣属于尤里安皇帝,光荣属于奥古斯都·尤里安!”
“给杀死了!给杀死了!”
“闭嘴,傻瓜!奥古斯都活着——我们刚刚亲眼看见了!”
“副皇帝活着?”
“不是副皇帝,是皇帝!”
“谁说给杀死了?”
“这个恶棍在哪儿?”
“想要杀死!”
“谁想要杀死?”
“君士坦提乌斯!”
“让君士坦提乌斯滚蛋!让可恶的太监们滚蛋!”
在昏暗中,有一个人骑着马飞快地跑过去了,勉强被认出来。
“德岑西乌斯!德岑西乌斯!捉住这个强盗!”
那支笔仍然支棱在德岑西乌斯的耳朵后面,行军墨水瓶在腰带上晃来晃去。他在一片哈哈大笑和谩骂声中消失了。
人越聚越多。暴动的军队在黄昏的黑暗中骚乱起来,发出雷鸣般的嘈杂声。早晨出发的赫鲁利人军团和威猛军团返回兵营,也参加了暴动,这时,愤怒变成了天真的兴奋。许多人拥抱着同乡、妻子儿女,犹如久别重逢。有些人高兴得哭了。还有人叫喊着用剑敲击着盾牌,发出响亮的声音。燃起一堆堆篝火。出现了一批演说家。斯特隆比克年轻时在安条克曾经是个打诨逗趣的能手,这时感到来了灵感。伙伴们把他抬起来,他用手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开口说道:“nos quidem ad orbis terrarum extrema ut noxii pellimur et damnati.——要把我们派到天边去,把我们当成了罪犯,当成了恶人歹徒;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用鲜血从奴隶主手中赎买出来的,又将陷入阿勒曼尼人的羁绊。”
没等他说完,从兵营里传来尖厉刺耳的号叫声,仿佛杀猪似的,同时还能听见士兵们非常熟悉的鞭挞裸体的声音;军士们在鞭挞万恶的百人长cedo alteram。鞭挞自己长官的那个士兵扔下血淋淋的鞭子,在一片哈哈大笑声中模仿着百人长愉快的声音大声叫道:“来个新的!——cedo alteram!”
“到皇宫去!到皇宫去!”人群吼叫起来,“我们要宣布尤里安是奥古斯都,给他戴上皇冠!”
大家扔下半死不活的百人长,让他躺在院子里的血泊中,一哄而去。透过乌云可以看到稀疏的星星闪着寒光,一股猛烈的风卷起一片尘埃。
大门、房门和护门板都钉死了:房子好像没人居住似的。
尤里安预感到了暴动,没有躲到任何地方去,但几乎没有让士兵们见到,而是忙于占卜。等待奇迹和显灵,一直等了两天两夜。
他穿着毕达哥拉斯式的白色长衣,手里端着油灯,沿着一个很狭窄的楼梯往宫殿塔楼的最高处攀登。塔楼顶上站着一位波斯魔法师,他戴着尖顶毡帽,在观测星辰,这是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的助手,是他派到尤里安这里来的,名叫诺戈达列斯,正是他当年在阿尔格尔山脚下西拉克斯的小酒店里为统兵官斯库迪洛预言了他的命运。
“怎么样?”尤里安望着漆黑的天穹,很不安地问道。
“看不见,”诺戈达列斯说,“云彩给遮住了。”
尤里安用手做一个很不耐烦的动作:
“没有任何预兆!仿佛天和地商议好了……”
飞起一只蝙蝠。
“看看,看看,你也许能根据它的飞翔做出某种预见。”
蝙蝠冰冷的神秘的翅膀几乎触到尤里安的脸上,然后消失不见了。
“你感到亲切的灵魂,”诺戈达列斯小声说道,“记住:今天夜间应该发生一起伟大的事件……”
传来军队的呼喊声,不很清晰,因为风太大。
“你如果还能知道什么事,就过来。”尤里安说,然后到下面藏书室去了。
他在大厅里来回踱着,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脚步很快,但不均匀。有时机警地停下来。他觉得有个人跟在他的身后,一股超自然的奇怪的寒气在黑暗中向他的后脑勺袭来。他迅速地转过身体——不见一个人影,只是沸腾的血液在他的太阳穴里嘣嘣直跳。他重新开始走起来——他又觉得有个人快速地向他耳语,可是并没有听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话。进来一个仆人,禀报说,一个老头从雅典来,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拜见他。尤里安高兴得叫了起来,马上前去迎接。他认为这是马克西穆斯,可是错了:那是厄琉西尼亚神秘仪式 1 的大法师,他也焦急地等待着这个人。
“父亲,”副帝说,“救救我吧!我应该知道诸神的意志。快走!全都准备好了。”
就在这一瞬间,皇宫的周围,响起了军队在近处的呼喊声,如同雷鸣,震耳欲聋,经年的砖墙被震动了。
宫廷持盾兵队长跑进来,惊恐得脸色煞白:
“暴动了!士兵们在拆毁大门!”
尤里安做了一个命令的手势。
“别害怕!等以后再说,等以后再说!不准放任何人进来!……”
他抓起大法师的手,领着他下了一个很陡的楼梯,进入地窖,随手把沉重的铁门关好。
地窖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火把的火焰映照在太阳神赫利俄斯-密多罗的银像上;香炉里点着神香,各种容器里分别盛着祭神用的圣水、葡萄酒、蜂蜜,还有撒在祭品上的面粉和食盐;笼子里装着占卜用的各种禽鸟,鸭子、鸽子、母鸡、鹅、鹰;一只羊羔被捆绑着,咩咩地叫。
“快点儿!快点儿!我应该知道诸神的意志。”尤里安催促大法师,递给他一把很锋利的刀。
老头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做完了祈祷和祭神的仪式。他宰了一只羊羔,把一部分肉和油脂放进祭坛的炭火里,嘴里念着神秘的咒语,开始观察内脏;用熟练的手翻出肝、心、肺,翻过来调过去地进行研究。“强者将被推翻,”大法师指着羊羔还热乎的心脏说道,“可怕的死亡……”
“谁?”尤里安问道,“是我还是他?”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副帝,”老头说,“你不必着忙。你今天夜里不要做出任何决定。等到明天早晨:预兆很可疑——甚至……”
他没有说完,又着手另一个祭物——鹅,然后又是鹰。从地面上传来人们的嘈杂声,好像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响起了铁棍撞击铁门的声音。尤里安什么都没有听见,贪婪好奇地观察着血淋淋的内脏:指望在杀死的母鸡的肾脏中看到诸神显示的秘密。
老法师摇着头,重复道:
“你不要做出任何决定:诸神沉默不言。”
“这是什么意思?”副帝不满地说,“可找到沉默的时候了!”
诺戈达列斯走进来,一副庄严的神情:
“尤里安,你高兴吧!今夜将决定你的命运。快点儿,要大胆——否则就晚了……”
魔法师看了看法师,法师看了看魔法师。
“当心!”厄琉西尼亚神秘仪式的法师皱着眉头说。
尤里安站在他们二人中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如何是好。两个占卜官都高深莫测;他们彼此嫉妒。
“怎么办?怎么办呀?”尤里安说。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高兴起来:
“等一等,我有一本古代的巫书——《论占卜中的矛盾》。不妨查一查!”
他向上面藏书室跑去。他在一条通道里遇到了多罗西斯主教,只见他身穿法衣,手里拿着十字架和圣餐。
“这是干什么?”尤里安问道,不由自主地躲开。
“给娘娘领圣餐,她要死了,副帝。”
多罗西斯盯着尤里安那件毕达哥拉斯式的衣服、他那张苍白的脸、发红的眼睛和血淋淋的双手。
“娘娘,”主教继续说,“希望临死之前能够见见你。”
“好,好——但现在不行,等以后吧……噢,上帝呀!又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这种时候,她所做的一切多不合时宜!……”
他跑进藏书室,开始翻弄积满灰尘的羊皮纸卷。突然,他听见有个人伏在他的耳朵上清晰地小声说:“要大胆!要大胆!要大胆!”
“马克西穆斯!是你!”尤里安惊叫道,转过身来。
屋子里一片漆黑,不见一个人影。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把手放到心口上,前额上浸出了冷汗。
“这就是我所期待的,”尤里安说,“这是他的声音。现在可以走啦。一切都结束了。命运之签已经抛出了。”
铁门倒塌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士兵们冲进中庭。传来人群的号叫声,很像野兽的嗥叫,脚步声无数。透过护窗板的缝隙可以看见火把血红色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不能迟疑了。尤里安脱下毕达哥拉斯式的白衣,穿上铠甲,戴上头盔,披上御坡风,系上佩剑,向通往房门的主楼梯跑去,开了门,突然出现在军队面前,脸色庄严而又明朗。
所有的疑虑全都一扫而光:他的意志在行动中坚定了;他有生以来还从未曾体验过这样的内在力量、精神上的明确性和清醒。人群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那张苍白的脸显得威严和可畏。他做了一个手势——全体静下来。
他发表讲话:让战士们保持安静,让他们相信他不会抛弃他们,绝不允许把他们派到异国他乡去,他将恳求自己的“值得热爱的哥哥”君士坦提乌斯皇帝。
“让君士坦提乌斯滚蛋吧!”战士们异口同声地打断了他的话。“让弑兄者滚蛋!你才是皇帝,我们不要别的皇帝。光荣属于战无不胜的奥古斯都·尤里安!”
他巧妙地扮演着一个大吃一惊的、甚至被吓坏了的人的角色:垂下目光,把脸转向一旁,向前伸出双手,掌心向上,仿佛是在推卸这种罪恶的赏赐,要躲开它。叫喊声更大了。
“你们在干什么?”尤里安装作惊恐的样子喊道,“你们不要毁了自己,也不要毁了我!难道你们以为我会背叛圣上吗?”
“他杀了你的父亲,他杀了加卢斯!”战士们喊道。
“静一静,静一静!”他挥动着双手,突然跑下台阶,向人群奔去,“你们还都不知道吧?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发了誓……”
尤里安的每个动作都是狡猾的、假装出来的。战士们把他围拢起来。他抽出剑,举起来,对准自己的胸膛。
“最英勇的儿郎们!我身为副帝,宁肯死也不愿意背叛……”
他们抓住他的手,强行夺下剑。许多人跪在他的脚下,抱住他的双腿,眼含热泪地把胸膛触在剑锋上。
“我们要死,”他们喊道,“为你而死!”
另外一些人把双手向他伸来,哀求地号叫着:
“可怜可怜我们吧,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的父亲!”
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兵跪在地上,抓住首领的手好像是要亲吻,把他的手指放到自己的嘴上,让他摸摸没有牙齿的嘴唇。他们讲了难以形容的疲劳、为了长期服役而遭受的难以想象的困苦;许多人脱下衣服,让他看看他们那些衰老的身躯、战斗中受伤的疤痕、皮鞭在脊背上留下的可怕伤疤。
“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你就当我们的奥古斯都吧!”
尤里安的眼睛里涌出真挚的泪水:他爱这些粗糙面孔、他所熟悉的兵营里的空气、这种无拘无束的兴奋,他从中感觉到了力量。暴动是可怕的——他根据特殊的特征发现了这一点:战士们没有相互打断话头,而是异口同声地高喊,仿佛事先商议好了似的,喊完之后又一齐停下——一会儿是高声齐喊,一会儿是全体沉默。
他最后仿佛并不心甘情愿,而是迫于压力,小声说道:
“亲爱的弟兄们!我的孩子们!你们看——我不管是活还是死,都是你们的;我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拒绝你们……”
“给他加冕,给他戴上皇冠!”他们胜利地高喊道。
可是并没有皇冠。机灵的斯特隆比克建议道:
“请奥古斯都下令让人拿来娘娘的一串珍珠项链。”
尤里安不赞成,说女人的装饰品不配当皇冠,而且对于新的统治者来说是个不吉利的标志。
战士们没有停止吵闹:他们一定要看见自己选出来的人头上有光辉灿烂的装饰物,这样才能相信他是皇帝。
一个鲁莽的军士从战马身上拽下一个铜扣护胸,建议用它当皇冠给奥古斯都戴在头上。
大家不喜欢这个东西:护胸的皮垫散发着马汗的气味。
大家焦急地寻找别的装饰品。威猛军团的旗手阿拉加里从脖子上拽下一条鳞状铜链,这是他获得这一称号时得到的奖赏。在尤里安的头上缠了两圈:这条铜链便使他成了罗马皇帝。
“到盾牌上去,到盾牌上去!”
阿拉加里让他站到一个圆形盾牌上,千百只手把皇帝抬了起来。他看见了戴着铜盔的头的海洋,听见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声:
“奥古斯都·尤里安,神圣的奥古斯都万岁!divus augustus!”
他觉得,命运之神的意志实现了。
火把熄灭了。东方现出鱼肚白。宫殿塔楼粗糙的砖墙黑得很阴森。只有一个窗户亮着灯。尤里安猜到了,这是他濒临死亡的妻子海伦娜的那个房间的窗户。
拂晓的时候,疲倦了的军队静了下来,他前去看她。
已经迟了。死者躺在狭窄的处女的床上。大家都跪在地上。她紧闭着双唇。枯槁的修女遗体散发着贞洁的寒气。尤里安没有感到良心有愧,只是怀着浓厚的好奇心,看了看妻子那张安详的苍白的脸,心里暗自想道:“她为什么临死之前希望见到我?她想要对我说些什么,她能够说些什么?”
注解:
1厄琉西尼亚神秘仪式,古希腊祭祀得墨忒耳和佩耳塞福涅的庆祝活动,分春秋两次,用动物进行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