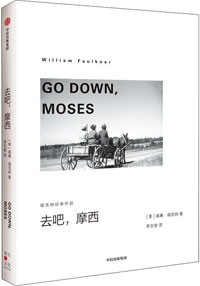阴历六月十六,撤退以来第一次宿营。
军队拒绝继续前进。皇帝苦苦哀求,规劝开导,威胁恫吓,全都无济于事。克尔特人、斯基泰人、罗马人、基督徒和多神教徒、胆小者和勇敢者——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用一句话来回答:“回去,回去!”
众将领暗自幸灾乐祸,埃特鲁里亚占卜官明显地得意起来。烧掉战船以后,群情激愤,纷纷造反。不仅加利利教徒,就连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者们也都相信,诅咒将要落到皇帝的头上,复仇三女神欧墨尼得斯不会饶过他。每当他巡视兵营的时候,大家都停止谈话,所有的人都怀着恐惧的心情躲到一边去。
《神谕书》和《启示录》,埃特鲁里亚占卜官和基督教的预言家,诸神和天使联合起来,好使叛教者遭到毁灭。
于是,皇帝终于宣布说,他要率领他们穿过科杜埃纳省,朝着富饶的希利奥科姆方向返回祖国。采取这样一条撤退路线,最低限度有希望与普罗科庇乌斯和塞巴斯蒂安的军队会师。尤里安安慰自己,心想,他还没有走出波斯的国境,因此有可能与沙普尔王的主力遭遇并且取得胜利,从而纠正一切过失。
可是波斯人再也没有出现。他们希望在决战之前首先让罗马军队把力量消耗殆尽,因此他们把已经成熟的麦田、村落里的粮仓和草料场全都烧光。
士兵们走在死气沉沉的荒原里,只见不久以前的大火还在冒烟。开始了饥馑。
波斯人为了加重灾难,破坏了水渠的堤坝,焚烧过的土地又遭到水淹。亚美尼亚高山上的积雪在夏天融化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来势凶猛,竟使河水暴涨,漫出河岸,这又帮了波斯人的大忙。
在六月骄阳的烤灼下,水迅速干涸了。还残留着大火的余温的土地上,处处是水洼和温吞吞黏糊糊的黑色稀泥。每到晚上,潮湿的灰烬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水气和甜腻腻的焦煳气味,一切——空气、水,甚至士兵们的食物和衣服,全都沾上了这种气味。腐烂的沼泽地里,各种昆虫——白蛉子、毒胡蜂、牛虻和苍蝇,黑压压一片,在驮畜的头上盘旋,叮咬着军士们汗水混合着泥土的皮肤。不分白天和黑夜,不停地发出嗡嗡声,使人昏昏欲睡。马发狂了,牛挣脱了车轭,撞翻了辎重车。士兵们经过艰难的跋涉之后得不到休息,甚至躲在帐篷里都逃脱不掉昆虫的叮咬,昆虫无孔不入,必须从头到脚裹上让人气闷的被子,才能入睡。挨了一种粪黄色的小蝇子叮咬之后,便会红肿、起泡,起初发痒,后来疼痛,最后则发炎溃烂,变成可怕的脓疮。
最近几天,太阳没有露脸。天空覆盖着闷热的白色云层,它们那停滞不动的光亮看起来比阳光还刺眼。天幕低垂,让人感到气闷和压抑,好像是热气腾腾的澡堂里的天花板。
士兵们一个个消瘦了,虚弱了,拖着无力的脚步,垂头丧气地走着,走在无情地低垂着的像石灰一样雪白的天空和烧成炭的黑色大地之间。
他们觉得,那个被上帝所摈弃的人就是反基督,他故意把他们带到这个可恶的地方,想要毁灭他们。有的人发牢骚,骂他们的头儿,但语无伦次,好像是在说梦呓。也有些人悄悄地祈祷和哭泣,像是患病的孩子,向伙伴们乞讨一小块面包,乞讨一口酒。有些人由于体衰力竭而死在路上。
皇帝下令把为他以及他的近臣储备的最后的给养分发给饥饿的士兵。他本人只喝稀溜溜的面汤,外加一小块油脂——哪怕是最不挑剔的士兵对这种食品也都不屑一顾。
由于竭力克制,他一直感到亢奋,身体奇怪地轻松,仿佛是能够飞翔,这一点支撑着他,使他的力气增加了十倍。他尽量不去想将会有什么结果。败归安条克或塔尔苏斯,遭到加利利教徒的耻笑和奚落——只要一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无法忍受。
那天夜里,士兵们正在休息。北风驱散了昆虫。从皇帝最后的储备中拿出来的奶油、面粉和葡萄酒,多多少少缓和了辘辘的饥肠。兵营已经进入梦乡。
尤里安返回帐篷。
近来,他尽量少睡眠,只是天亮前才眯一小觉。一旦睡得太熟,必定会惊醒,出一身冷汗,他需要意志力量来压下这种惊恐。
他走进帐篷,用铁镊子剪掉挂在帐篷中央的铜灯上的灯花。周围散乱地堆着行军书库的羊皮纸卷,其中有一部《福音书》。他准备进行写作:哲学著作《反加利利教徒》,这是他所喜欢的夜间工作,两个半月之前出发远征时即已开始。
他背朝着帐篷的门坐着,重读手稿,突然听见簌簌声。他回过头,惊叫一声跳了起来:他觉得是看见了幽灵。门口站着一个少年,只见他穿着一件很寒酸的深色驼毛长袍,肩上披着一张落满灰尘的羊皮——这是埃及隐修士常用的服饰,赤脚穿着用棕榈叶编的鞋。
皇帝只是看着和等待着,而不能说出一句话来。一片寂静,这是夜深人静的时刻才有的那种寂静。
“你可记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你可记得,尤里安,你曾到修道院去找过我吗?当时我把你赶走了,可是我却不能忘记,因为我们二人永远是亲密的……”
少年从头上摘下深色的修士盖头,尤里安看见了金发,认出了阿尔西诺亚。
“你从何处来?你怎么到了这里?为什么要这身打扮?”
他仍然惊魂未定——这会不会是幽灵,她会不会跟她突如其来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尔西诺亚用了不多的几句话向他讲述了他们二人分手以后发生的事。——她离开了自己的保护人戈腾西乌斯,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分给了穷人,她曾长期生活在加利利教隐修士中间,那是在马雷奥提斯湖以南,利比亚光秃秃的群山之间的尼特里亚和斯凯提亚沙漠里。有少年尤文廷陪伴着她,他是盲长老迪迪穆斯的学生。他们二人走访了许多伟大的苦行僧。
“那又怎么样?”尤里安问道,他心中仍然不无惊惧,“怎么,姑娘?你在他们那里可曾找到了你所寻求的?”
她摇摇头,哀伤地说道:
“没有。只有一些闪念,只有一些暗示和预兆……”
“说吧,全都说出来!”皇帝催促她,他的眼睛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我能说吗?”她慢腾腾地开始了,“你看,我的朋友:我在他们那里寻找自由,可是那里并没有自由……”
“是啊,是啊!不是吗?”尤里安越来越得意了,“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阿尔西诺亚。你可记得?”
她坐到铺着豹皮的行军椅子上,继续心平气和地说起来,脸上仍然带着以前那种忧伤的笑容。他兴奋而贪婪地听着,不放过每一个字。
“请问,你是怎样离开这些不幸者的?”尤里安问道。
“我也曾受到过诱惑,”她回答道,“有一次,在沙漠的乱石中间,我发现一块洁白的大理石碎片,我拾了起来,长时间地欣赏着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突然想起了雅典,想起了自己的时代,想起了艺术,也想起了你,仿佛是如梦初醒——于是我决定重新回到人世间来,作为一个艺术家而生活,作为一个艺术家而死去,上帝就是把我造就成这样一个人的。这时,迪迪穆斯长老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梦,说我让你跟那个加利利人和解了……”
“跟那个加利利人?”尤里安轻轻重复着,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眼睛失去了光辉,嘴上的微笑也消失了。
“我想要见到你,”阿尔西诺亚继续说道,“想要知道,你在自己的道路上是否找到了真理,你最后到了何处。我换上男修土的装束;我跟尤文廷教兄一起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乘船来到安条克的塞琉西亚,跟着一个叙利亚人大商队穿过阿帕梅亚、伊皮凡尼亚、埃德萨——最后到了国境线;历经千难万险穿过波斯人所遗弃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我们在离阿布扎特村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你的兵营,那是在泰西封胜利之后。这样,我就到了此地。好了,你的情况如何,尤里安?”
他叹息一声,把头垂到胸前,什么都没有回答。
后来,他皱着眉头,用祈求而又怀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问道:
“你如今也恨他了,阿尔西诺亚?”
“不。为什么呢?”她简单地小声回答道,“难道埃拉多斯的哲人们不是很接近于他所说的吗?那些在荒漠里折磨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人——他们与恭顺的玛丽亚之子却相去甚远。他爱孩子们,也爱自由、饮宴的欢乐和白色的百合花。他爱生活,尤里安。但是我们却离开了他,因此糊涂了,精神上变得忧郁了。他们全都把你叫作叛教者。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叛教者……”
皇帝跪在她的面前,仰起脸来,眼睛里充满了祈求,噙在眼睛里的泪水慢慢地顺着两腮流淌下来。
“不要,不要,”皇帝喃喃地说,“你别说了……为什么呢?……把过去曾经有过的留给我吧……请你不要重新成为我的敌人……”
“不!”她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喊道,“我应该对你说出一切。你听着。我知道,你是爱他的。你别说话,是这样,这就是你的诅咒。你在反对谁呢?他怎么能是你的敌人呢?当你的嘴诅咒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时,你的心却渴望他。当你为反对他的名字而斗争时,你却比那些口口声声离不开‘上帝,上帝’的人更接近他的精神。因此,这才是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并不是他。你为什么比那些加利利教修士更厉害地折磨自己呢?”
尤里安跳起来,脸色煞白,脸形扭曲了,两眼射出凶恶的目光。他喘着粗气,小声说道:
“你滚,给我滚开!我了解你们加利利教徒的鬼把戏……”
阿尔西诺亚惊恐地看着他,觉得他像是一个疯子。
“尤里安,尤里安!你怎么了?难道就因为一个名字?”
可是他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眼睛暗淡无光了,脸变得冷漠了,近乎轻蔑。
“你走吧,阿尔西诺亚。把我说的一切全都忘了吧。你看见了,你我不是同路人。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阴影横在你我之间。你没有弃绝他。不与他为敌的人,不可能是我的朋友。”
她跪在他的面前:
“为什么?为什么?你在干什么呀?你可怜可怜自己吧,暂时还不算晚!回过头来吧,否则你……”
她没有把话说完,可是他却替她说完了,露出高傲的冷笑:
“否则我就得毁灭?由它去好了。我要沿着我的道路走到底,不管这条道路把我引向何处。假如像你所说的,我对待加利利人的学说是不公平的,那么请你回想一下,我吃了他们多少苦头!我的敌人何其多,他们何其卑鄙!有一天,我看见罗马士兵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里发现一头狮子,它遭到一群毒蝇的袭击,毒蝇钻进狮子的嘴里、耳朵里、鼻孔里,不让它呼吸,糊住了它的双眼,于是用自己的毒针慢慢地战胜了狮子的勇猛。我也将会这样毁灭。加利利教徒将会这样战胜罗马恺撒!”
姑娘仍然向他伸出双手,但已经不再说话,不再抱着希望,像是一个朋友向已死的朋友伸出双手一样。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深渊,活着的人是无法越过的……
阴历七月下旬,罗马军队经过在被焚烧过的草原上长久跋涉之后,终于在杜鲁斯小溪深深的河谷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幸免于大火的青草。军士们高兴得难以言表,躺在地上,呼吸着芳香的潮气,把湿润的草茎紧紧贴在满是尘土的脸上,贴在红肿的眼皮上。
紧挨着是一块成熟了的麦田。军士收割了小麦。他们在这个舒适的河谷里休整了三天。第四天早晨,罗马哨兵发现周围山冈上升起一片烟云,或者也可能是尘埃。有人认为这是野驴,这种动物为了防御狮子的袭击,通常都成群结队;也有人认为这是萨拉森人,他们听到泰西封被围的传闻,因而被吸引出来;还有人表示担心,这会不会是沙普尔王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
皇帝下令吹号集合。
各个大队在河岸上布阵,排成规整的圆形防御队列,外圈的士兵举起盾牌,构成一道铜墙铁壁。
烟或者尘埃的帷幕在天边上一直停留到天黑,任何人都猜不透这道帷幕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
夜色漆黑,寂静无声,天上不见一颗闪烁着的星星。
罗马人没有睡觉,他们围着篝火站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