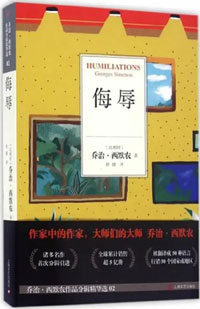克列奥门尼斯:请进,您的仆人在恭候您。
霍拉修:克列奥门尼斯,现在你该怎么说,你这话难道不是虚礼么?
克列奥门尼斯:这是因为你很讲礼节。
霍拉修:那天人们告诉我你在哪里时,我真想亲自去告诉你谁正在找你,并要你随我到寒舍来。
克列奥门尼斯:这实在是太不敢当了。
霍拉修:你知道我是多么从善如流,用不了多一会儿,你准能教会我把礼貌规矩统统扔到一边去。
克列奥门尼斯:你才是我的好老师。
霍拉修:我知道,你会原谅我。你这间书房很漂亮。
克列奥门尼斯:我喜欢它,因为阳光永远照不进它里面。158
霍拉修:这房间真不错!
克列奥门尼斯:你我到里面坐吧,宅中的房间里,数它最凉爽了。
霍拉修:正遂我愿。
克列奥门尼斯:我本希望在这之前便能见到你。你思考得太久了。
霍拉修:只有八天嘛。
克列奥门尼斯:你考虑过我那天对你说的那些新见解了么?
霍拉修:考虑过了。我还认为它并非不可能,因为我相信: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既没有思想意念,也没有任何知识。所以我已经很清楚一点:一切艺术与科学都必定开始于某个人的脑子里,无论现在其起源已经如何为人们遗忘,都是如此。上次离开你之后,我已对礼貌的起源思考过二十次了。一个尚属通达世事的人,若在未开化民族当中发现了彼此掩饰自傲的最初尝试,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场景啊!
克列奥门尼斯:这能使我们知道:使我们惊异的,主要是事物的新颖之处,它们既可能引起我们的反感,也可能获得我们的赞同;而面对熟悉的事物,我们却往往无动于衷,尽管它们最初作为新事物出现时也曾使我们惊异。你现在正转而相信一个真理,而八天以前你却宁可出一百个金币,也不愿去了解它。159
霍拉修:我已经开始相信,我们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惯了一种事物,日后它便不会在我们眼中显得那么荒唐。
克列奥门尼斯:从最幼小的时候起,我们便受到了一种还算不错的教育,它孜孜不倦、不苟不懈地教给我们各种礼节,例如鞠躬、脱帽致意以及其他行为规范。因此,我们甚至在成年时便很少会把有礼貌的举止看作后天习得的东西,很少会把文雅谈吐看作一门学问。在姿势和动作方面,在言谈与写作方面,有上千种东西被叫作天性使然、轻而易举,而它们却给他人和我们自己造成了无限的痛苦。我们知道,那些东西乃是人为技巧的产物。我知道,舞蹈大师的四肢被弄出了何等难看的肿块啊!
霍拉修:昨天上午我静坐沉思,忽然想起你说的一句话,它让我笑了,而我最初听见时并未仔细思索过它。谈到处于幼稚期的民族一旦开始掩饰其骄傲、便有了初步礼节时,你曾说:每天都必须做出新改进,直到其中一些人变得足够厚颜无耻,不但能矢口否认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而且能佯称自己对他人的评价高于对自己的评价。注103160
克列奥门尼斯:可以肯定,那必定是各个地方阿谀之举的先驱。
霍拉修:谈到阿谀谄媚和厚颜无耻时,对世上第一个有脸对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人说“我是您谦卑的仆人”者,你是怎么想的?
克列奥门尼斯:倘若那句话是个新鲜的奉承之辞,我会更想知道轻信它的骄傲者何以如此头脑简单,尽管我也想知道说那话的小人何以如此厚颜无耻。
霍拉修:那句话当然曾是新的。求你告诉我,你认为究竟是脱帽致意更古老,还是“您谦卑的仆人”这个说法更古老?
克列奥门尼斯:两者都既古老又摩登。
霍拉修:我想脱帽致意更古老一些,因为它是自由的象征。
克列奥门尼斯: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说“您的仆人”若尚未实行,第一个脱帽致意的人便不能为人理解。说“您的仆人”若尚未成为一种既定而众所周知的恭维方式,那么,一个人完全可能用脱鞋来表示尊敬,像用脱帽一样。
霍拉修:因此,如你所言,他很可能成为第一个以脱帽表示敬意的人,而不是第一个说“您的仆人”的人。
克列奥门尼斯:到今天为止,脱帽一直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礼貌之辞的无声表现。请注意习俗以及那些既定观念的力量吧。你我都嘲笑这种古老的荒谬之举,都非常肯定一点,即这种做法必定来自最拙劣的阿谀奉承。可是,我们遇到不太亲密的熟人时,却都不会不脱帽致意,都不会不做出这点礼节。不仅如此,我们若不这么做,甚至还会感到很痛苦。但我们却没有理由相信:说您的仆人这句恭维之辞的做法始于身份相等者之间。其实,它最初是阿谀者对君王说的,后来才渐渐被普遍使用。这是因为,身体、四肢的一切谄媚姿势和卑躬屈节,极可能来自对征服者和暴君的奉承。征服者和暴君使人人都害怕他们,一丁点对抗的影子也会使他们惊恐,而使他们最开心的东西,乃是那些俯首帖耳、毫无反抗的姿势。你知道,那些姿势无不具有这种倾向。它们给人安全感,是无言的努力,意在平息和消除征服者和暴君的恐惧与疑虑,即怀疑自己会受到伤害。面带恭顺,磕头,下跪,深深鞠躬,双手贴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两臂相抱,以及一切能表示“我们既不放肆、又不设防”的恭顺姿态,这些都是显示给在高位者的明显标志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仿佛在说:与对他的尊重相比,我们认为自己非常卑微;我们任凭他的摆布,绝无抵抗之念,更谈不上向他进攻。所以,说“您的仆人”和脱帽致意,最初都是对有权得到服从者表示的服从。161-162
霍拉修:经过漫长的时间,它就渐渐变得更为常见,成了一种双方互相致意的礼节。
克列奥门尼斯:我想就是如此,因为我们看到:礼节增加时,致意的最高级形式便成了寻常,于是,向居上位者表示敬意的新形式便被发明出来,取代了旧的。
霍拉修:因此,“阁下”(grace)这个称呼不久前还惟有对我们的国王和王后才能使用,而现在已经容许用它称呼红衣主教和公爵了。
克列奥门尼斯:“殿下”(highness)这个字也是如此。现在不仅对国王的儿子,甚至对国王的孙子都可以使用。
霍拉修:“大人”(lord)这个字的含义中附加的尊贵,在我们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保留得更好。在西班牙、意大利、高地与低地荷兰,几乎对每个人都可以滥用这个字。
克列奥门尼斯:它在法国的命运要好些,因为在那里,“sire”(大人)这个字里包含的尊严毫无损失,惟有对君主才能使用。而在我们这里,它已经成了一个敬称,即可以对国王使用,也可以对鞋匠使用。163
霍拉修:无论时光使这个字的意义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由于它变得日益完美,恭维还是变得愈来愈不那么直截了当了,而它利用人之骄傲的意图,也比从前掩饰得更巧妙了。当面称赞一个人,在古人当中是很普遍的做法。谦逊是尤其要求基督徒具备的一种美德,我想到这一点,便常常捉摸:教会的神甫们何以能受得了布道时会众对他们的喝彩鼓掌,尽管有些神甫反对这样做,但许多神甫却似乎都非常喜欢听到喝彩鼓掌。
克列奥门尼斯:人性总是相同的。喝彩能使那些竭尽全力、吃遍苦头、耗神费力的人重振精神,效果极佳。反对这样做的神甫们,其实是反对滥用它们。
霍拉修:我们时常能听见绝大部分听布道的人大叫:真有智慧啊,妙极啦,再对不过啦,简直是奇迹,太尖锐啦,简直是天才啊!他们也告诉布道者自己是东正教徒,有时还称他们是最棒的福音传播者。那场景实在很是古怪。
克列奥门尼斯:当一句话结束时,使用这些词句或许还算过得去;但大多数人却一再地高声重复它们。他们拍手跺脚,其声嘈杂,无论布道讲到什么地方,随时都会被这噪音搅扰,因此,他们听到的布道内容,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尽管如此,一些神甫还是承认:这些喝彩声的确使他们非常受用,并且能够安抚人类的弱点。164
霍拉修:现在,人们在教堂的行为要规矩多了。
克列奥门尼斯:旧西方世界的异教信仰几乎消失之后,基督教徒的宗教热忱便比以前大为减少了,因为以前有很多反基督教的异教徒。在废止那种时尚方面,宗教热情的匮乏发挥了很大作用。
霍拉修:可是,无论那是不是一种时尚,它想必总是很令人厌恶。
克列奥门尼斯:当今,我们在一些剧场里也能看到观众的反复赞叹、鼓掌、跺脚,以及喝彩的最夸张表现。你想到过么:受人喜爱的演员是否会讨厌这些东西?最高级的精英人士是否讨厌俗众对他们的欢呼声和士兵们刺耳的喊叫声?
霍拉修:我认识一些王公贵族,他们非常讨厌这些东西。
克列奥门尼斯:那是因为他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太多了;不过,他们最初可绝不会讨厌它们。操纵一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其结构的承受力。有限的动物不能领受无限的快乐,因此我们才懂得:快乐若超出其恰当界限便会变为痛苦。不过,只要不违反一国的风俗习惯,那么,任何喝彩的喧哗,其持续只要不超过合理时限,便都不会使人不快。我们时常以喝彩表示赞赏;而听到喝彩时,我们也认为十分得体。然而,若是滥饮,再甘甜的美酒也会令人反胃。165
霍拉修:美酒愈甘甜香醇,便愈容易令人感到厌腻,愈不宜恣意滥饮。
克列奥门尼斯:你这个比喻没有错,欢呼喝彩最初会令人陶醉,或许还会继续给人八九分钟无法言喻的快乐。然而,同样的欢呼喝彩若总在持续,全无间断,那么,用不了三个钟头,它便会使人渐次感到中度愉快,无动于衷,大倒胃口,心烦气躁,甚至因厌恶而痛苦。
霍拉修:声音当中必定包含着巨大的魔力,因而能对我们产生如此不同的影响。我们时常会看到这些影响。
克列奥门尼斯:我们从欢呼喝彩中获得的快乐并非来自听觉,而是来自我们对喝彩起因的看法,即对这些声音的起因、即对他人的赞许的看法。在意大利所有的剧院里,你都可以听到:当全体观众都要求安静和集中注意力时,那就是在用约定俗成的方式表示善意与赞许,而他们此时发出的声音很接近我们的嘘声,与我们的嘘声几乎毫无区别,而嘘声却是我们表示厌恶和轻蔑的最鲜明标志。毫无疑问,对库佐尼来说,更悦耳的是对福斯蒂娜喝倒彩的尖叫声,而不是她听到的这个得意洋洋的对手技艺最高超的声音注104。166
霍拉修:那实在太令人厌恶了!
克列奥门尼斯:土耳其人用绝对的肃静表示对他们君主的尊敬。土耳其后宫严格执行这种礼仪,而愈接近土耳其苏丹的寝宫,这个礼仪就执行得愈严。
霍拉修:这种肃静,当然是满足骄傲之心的一种更文雅的方式。
克列奥门尼斯:这一切都取决于时尚和风俗。
霍拉修:可是,为满足一个人的骄傲而提供的无声礼物,即使没有丧失听觉,也照样可以为他享用;而欢呼喝彩却做不到这点。
克列奥门尼斯:在满足骄傲之情上,这太微不足道了。我们从放纵欲望中获得的快乐,要超过其他任何快乐。
霍拉修:可是,肃静所表达的尊崇与敬重,却比喧哗更强烈,更深刻。
克列奥门尼斯:它对平息怠惰者的骄傲很有效,但活跃进取者却喜欢唤起骄傲之情,即使它得到了满足,也依然让它保持活跃,并且无疑会比前者更赞成喝彩喧哗。然而,对这两种方式,我并不打算做出臧否,而宁可全都予以赞同。为了激励人们行为高尚,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习惯于喝彩喧哗,并且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奥斯曼帝国的人则素以肃静去满足骄傲,这使他们成了惟命是从、忠实恭顺的奴仆,而这正符合其君主的要求。在一人大权独揽的情况下,沉默或许更有效果;而在臣民享有一定自由的情况下,喝彩喧哗或许更有效果。只要善加理解,善加利用,这两种方式都是迎合骄傲的有效手段。我认识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习惯于战场上的呐喊,响亮的喝彩鼓掌能使他快乐万分;但他有一次却对自己的男管家大发雷霆,因为后者收拾餐具时弄出了一点点响声。167
霍拉修:那天,我的一位老姑妈解雇了一个极聪明的下人,因为他没有踮起脚尖走路。我也必须承认:男仆的沉重脚步声,仆人们一切不合礼仪的大呼小叫,都会使我感到极为厌恶,尽管此前我从未思考过那是因为什么。你我上次交谈时,你描述了自赏的种种表征,讲到了未开化者的自赏会有哪些表现,其中你提到了笑。我知道,笑是我们人类独具的特点。求你告诉我:你是否认为笑也来自骄傲呢?
克列奥门尼斯:霍布斯就赞同那个观点注105,并且,笑大多来自骄傲。不过,这个假说仍旧无法解释一些现象。所以我宁可说:笑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当我们不明原因地感到快乐时,自然就会笑。我们若感到自己的骄傲得到了满足,若听见或看见自己欣赏或赞同的事物,若放纵了其他任何激情或欲望,而使我们高兴的原因又显得正当而有价值,我们便不仅仅会发笑了。但是,倘若事物或行为非常古怪,越出了常轨,又碰巧使我们高兴,而我们又说不出其原因何在,它们通常也会使我们发笑。168
霍拉修:我宁可相信你的见解就是霍布斯的观点,因为使我们发笑的事物,大多都会使他人感到多少有几分羞愧,使他人感到不自在,或是会伤及他人。
克列奥门尼斯:可是,你又怎么看待呵痒呢?连又聋又瞎的婴儿也会因被呵痒而笑。
霍拉修:你能用你的理论来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么?
克列奥门尼斯:我对自己的解释并不满意,但我会尽量向你解释。经验告诉我们:一般地说,皮肤愈光滑,愈柔软,愈敏感,人就愈容易被搔痒。我们也知道:用粗糙、尖利和坚硬的东西去接触皮肤,我们甚至在感到疼痛以前就会感到不快;相反,若用柔软光滑的东西去接触皮肤,则不但不会惹人厌恶,反而会使人愉快。轻柔的接触会同时影响到几根神经,其中每一根都会产生舒适感,因此便可能造成一种混合快感,而那便是笑的契机。169
霍拉修:但是,你何以认为自发的快感中存在着无意识的动作呢?
克列奥门尼斯:无论我们自称自己形成意念时的行动多么自由,那些意念对身体的影响却不受人的意志的支配。与笑最直接对立的,莫过于不悦了。不悦使额头产生皱纹,使双眉紧蹙,使嘴唇紧闭。而笑则截然相反,你知道,exporrigere frontem 注106就是拉丁语里表示“愉快”的短语。人们呼气时,胸腹部肌肉会向内牵拉,横膈膜则被拉到高于平时的位置。而用力吸气时,我们仿佛在努力挤压心脏(尽管不会奏效),用那种挤压的姿势吸入尽可能多的空气。我们呼气时也像吸气时一样用力,吸气时使用的所有肌肉突然同时放松。大自然的这种设计,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我保护的劳作,那劳作乃是大自然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能叫出声音、能因苦恼、疼痛以及危险迫近而抱怨的动物,其动作是何等下意识啊!在巨大的痛苦中,大自然所做的种种努力非常剧烈,乃至能使挫败天性,她吩咐我们用声音将真实感觉隐藏起来,我们被迫撅起嘴巴,或者深深地吸气,咬着嘴唇,或让双唇紧闭,用最有效的办法阻止气息呼出。我们因悲痛而叹,因欢乐而笑。笑时给呼吸稍加压力,而在其他任何时候,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出现。所有外部肌肉和体内的一切都很松弛,似乎除了笑的痉挛性振动传达给它们的运动之外,全无其他任何运动。170
霍拉修:我见过有些人会笑得耗尽气力。
克列奥门尼斯:我们看到:叹气时这一切情况是何等截然相反!疼痛或深重的悲哀使我们放声痛哭时,我们的嘴巴就咧成了圆形,或至少是椭圆形,双唇突出,互不相碰,舌头缩进。因此,各个民族的人在惊叹或叫喊时才都发出“啊”(oh)的声音!171
霍拉修:为什么呢?求你解释一下吧。
克列奥门尼斯:因为当嘴巴、嘴唇及舌头保持这种姿势的时候,它们既发不出其他元音,也根本发不出任何辅音。笑的时候,嘴唇回收,嘴巴咧得最宽。
霍拉修:我认为你不该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哭泣的时候情形也是如此,而哭泣无疑是悲哀的标志。
克列奥门尼斯:人在极度痛苦时,心脏承受着极大压力;人们往往极力抗拒焦虑,少数人会因焦虑而哭泣。不过,人们哭泣却可以减轻压力,并能使压力显著缓解,因为人在哭泣时会解除抵抗。悲痛的哭泣并不算是悲哀的标志,因为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再也无法继续克制自己的悲哀了。因此,哭泣才不被看作男子汉的行为,因为它似乎表明我们已经丧失了所有力量,是对悲哀的屈服。然而,在成年人,哭泣这个动作本身却并非悲痛所独有,人们高兴时也会哭泣。有些人虽然在巨大的悲痛中表现得极为坚强,在最大的不幸中也绝不哭泣,却会在观看一出动人戏剧的场景时由衷地哭泣。有些人很容易对一种事物激动不已,另一些人则更容易受另一种事物的感动。不过,无论使我们大受感动的是什么事物,它都会征服我们的头脑,促使我们哭泣,因而成为哭泣的无意识起因。所以说,除了悲痛、欢乐和怜悯,其他一些与我们毫不相关的事物也会影响我们,例如:讲述惊人的事件,上天对美德的突然照拂,英雄事迹,慈善之举,恋爱,友谊,面对巨大危难,或者听到、读到人类的高尚思想与情操。这些事物若是突然传达给我们,而传达的方式为我们所悦纳,又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并被表达得栩栩如生,就更容易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还看到:最容易因这些毫不相关的起因而洒泪的,是那些富于心智、心有灵犀的人,而其中那些最仁厚、最慷慨和最率真者,则最容易洒泪。相反,愚钝者、残忍者、自私者及工于心计者,则极少被那些事物所打动。因此,真正的哭泣向来都是一种真切而无意识的标志,它表明某种事物打动并征服了心智,无论那是什么事物。我们也发现:外界的暴力,例如疾风、浓烟、洋葱的臭味,以及其他挥发性的刺激气味,等等,都会影响人体泪腺导管及腺体暴露的外围神经,于是,突然肿胀与精神压迫便会作用于内部组织。在种类无限、构造不同的有生命动物身上,上帝的智慧体现得最为显著。这些动物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出于独具匠心的设计,都能最精确地适用于不同的既定目的。人体首先是一件最令人惊叹的艺术杰作。解剖学家大概完全通晓所有的骨骼、韧带、肌肉和肌腱,并且能非常准确地分解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膈膜。同样,博物学家也可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人体的内部运作,研究健康与疾病的不同表征。他们都会赞叹人体这台奇妙地机器。但是,若不精通几何学和力学,任何人都不会领悟到那工艺本身有何等精巧,何等高妙,何等美丽;即使对那些他能见到的人体器官,也是如此。172-173
霍拉修:数学被引入医学到底有多久了?我听说,医学这门技艺正是借助数学才具备了高度的确定性。
克列奥门尼斯:你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若指的是治病的技艺,那我便要说:数学与医术从未有过任何牵连,也不可能有任何牵连。人体结构与人体运动大概能从力学的角度加以说明,而一切体液都服从于流体静力学规律(laws of hydrostaticks)。然而,我们若想发现无限远离视线的、全然不知其形状及大小的事物,数学的任何部分都毫无帮助。医生也和其他人一样,对不同疗效及性状的物质的药理及成分一无所知,对用做草药的物质的汁液、因而连同用它们做成的一切药物,也都一无所知。再没有比医术更缺乏确定性的技艺了。在医术中,即使最有价值的知识也无不来自观察,并只能来自观察。有才能、注重实用的人若研究医术,惟有经过长期而审慎的体验,才可能具备那些知识。但是,说数学帮助了医术,或者说数学在治病方面有用,这却是个欺骗,如同教友派的文章、卖艺人的帮手一样使人误入歧途。174
霍拉修:可是,骨骼、肌肉以及人体一些更显眼的部分都具备了非常高超的技能,因此,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体中那些我们无法感知的部分也生就了同样高超的技能么?
克列奥门尼斯: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显微镜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而我几乎不会认为:大自然竟然会在我们无法跟踪到她的地方停止运作。我相信:我们思想和心思的好恶对人体某些部分的影响,要比我们迄今所发现的更实在,更下意识。在它们对眼睛和面部肌肉的显著影响当中,有意识成分必定显现得最少,因此我才提出以上那个见解。与男人们在一起时,我们处于警戒状态,而往往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我们嘴唇闭合,下腭合拢,嘴部肌肉略微绷紧,脸的其余部分始终保持在原位。你若带着这副模样走进另一个房间,见到一位温存亲切、举止从容的年轻美女,那么,不等你想到,你的表情就立即会不可思议地产生变化。你还未意识到自己脸上有了变化,你的表情就早已是另一副模样了。此刻看到你的人都会发现:与方才相比,你表情中的温柔成分更多,严厉的成分更少了。我们让下颚下垂的时候,嘴巴便会略微张开。这时,我们若茫然地望着前方,并不特别注意观看什么目标,换言之,我们若是让面部松弛,不给面部肌肉施加任何压力,那么,我们的面容便可能非常接近自然状态。婴儿尚未学会吞咽唾液时,嘴巴通常都是张开的,并总是淌口水。婴儿尚未具备智力、头脑尚处于混沌状态时,其面部肌肉其实是松弛的,其下颚是下垂的,其嘴唇也是放松的。至少,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婴儿脸上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比后来要多。人到耄耋之年,智力衰退,这些现象便会再度出现。此外,在绝大多数痴呆者脸上,只要他们活着,便始终都能观察到这些现象。因此,一个人的行为若非常愚蠢,或说起话来如同天生的傻瓜,我们会说他“wants a slabbering-bibb”(关不住口水)注107。想到这一切,再想到世上最易动怒的是呆子,最不受骄傲支配的也是呆子,我便要问:我们面部那种体面表情里,是否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自赏呢?这种自赏下意识地影响着我们,并且仿佛在帮助我们。175-176
霍拉修:我无法解答你。我十分清楚的只是,关于人类下意识机制的这些推测,使我发现自己的有关知识甚为贫乏,我实在不明白,你我何以会谈到了这个话题。
克列奥门尼斯:你要探究人类爱笑的根源,而谁都无法说明爱笑的原因;即使稍带确凿成分的原因,也无法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猜度,所以,人们除了从中得到早已形成的种种偏见之外,得不出任何结论。然而,我为你提供这些不成熟的思想,却意在使你领悟大自然的作品是何等神秘莫测。换句话说,大自然的作品随处可见,无不蕴含着显而易见的力量,而人类的智能却无法领会。不倦的观察、审慎的体验和以归纳的事实为依据的论证,以此获得的有用知识,要比依靠直接谈论终极原因、根据先验前提进行推理的傲慢尝试获得的更多。即使对大自然的时钟机构一无所知,并从未深入其内部,也能依靠洞察力发现其运动的原因,我不相信世上哪个人具备这样的睿智。但任何能力中常者,却肯定都能仅仅依靠外部的观察而看出:大自然的时钟机构万分准确,与时间同步,而这来自某种无形的奇妙工艺的精确性;其指针的运动,无论停留在与之相应的哪个数字上,其最初起因都是时钟内部某种东西的首先运动。同样,我们还可以断肯定:思想对身体的影响非常显著,因此,它便能通过联系而产生一些动作,因而那些动作是下意识的。不过,这种操作所使用的那部分身体器官和手段,却是我们的感官远远无法感知的。这些动作具有异常惊人的迅速性,我们的能力永远无法察觉它们。177
霍拉修:可是,灵魂的作用不正是思考么?它与下意识机制有什么关系呢?178
克列奥门尼斯:不能说人体内的灵魂的作用就是思考;这就像不能说建筑师的作用就是建造房屋一样,因为造房子的是木工和泥瓦匠等人,而建筑师则用粉笔画线并监督施工。
霍拉修:你认为,灵魂更直接地寄寓在大脑的哪个部分?换言之,你是否认为灵魂分散在整个大脑中?
克列奥门尼斯:我对此所知道的,已经全对你说了。
霍拉修:我清晰地感到:思考的运作乃是一种劳作,但它至少是我头脑里的某种运作,而不在我的小腿或胳膊里。请告诉我:我们从大脑的解剖学那里得到了哪些真知灼见呢?
克列奥门尼斯:在有关大脑的知识里,没有任何先验的东西。最高明的解剖学家的知识,并不比屠夫学徒的更多。我们可能赞叹大脑硬膜和脑脊软膜奇妙地一致,赞叹包围着大脑的血管及动脉的交织密网,可是,一旦把它们切开,我们便只能看到数对神经及神经根,只能观察到一些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腺体,而它们与大脑质地不同,这一眼便能看得清清楚楚。最好的博物学家若注意到了这些,并且用不同名称把它们区分开来,其中一些名称并不十分恰当,更谈不上精确,他就必定会意识到:即使在这些较大的可见部分当中,除了神经及血管之外,能用以大致解释大脑运作原因的东西也很少。不过,对于大脑本身的神秘结构以及大脑更为深奥的运作机制,他却一无所知。但是,整个大脑却似乎是一种髓状物质,其中致密地储藏着无数无法看见的细胞,它们按照一种无法想象的次序分布在大脑里,簇集在一起,其种类繁多的曲折盘绕,令人困惑。博物学家或许还会补充说: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庞大储库,人类忠实的感官不断获取无比丰富的意象,并把这些宝藏储存在其中。正是在这个器官中,精力被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然后升华为几乎没有实体的微粒;其中最微小的粒子不是一直在寻找那些保留下来的意象,就是以各种不同方式保存那些意象,穿过那种奇特物质的无数褶皱,不停地完成着那种无法解释的运作,而这种运作的深思熟虑,连最杰出的天才也会为之惊叹叫绝。179
霍拉修:这些推测固然都非常美妙,但什么也证明不了。你说过,大脑物质实在太微小,因此我们对其运作一无所知。可是,光学镜片若有了更大的改进,若能发明一些显微镜,能把对象放大到目前的三四百万倍,那些微粒显然便可以被观察到了,只要那些完成大脑运作的东西哪怕具备一丁点实体即可。而目前,这些微粒还远远不能被你所说的那些感官察觉到。180
克列奥门尼斯:这样的改进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但即使能做到这些改进,我们从解剖学那里得到的帮助依然会很少。动物活着的时候,我们无法见到其大脑,也无法深入到其大脑中进行研究。你就是把一只钟表的主发条拆下来,掏出表芯,只剩钟表外壳,也不可能发现究竟是什么使它运作、指示时间的。我们可以检查钟表的所有齿轮,检查其他每一个属于钟表运动或动作的部分,并或许能找出它们在转动指针方面的用途;但是,这种运作的终极原因却将永远是个谜。
霍拉修:我们体内的主发条就是灵魂,它是非物质的,是不朽的。可是,那些有着与我们类似的大脑、却没有非物质的不朽灵魂的动物,其主发条又是什么呢?你不认为狗和马也会思考么?181
克列奥门尼斯:我相信狗和马会思考,尽管其思考的完善程度远逊于我们人类。
霍拉修:它们体内主管思考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它呢?它们的主发条究竟是什么呢?
克列奥门尼斯:我只能回答你说:那就是生命。
霍拉修:什么是生命?
克列奥门尼斯:人人都懂得这个字的含义,尽管或许谁都不知道生命的本源是什么,而它使人体所有其他部分运动。
霍拉修:对一切已经知道无法了解其究竟的事物,人们的见解一向都是莫衷一是,并且,人人都竭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克列奥门尼斯:若有傻子或者无赖,他们确实会如此。但是,我可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关于大脑运作的议论只是一种推测。你若认为它不合情理,我也只好作罢了。一种事物的本质若没有任何外在表现,你就不要指望能去证明它。动物呼吸停止、血液不再循环时,其体内情况便与其肺脏还在活动、血液及体液还在周身充分运动时大为不同。你见过蒸汽机,你知道,驱动引擎的就是水蒸气注108。动物死后,我们无法看见那些承担大脑运作的飞逝微粒;而当引擎熄火,水也冷却时,我们却依然可以看见引擎里的蒸汽,它们承担着全部运作。尽管如此,若让一个人去看并未工作的引擎,并向他解释引擎的工作原理,他心中又完全理解水经加热能化为蒸汽,却仍不相信那种解释,这还是格外无法令人置信。182
霍拉修:可是,你不认为灵魂是各不相同的么?它们难道都是同样地好或同样地坏么?
克列奥门尼斯:对于物质和运动,至少对于我们使用这两个词时所指的东西,我们有一些尚能为人接受的见解。因此,我们能够形成对有形事物的见解,尽管我们的感官无法把握它们。我们能想象出只有我们肉眼(甚至借助最好的显微镜)能看见的一千分之一大的物质部分;可是,灵魂却完全无法为感官把握;对它未向我们揭示的东西,我们的确切了解实在是少而又少。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基于人们之间的差异,并且完全归因于这种差异,它或者是构造上的差异(即人体稳定结构精确程度的大小),或者是在利用这种构造上的差异。新生儿的大脑是个charte blanche注109,何况,你也曾正确地提到过:我们的意念无不来自我们的感官。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认为:在灵魂的支配下,精力以无法想象的飞快速度,追踪、连接、分离、改变及合成着各种意念,而思维活动就存在于精力在大脑中的这种查找当中。因此,婴儿满月后,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除了喂养和使其不受伤害之外,便是从训练两种最有用的感觉(即视觉与听觉)入手,使他们吸取种种意念,让他们的大脑开始进行这种运作,并通过我们的示范,鼓励他们在思维上模仿我们,而婴儿的思维活动最初是很差的。由此可见,对健康婴儿说话愈多,在他们面前的活动愈纷繁,对他们便愈有益处,至少在婴儿两岁以前是如此。为照料婴儿、使之接受这种早期教育,我宁愿选择一个活泼的年轻村姑,也不选择世上最聪明的年长保姆,因为前者的舌头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刻,她总是围着婴儿转;婴儿醒着的时候,她从不停止逗他开心,从不停止和他玩耍。若负担得起,雇用两至三名这样的村姑会要比只雇一个更好,因为这样一来,她们便可以轮流休息。183
霍拉修:这么说,你是认为儿童从保姆们那些愚蠢的闲聊里获益匪浅了?184
克列奥门尼斯:那闲聊对儿童的益处简直无法估量,既能教会他们思考,也能教会他们说话,其收效比她们虽有闲聊之才却不闲聊更快、更好。她们的任务就是尽量运用那些机能,使婴儿不断忙于和她们周旋,因为这个时期所丧失的良机,永远也无法追回。
霍拉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少记得自己两岁以前的所见所闻。那么,倘若儿童们从未听到过那些闲聊,其损失是什么呢?
克列奥门尼斯:打铁要趁其热且柔软之时,同样,教育儿童要从幼年开始,因为那时他们的全身肌肉、每一根血管、所有的肌体组织都是柔软的,比日后更容易接受轻微印象的影响。在幼儿身上,骨骼大多还是软骨,而大脑本身也比日后柔软得多,呈流体状态。正由于这一点,幼儿才不能像日后那样较好地保留所获意象,他们的大脑物质后来将变得比较坚硬。然而,由于先前获得的意象已经丧失,新印象便会不断接替它们。大脑最初被用作各种口令的记录板,或是一个供操作的采样器。婴儿应当学会的,首先就是自我表现的行为,即练习说话,并养成一个习惯,即储存各种意象,迅速而灵巧地支配已保留意象,以达到既定目的。养成这个习惯的最佳时期,莫过于大脑物质柔顺、各个器官也最灵活而柔顺的时期。因此,只要婴儿全力练习思考和说话,无论他们想什么和说什么,全都毫无害处。在活泼的婴儿身上,我们很早就能从他们的眼睛中发现:即使还做不到,他们也已经在努力地模仿我们;他们的大脑在从事这样的练习,他们尽量尝试着思考,并竭力说出一些单词。从婴儿不连贯的动作上,从他们说出的那些格外荒谬的话语中,我们便可以得知这一点。不过,良好思考中包含的努力,要比清晰讲话中包含的更多一些,因此,良好的思考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185
霍拉修:真怪,你居然谈到了幼儿教育,并且如此重视一种我们极为自然地具备了的事情,它就是思考。对一切人来说,思考都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情。“疾如思想”就是一句成语。不用片刻工夫,一个愚蠢的农夫便能让自己的思想从伦敦转到东京,就像最伟大的智者一样轻而易举,毫不费力。
克列奥门尼斯: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像进行思考时一样,使人们之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别。与我所说的这种差别相比,人们在身高、体型、气力及美貌上的差异简直微不足道。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思考的娴熟自如更有价值,更能清晰地表现于人们身上了。两个人可能具备同等的知识,但其中一个所做的即兴发言,另一个则需要精心准备两个钟头才行。186
霍拉修:我可以肯定,只要知道如何用更少的时间做准备,谁都不会为了一次发言而精心准备上两个钟头。因此,我不知道你根据什么假定这样两个人具备同等的知识。
克列奥门尼斯:知道这个字有两层含义,而你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见到一把小提琴时知道它是小提琴,这与你知道如何演奏它可大不相同。我所说的知识属于前一种。你若从那个意义上去看这个问题,就必定会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无论怎样的钻研,都无法从大脑中取出里面本来没有的东西。假定你用了三分钟想好了一封短信,而另一个人虽然也会写信,并且写得和你一样快,却用了大约一个钟头才想好同样的短信,那么,我便能清楚地看出:那个思维缓慢者的知识和你一样多,至少他没有显示出知识比你少;他获取的那些意象虽然与你相同,他却不能找到它们,或至少是不能像你那么迅速地按照短信的次序把它们配置在一起。两篇同等美妙的习作,无论是散文还是韵文,倘若我们肯定其中一篇是即兴之作,而另一篇是两天劳作的成果,那么,那即兴之作的作者的天赋才能便超过了另一个,尽管我们必定知道这两人的知识一样多。因此你看:作为大脑获得的丰富意象的知识,与作为需要时找出那些意象、使之随时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知识(或称技能),两者是不同的。187
霍拉修:我们知道一个事物,却不能随时想起它,我曾以为这是记忆的过错。
克列奥门尼斯:记忆的过错要对此负一部分责任。不过,有些人博览群书,记忆力也非常好,但对事物的判断力却很差,或很少能准确恰当地谈论事物,或说出来时已经为时太晚。在helluones librorum注110当中有些可怜的书虫,读起书来胃口无边,却食而不化。在大型图书馆里,我们时常可以遇到许多饱学的傻瓜,从这些人的著作看来,他们把知识储存在头脑里,其方式想必十分近似把家具放置在架子上。对他们来说,大脑中储存的珍贵知识犹如重负,而不是一种能带来荣耀的东西!这一切都源自思考机能的一个缺点,一种笨拙,源于缺乏一种才能,即运用既得概念、以争取最佳收益之才。相反,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头脑虽然很好,却根本不读书。若接受了同等的教育,大多数女人都比男人更快接受创新,更具应答的急智。我们看到其中一些女人在交谈方面遐迩闻名,若想到她们又很少有机会去获得知识,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惊异。188
霍拉修:但是,这些人却极少具备明智的判断力。
克列奥门尼斯:那只是由于她们缺少练习,缺少实际应用,且不够刻苦而已。思考深奥的事物,这不属于女人的生活领域。女人通常被放置的那些位置,已经为女人找到了其他的工作。然而,没有一种脑力劳动是女人不能从事的;至少,在获得同等帮助的条件下,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从事脑力劳动,只要她们着手去做并坚持到底即可。明智的判断力不过是这种脑力劳动的结果罢了。一个人若尽力仔细分析事物,将事物放在一起做比较,以抽象概括、不偏不倚的方法去思考事物,换言之,他考察两个命题时,若仿佛并不在乎哪个命题是真,而不带偏见,把全部脑力贯注于命题的每一个部分,全面地考察同一个事物;他若时常这样去做,我会认为:caeteris paribus注111,此人便很可能获得我们所说的“明智的判断力”。与造就男人的工艺相比,造就女人的工艺似乎更优雅,更完美;女人的容貌更精巧,声音更甜美,其整个外表也更精致。男女皮肤的差别,则犹如细布与粗布的差别。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大自然只造就了女人这些我们能看到的优点,而在造就女人大脑时,却并没有像造就其外表时那样精心;大自然赋予女人美妙的身体结构和高度精确的组织构造,这在她们身体的其余部分都展示得非常明显。189
霍拉修:“美”是女人的属性,而“力”则是男人的属性。
克列奥门尼斯:大脑的那些微粒无论怎样细小,都包含着一些意象,都在协助思考的运作。在身体构造的契合性、对称性和精确性上,人与人之间必定存在着差别;这正像人们较大的肢体之间也存在差别一样。因此,女人胜过我们男人之处乃是其器官的精良,无论是器官的协调性还是柔韧性,都超过了男人,而这在思考艺术中都至关重要,并且是惟一堪称天赋才能的东西,因为我所说的这种依靠实践的才能,乃是与恶名一起获得的。
霍拉修:造就女人大脑的工艺,比造就男人大脑的更为精巧,因此我猜:造就牛羊犬马大脑的工艺大概是无比粗糙。190
克列奥门尼斯: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想。
霍拉修:无论怎样,那个自我,即发出意志及愿望、对事物作出选择的那个部分,都必定不具备什么实体,因为若具备实体,它就必定要么就是单一的微粒(而我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要么就是许多微粒的复合体,而这简直使人无法想象。
克列奥门尼斯:我不否认你的话。况且我已提到过:在一切动物身上,思考与行动的本源都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即使说这本源不具有实体也无济于事,并不能解决解释或设想它时的困难。我们肯定的一个a posteriori注112命题是:无论这个本源是什么,它与身体之间必定存在一种双向的接触。而非物质实体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说思想可能是物质与运动的结果一样,都是人类的能力所无法领悟的。
霍拉修:虽然其他许多动物都似乎被赋予了思想,但除了人以外,在我们熟悉的动物当中,我们不知道有哪一种表现出了(或看上去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思考。
克列奥门尼斯:若无法观察到动物的各种性质,我们便很难确定动物究竟是否具备某些本能、特征和能力。不过,动物身体机器那些主要的、最必需的部分,却很可能不如人体机器的那样精巧复杂,因为在动物身上,那些部分在三年、四年、五年,至多在六年之内便能发育到最完善的程度;而在人身上,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还没有成熟;要经过二十五年,人体的这些部分才能发育成熟并具备充分的力量。一个五十岁的人能想起自己二十岁时做过的事,想起自己曾是个男孩、曾有过哪几位老师,这种意识完全要依赖记忆,并永远无法追溯到底。换言之,倘若尚不善于思考,大脑尚未处于恰当的协调状态,尚不能长久地保存所获意象,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记得两岁以前的自己,不会记得两岁以前遇到的任何事情。然而,这种回忆无论溯及多么遥远的以往,它使我们产生的自我了解,其确切程度都不及另一个人对我们的了解,他自幼与我们一起长大,而我们见不到他的时间,从不会超过一星期或一个月。儿子三十岁时,母亲比儿子更有理由知道:儿子就是被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个人。这样的母亲每日都记挂着儿子,时时记得儿子面容的种种变化,她对儿子的了解更肯定,因为她知道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并没有变;而她却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了变化。因此,我们只知道:这种意识就是各种精力穿行于大脑全部迷宫的奔跑搜寻(搜寻与我们有关的事实),或者就是这种运作产生的结果。失去记忆者尽管其他方面或许完全健康,但思考起来却至多像个傻瓜,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与一年前一样,而只觉得刚刚认识自己两个星期。记忆丧失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完全丧失记忆者,ipso facto注113已经是个白痴了。191-192
霍拉修:我知道,我已经使你我的这番闲谈离题太远了,但我并不为此后悔。你关于大脑运作机制以及思想对较大肢体的下意识影响的话,是个可供冥思的高尚主题,它涉及那种无限的、不可言喻的智慧,依靠它,所有动物显然都被赋予了各种本能,以使它们适应实现其各自的造化意图的要求。所有欲望都被无比巧妙地融进了各种动物的身体构造当中。你对我解释了文明礼节的起源,我认为你的解释再合理不过了。而你在论述自赏时,指出了我们人类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优越,在最高意义的顺时应变和不屈不挠的勤奋方面,人类也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依靠这种优越性,众多的人从一种最顽固而无法克服的激情当中,得到了不计其数的益处,既得到了个人的安逸与舒适,又维护了群体的福祉、安全和团结。而那种激情,其本质似乎是破坏人的合群性、破坏社会的,并且永远会促使未经教化的人们彼此伤害。193
克列奥门尼斯:依靠同样的论证方式,即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为根据进行归纳推论,自赏的性质及用途以及其他各种激情便很容易得到解释,并变得能够为我们理解了。生存必需之物并没有现成地摆在各种动物眼前,随它们取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动物便具备了各种本能,而本能则促使动物去寻觅这些生存必需之物,教动物如何获取它们。满足欲望的热忱和意愿,总是与动物自身的力量和本能作用于动物的驱力相应。但是,这些生存必需之物分散在各个地方,动物又无比众多,形形色色,并都有自己想要满足的需求,因此,有一点便一定十分明显,那就是:动物获取生存必需之物、以满足不同天性之需的尝试,必定经常是障碍重重,徒劳无功。另外,倘若每个动物都未被赋予一种激情,它唤起他的全部力量,以超越一切的紧迫感,激励他去克服他维系生存的伟大工作之路上的各种障碍,那么,许多动物便极少能获得成功。我所描述的这种激情,就叫作“愤怒”。怀有愤怒的激情和自赏心理的动物,看到其他动物享用着他需要的东西如何会心生嫉妒,这很容易解释。艰辛劳动之后,连最狂野、最勤勉的动物也要寻求休息。由此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都或多或少地热爱安逸。动物竭力使用其力量,这会使它们疲惫;而经验告诉我们:要补偿精力的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进食和睡眠。我们看到,那些必须克服最大障碍才能维持生存的动物,其愤怒之情最为强烈,并且都生就了最具伤害性的前肢。这种愤怒若总是在主宰一只动物,那动物便总是会不顾面临的危险,因而很快遭到毁灭。正因为这一点,动物才全都被赋予了恐惧之心:遇到带枪的猎人,即使雄狮也会掉头而逃,其他许多动物也无不如此。根据我们对野兽的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最完善的动物当中,同一物种的动物大多都具备一种能力,即彼此使对方知道自己的需求。我们还可以肯定,一些动物不但能够互相理解,而且可能已经学会了理解我们人类。若用人类与其他动物作比较,考虑到人的身体构造,人的各种显著素质,人高于其他动物的思考及回忆机能,人学会说话的能力,以及人手及手指的有用性,我们便没有理由怀疑:人比我们知道的其他任何动物都更适宜于社会。194-195
霍拉修:由于你彻底否定了沙夫茨伯里大人的理论,我希望你给我讲讲你对社会、对人的合群性的总体看法。我会万分注意地聆听你的见解。
克列奥门尼斯:人的合群性,即人对社会的适应性,其起因并不深奥难懂。能力中常者只要具备一定阅历,对人性有一定了解,并真心渴望了解真相,而不带先入之见地去探究,便能很快找到那个起因。但是,大多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却都是为了某种目的,都为了证明某种理由是正确的。一位哲学家若像霍布斯那样说人天生就不适于社会,而又把其原因仅仅归于婴儿降生时不具备任何能力,那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倘若这哲学家的论敌认为:人能够获得的一切都应当被看作人的社会适应性的起因,那也同样没有说中问题的要害。
霍拉修:可是,人的头脑中难道不存在一种天然属性,它促使人去热爱同类,而这种属性超过了其他动物的同类之爱么?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天生就具备仇恨与憎恶之情,它们使人彼此待如豺狼熊罴么?196
克列奥门尼斯:我不相信你这些说法。根据我们见到的人类事务和大自然的种种作品,我们更有理由想象:人喜欢联合的欲望和性向,并非来自对他人的爱,这正如我们不得不相信:行星间的吸引力大于遥远的恒星对它们的吸引力,这并不是行星在同一个太阳系里始终一同运行的真正原因。
霍拉修:我可以断定,你并不相信恒星之间有什么爱。所以,还是请你列举出更多的理由来吧。
克列奥门尼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与行星之间的这种爱明显抵触。我们每天都能看见数千件事情,它们能使我们相信:人把世间一切都放进了自己心中,而这既不出于爱,也不出于恨,而仅仅是为了人自己。每一个人自己都是个小世界;而只要智力与能力允许,一切动物都会竭力使自己快乐。在所有动物身上,这都是一项持续不断的艰苦劳作,并且仿佛就是生命的意图。由此我们便可以说:人对事物的选择必定取决于人们对快乐的看法;任何人都不会做出当时对他似乎并不最为有益的行动。
霍拉修:那么,对video meliora proboque,deteriora sequor注114这句话,你又做何解释呢?197
克列奥门尼斯:它只是说明了我们天性的堕落。然而,人们尽可以畅所欲言。人所不赞成的任何自发动作,不是痉挛性的,便是不由自主的,我这里指的是那些受意志支配的动作。例如,一个人在两种事物中作出取舍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选择最为恰当,无论其理由有多么自相矛盾、多么不着边际,多么有害。没有这种情况,世上便不会有人去心甘情愿地自杀,而惩罚罪犯也就成了不公正的事情了。
霍拉修:我承认人人都极力使自己快乐,但是,同一物种的动物之间居然存在这么大的差别,例如人们对快乐的看法就大不相同;另外,其中一些动物还把其他动物最憎恶的事情当作自己的快乐。这些情况实在使人难以想象。都在追求快乐,但问题在于:哪里才能找到它。
克列奥门尼斯:快乐存在于现世的完美幸福当中,犹如存在于哲人石注115当中一样。智者贤人也好,傻瓜蠢材也罢,都曾以各种办法去寻觅这两者,但迄今都没能如愿以偿。不过,在寻找这两者的过程中,勤奋的探寻者们却时常碰巧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他们本来并不是在寻找那些东西,人类睿智的劳作和即时意图也绝不会发现它们。在地球上任何适于居住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能互相帮助,共同御敌,并能组成政治实体。在这个实体中,人们能在数百年内舒适地生活在一起,不知道上千种事情,而他们若知道了那些事情,每人都会有助于使公众的幸福(此指人们对幸福的共同认识)臻于完美。我们已经发现:在世界的一部分地方,一些伟大繁荣的民族对舰船一无所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海上交通却已经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在人们懂得如何使用罗盘航海之前,航海术已经有了无数的改进。硬说这部分知识就是人们选择航海的理由,或者用它来证明人类天生就具备从事海事的能力,全都是荒谬的。要经营一个菜园,我们就必须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有了这些条件,我们除了耐性、菜种和正确培植之外,便不需要其他了。精良的甬道、沟渠、雕像、凉亭、喷泉以及小瀑布,虽是对自然美景的重大改进,却并非菜园所不可或缺。一切民族必定都经历过简陋的初始,而在那些初民身上,人的社会适应性也如同后来一样显著。人被称为社会性的动物,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因为人们普遍以为,人天生就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喜欢社会,更需要社会;其二,因为人联合起来所获的益处,显然比其他动物联合起来(倘若它们打算联合的话)所获的更大。198-199
霍拉修:你为什么说“人们普遍以为” 人天生就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喜欢社会,更需要社会呢?难道那不是实际情况么?
克列奥门尼斯:我这么小心措辞,实在是很有理由的。一切生于社会的人,当然都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需要社会。不过,人是否天生就是如此,这却是个问题。但是,即使人的天性就是如此,那也谈不上什么卓越,也不值得夸耀。人热爱自身的安逸和平安,永远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这些必定已经足以促使人去热衷社会了,因为人在自然处境中穷困匮乏,孤立无助。
霍拉修:你说人在自然处境中穷困匮乏,孤立无助,这不是犯了与霍布斯一样的错误么?
克列奥门尼斯:根本不是,我指的是成年男女。他们的知识愈广,他们的素质就愈高;他们拥有的东西愈多,他们在其自然处境中就愈显得穷困匮乏,孤立无助。一个年金两万五千到三万英镑的贵族,拥有三四辆六轮马车和五十多名仆人,而若不计他的财产,单看他本人,他要比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更穷困匮乏,因为后者每年只有五十英镑收入,已经习惯了步行。因此,一位从不亲手给自己别别针的太太,从头到脚,无论穿衣还是脱衣都如同一个玩具娃娃,非要女仆以及另外两三名使女服侍不可,她要比那个挤奶女工朵尔更孤立无助,因为后者整整一个冬天都摸黑自己穿上补丁衣服,而且速度比做其他事情还要快。200
霍拉修:可是,你所说的改善自己处境的欲望,难道不是非常普遍、不是任何人都有的么?
克列奥门尼斯:任何堪称具有社会性的动物都是如此。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类当中任何一个可以叫出名字的人的特性。因为世上任何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中受过教育,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规划自己的生活,都会在自己的个性、财产、环境,或社会中他所属的那个部分里增添、减少、改变一些东西。在所有的动物当中,惟有在人身上才能见到这种情况。倘若人的欲望不这么过分,不这么繁多,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人在满足自己所谓需求时会如此勤勉。以上一切都表明:我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的第二个理由是:人联合起来所获的益处,显然比其他动物联合起来(倘若它们打算联合的话)所获的更大。要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必须到人的本性中寻找人胜过其他一切动物的品质,那些绝大多数人都具备的品质,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但这么做时,我们却不应当忽略人们身上所有能被观察到的东西,从人们的最年幼时期直到极为年迈的时期。201
霍拉修:我真弄不懂,你为什么要事先提醒要观察人的一生。仅仅观察一个人最成熟、最年富力强时所具有的品质,这还不够么?
克列奥门尼斯:所谓动物的驯服性,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指肢体的柔韧性,以及它们对灵活运动的适应性。动物发育完全时,这些性质或者完全丧失,或者大为削弱。在获得思考和说话机能的能力方面,我们人类迄今超过了其他一切动物。这种能力是属于我们人类天性的一个特殊属性,这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十分明显:人发育成熟后,倘若这种能力还是一直被忽略,它便会消失。同样,我们人类通常能享受的寿命比大多数其他动物的要长,因此,我们便拥有了一种其他动物没有的特权,即支配时间。与寿命只有人类一半、而能力与人相当的动物相比,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智慧(尽管它完全得自亲身经历)。caeteris paribus注116,六十岁的人比三十岁的人更懂得在生活中应当抓住什么、避免什么。在《两兄弟》里,弥克昂在为青年做的蠢事辩护时,曾对他的兄弟德梅亚说:ad ominia alia aetate sapimus rectius注117。这句话既适用于野蛮人,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家。正是这些能力的合力加上其他的特性,共同构成了人的社会适应性。202
霍拉修:可是,你列举的这些特性当中,并没有提到对我们这个族类的爱,这又是为什么呢?
克列奥门尼斯:首先是因为,我已经说过,对同类的爱似乎并不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其他动物也具备这种爱;其次是因为,这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切政治实体的本质,便会发现:对同类之爱之类的情感,历史上都没有过任何信赖,没有过任何重视,无论是为了建立政治实体,还是为了维持政治实体,都是如此。
霍拉修:但是,这个称谓本身与这个字的含义,却彼此从对方引进了“爱”这个字义,并通过反面的性质显现出来。喜欢独处者厌恶结伴;性情孤独、沉默、抑郁者,则与喜欢交际者截然对立。203
克列奥门尼斯:我承认,我们把一些人比作另一些人的时候,往往在那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字。但是,当我们谈到一种人类独具的品性、说“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时,这个字就仅仅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天性中存在着某种适应性,绝大多数人依靠它来协力合作,并有可能联合成一个实体;这种实体赋予并利用每个人的力量、技能与智慧,它能控制自身,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仿佛被同一个人的心灵激活,被同一个人的意志驱动。虽然我愿意赞成一种见解,即在促使人们进入社会的各种动机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愿望,那就是天生追求结伴,但是,人这种强烈愿望却完全是为了自己,并且无不希望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除了希望得到一些好处或他想得到的其他东西,人从不会希求其他任何东西,无论是结伴还是其他什么,都不希求。我不赞同这样的见解:人天生就具有这种强烈愿望,而它来自人对同类的爱心,那爱心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的同类之爱。这种见解是我们对人类自身通常的恭维,但其现实依据也仅限于我们彼此都是“恭顺的仆人”而已。我坚决主张一点:这种所谓的“人对同类的爱”,以及据说我们怀有的、超出其他动物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天然好感,既不有助于建立种种社会,人们审慎交往时,也不依赖它;即使它不存在,人们也会照样联络交往。一切社会的确凿基础乃是政府。我们即将深入考察的这条真理,将为我们提供用以说明人的优越性及社会性的全部理由。这条真理显然表明了一点:即将结成一个共同体的动物,首先必须是可以被治理的动物。这种素质要求动物怀有畏惧感,并具备一定的理解力,因为没有畏惧心的动物是永远无法被治理的;若没有这种有用激情的影响,动物的智能与勇气愈多,它就愈不驯良、愈难治理。同样,没有理解力的畏惧只会使动物逃避它所惧怕的危险,而并不顾及自己脱险后的处境。例如,野鸟为了飞出鸟笼去吃食,会在鸟笼上撞出自己的脑浆。驯服的动物与可治理的动物,两者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一只动物若只是顺从另外一只,它仅仅是在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以此来避免另一件自己更不喜欢的事。我们或许会非常顺从,但对我们顺从的人却毫无用途。然而,做一个可被治理的人,则意味着极力使治理者满意,情愿为了治理者而竭尽全力。但是,爱则无不产生于家庭,因此,若把自我完全排除在外,任何动物都不可能为其他动物劳作,都无法长期与其他动物相安无事。可见,安于顺从,并学会了把自己受到的奴役理解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并因此而情愿为其他动物劳作,一只动物惟有如此,它才是真正的“可治理的动物”。把几种动物变为这种可治理的动物,并不会太困难。但是,除了人以外,世上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如此驯服,以至能被改造成为自己族类服务的动物。尽管如此,若没有这种驯服性,人就永远无法具备社会性。204-205
霍拉修:人不天生就是为了社会而设计的么?
克列奥门尼斯:我们从天启中知道:人就是为了社会而创造出来的。
霍拉修:但是若没有天启,或者你若是个中国人或墨西哥人,你作为哲学家又该如何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克列奥门尼斯:大自然为社会设计了人;同样,大自然为酿葡萄酒而造化了葡萄。
霍拉修:酿葡萄酒是人的发明,正像从橄榄和其他蔬菜中榨油、用大麻做绳子一样。
克列奥门尼斯:用独立的个人构成社会也是如此,并且,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这更要求技巧了。
霍拉修:人的社会性难道不是自然之作么?或者可以说,它难道不是自然的创造者、即神圣上帝的作品么?206
克列奥门尼斯:毫无疑问。不过,一切事物的内在长处及其特性也无不如此。所以说,葡萄适于酿造红酒,大麦和水适于酿造其他酒类,这些都是上帝的作品;但是,发现它们的用途并加以利用的,却正是人的聪明才智。同样,人的所有其他能力及其社会性,显然也都来自人的创造者——上帝。因此,我们的勤勉所能制造及获取的一切,其最初全都来自我们的创造者。但我们谈到自然之作,以区别于技艺之作,却仿佛无须我们的认可,便可以成立。因此我们才认为,一到恰当的季节,大自然便会产出豌豆。但在英格兰,若没有技艺和非凡的勤劳,你便无法在一月份得到嫩豌豆。大自然所设计的东西,她势必要亲自创育造化。有些动物能清晰地看到:大自然设计它们就是为了构成社会,蜜蜂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因为从实际效果看,大自然为此而赋予了蜜蜂种种本能。我们把自己及其他一切的存在都归功于宇宙万物的伟大创造者,不过,没有上帝的维系力量,各个社会便无法存在下去,同样,没有人类智慧的支持,各个社会也无法存在下去。因此,所有社会都必定都具有依赖性,或依赖于互相的契约,或依赖于强者加诸弱者忍耐之上的力量。技艺之作与自然之作之间的区别极大,因此我们不能不去分别了解这两者。先验的知解只属于上帝,上帝的智慧本身就包含着原初的确定性,而我们所说的“证明”,其实不过是从中借取的、不完善的副本而已。所以,在自然之作当中,我们既看不到苦心孤诣的努力,也看不到屡经尝试的痕迹。它们都很完整,并无不与自然的最初设计完全一致。自然之作若没有受到干扰破坏,它们必定都高度完美,为人的智能与感觉所无法领会。与此相反,可怜的人类除了根据归纳的事实作出的推理之外,却什么都无法确证,包含人类自身的存在。结果,人的技艺与发明之作便无不残缺不全,其中大多数在最初很是简陋低劣。人类的知识发展得十分缓慢,一些技艺和科学经历了许许多多世代的发展,才达到还算完善的程度。我们是否有理由想象:第一个派出蜂群的那个蜜蜂社会,其蜂蜡与蜂蜜的质量会远逊于其所有后代所生产的呢?何况,自然规律是固定的,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一切秩序和规则都是恒定的,人的才能与认可对它们根本不起作用。207-208
quid placet aut odio est,quod non mutabile credas?注118
在蜜蜂当中,难道不可能曾经有过形式不同于现在各个蜂群都服从的政府么?在政府这个问题上,人们做出过多少各式各样的思考!什么荒唐的设想没有被提出来过啊!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观点的分歧是何等巨大!什么生死攸关的争论不曾有过!然而,究竟什么是政府的最佳形式,这个问题却至今都没有定论。人们提出过不计其数的规划,无论好坏,都说是为了造福社会,使社会更加美好。可是,我们的智能却又何等短视,人的判断力又多么容易犯错误!我们往往发现,在一个时代似乎极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在其后世却分明是于人类有害;甚至在同一时代当中,为一国所崇敬的东西,在另一国却令人憎恶。蜜蜂在其器用和建筑上做过哪些改变呢?它们建造过非六角形的蜂巢么?它们曾用工具补足过自己的天赋能力么?世界上各个伟大的国家建造了何等雄伟的建筑,做出了何等惊人的伟绩啊!而大自然对这一切成就的贡献,却仅仅是提供了各种材料。大理石出自矿场,但用它做出雕像的却是雕刻家。人类拥有发明出来的铁质工具,种类无数,而大自然除给了我们她藏在地心的岩浆之外,什么都没给我们。209
霍拉修:但是,工匠、发明技艺者、改进技艺者,其大部分能力却都来自使劳动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而他们的天才则来自大自然。
克列奥门尼斯:其才能要依赖他们的身体构造,即人体机器的精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确如你所说,并且仅仅如此。不过,我已经承认过这一点了。你若还记得我关于人脑的那番话,便会发现:在每一个人完成那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与耐心方面,大自然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霍拉修:我若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清两件事情:第一,人超过其他一切动物的社会适应性虽然确实存在,但在大量的人聚合在一起、并得到妥善管理以前,它在个体的人身上却几乎无法被察觉到;第二,这种确实存在的性质,即人的社会适应性,乃是一种复合体,它由几方面的事物共同构成,而并非由人所独具、野兽所不具备的任何显著品性构成。210
克列奥门尼斯:你说的完全正确。每一粒葡萄都包含着一点儿汁液,而把大量的葡萄放在一起压榨,它们便会产出一种液体,依靠熟练的操作便可能被做成葡萄酒。不过,若考虑到要把那液体变成葡萄酒必须经过发酵,换言之,若考虑到发酵是酿造葡萄酒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便会十分清楚一点:若不是用语极为不当,我们就不能说“每一粒葡萄里都有葡萄酒”。
霍拉修:葡萄酒性,只要是发酵产生的结果,它就是一种外来因素;每粒葡萄只要单独存在,任何一粒都不能获得这种性质。因此,你若把人的社会性比作红酒的葡萄酒性,你就必须让我相信:社会当中存在着一种相当于发酵作用的东西。换句话说,单独的个人并不真正具有这种东西,众人聚合起来时,它也分明是一种外来因素。要构成社会,那种发酵过程就必不可少,如同使葡萄汁液产生葡萄酒性也离不开发酵一样。
克列奥门尼斯:这种相当于发酵作用的东西,可以从人们的交往中得到证明,因为若检验据以判断并宣布“人是最富于社会性的动物”的每一种机能及素质,我们便会发现:众人这些素质的相当一部分(若不是绝大部分的话)都来自人们之间的互相交往。fabricando fabri fimus注119。人是通过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才具备了社会性的。天生的温情促使所有的母亲去呵护照料自己的后代,在后代尚不具备自我照顾的能力时,母亲们养育他们,并使他们不受到伤害。不过,在穷人当中,女人没有闲暇让自己用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表达对婴儿的疼爱,而她们对孩子的溺爱与日俱增,她们往往不能照料孩子,不能和孩子一起玩耍。这样的孩子愈健康,愈安静,他们就愈容易被忽视,缺少与婴儿的闲聊,不时时唤起婴儿的精神,这往往是造成儿童日后无可挽回的愚蠢与无知的主要原因。我们常把完全是由于忽视早期教育造成的结果看作天生的能力欠缺。我们很少会见到从不与自己的同类交往的人,因而我们很难猜出完全没有经过教化的人是什么样子。不过,我们却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人的思考机能一定非常不完善;一个人若既没有任何东西可资模仿,又没有人去教他,那么,即使他再能接受调教,也毫无用途。211-212
霍拉修:因此,哲学家论述自然规律时说他们知道自然状态中的人想些什么,在没有指导的条件下,那些人如何解释自己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这实在是聪明过人。
克列奥门尼斯:洛克正确地指出:正确地思考和推理要求时间与实践注120。不善思考,只关心眼前需要的人,很难超越其现有水平。在地球上那些偏远的地方,在人烟最稀少之地,我们会发现:比起在大城市及相当规模的村镇里及其附近来,我们人类更接近自然状态。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人里中的最无知者身上,你大概可以知道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你若与他们随便谈些需要抽象思考的事情,那么,在五十人当中,连一个能听懂你的话的人都没有。不过,他们当中不少人却是有用的劳工,并且狡猾得足以撒谎骗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智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即使后来他愿意具备理智,也不能像穿一件衣服那样,马上就能如愿。说话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征,但没有人生来就会说话。即使两个野蛮人生下的第十几辈后代,也不具备任何稍微像样的语言。倘若一个人在二十五岁以前从未听到过别人说话,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在二十五岁以后能学会说话。213
霍拉修:你说过,当动物的器官尚属柔顺灵活、容易接受种种印象时,教育乃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无论是说话还是思考,这种教育的意义都万分重大。可是,人们能教会狗或者猴子说话么?
克列奥门尼斯:我认为不能。但我想:其他动物没有吃过一些孩子吃的那种苦,因为后者必须吃那么多苦,才能学会说出一个字。另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是:虽然有些动物的寿命或许比人类长,但没有任何物种像人这样有如此长的年轻期。另外,我们的成长要感谢被我们归因于人类超出其他动物的学习资秉(它来自人体结构及内部构造的高度精确性)的那些素质,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从我们的顺应性上获得什么帮助,因为人必须经历长期缓慢的逐步变化,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在我们的器官刚刚达到半成熟时,其他动物的器官已经硬化了。
霍拉修:这么说,在我们对人类被赋予的说话能力及社会性的恭维当中,惟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人若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接受教育,便能够依靠耐心和勤奋学会说话,并使自己具备社会性。214
克列奥门尼斯:否则便不行。一千个二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若都在野蛮的环境里长大,并且互不相识,你便永远无法使他们具备社会性。
霍拉修:我想,他们的教育若开始得这么晚,他们便不可能被文明化。
克列奥门尼斯:但我说的仅仅是社会性,因为它是对人的特定描述。换言之,我们不可能依靠技巧去治理这些人,如同不能以此去治理一千匹野马一样,除非你用两三千人去监视他们,并使他们一直怀着畏惧之心。因此,大多数社会,以及各个国家在最初的时候,很可能都是按照威廉·坦普尔爵士注121设想的方式形成的,但其过程却绝不像他说的那么迅速。我实在想知道:一个如他所说无疑具备了精明头脑的人,如何在一只未经教化的动物身上看到正义、精明和智慧;或如何在根本不存在文明社会时,甚至在人们尚未开始交往时去设想文明人。
霍拉修:我想,我以前肯定听说过坦普尔爵士的有关见解,但我忘了你指的是他哪个观点了。
克列奥门尼斯:他那本书就在你身后,在从下面数第三个架子上。第一卷。请你把它递给我。他的观点值得一听……这是他论述政府的一篇文章注122。在这儿:因为倘若我们考虑到,人通过生育众多子女来增加自己这个物种的数量;父母关怀子女,甚至为他们提供必需的食物,直到子女能够独立谋生。在一代代人身上,子女能独立谋生,这都大大晚于我们在其他动物那里观察到的情况;人类依靠父母的时间也大大长于其他动物;倘若我们不但考虑到人对子女的关怀,而且考虑到人为养活自己无助的子女而不得不付出的勤勉(无论是采集天生的水果时的,还是获取那些经过艰辛劳作才能得到的食物时的);倘若人不得不养活子女,不得不去捕捉那些比较驯服的动物、猎取那些比较野蛮的动物,有时还不得不鼓起全部勇气去保卫自己的小家族,与强大凶残的野兽搏斗(那些野兽会以人为猎物,正如人会以弱小温驯的动物为猎物一样);倘若我们设想人能够按照子女饥饿的程度或需要,慎重而有条理地分配食物(无论这些食物是什么),并且有时能把当天余下的食物留到次日,有时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让需要食物的子女挨饿……215
霍拉修:这根本不是个野蛮人,也绝不是个未经教化的人。他倒适合做个治安法官。
克列奥门尼斯:求你别打断我,让我念下去。我只念这一段:当儿子长大、能够参与维持家庭生计时,他便通过教训和实例让儿子懂得:家中作儿子的成年后应当去做什么,而日后作为另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又应当去做什么;告诉所有的子女:若要健康平安,什么品质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告诉他们:一般的社会(它们当然既包含着人们普遍推崇的美德,也包含着恶德)都爱护并鼓励人们去向善,都憎恶并惩罚向恶的人。最后还要告诉他们:遇到生活的各种事件时,若现世不能给他慰藉,就仰望上苍;每当发现了自己的脆弱之处时,就去求助于一种更高的、更伟大的自然。考虑到以上一切,我们一定会做出结论说:此人的孩子长大后,人们一定会称赞他的智慧、善良、英勇和虔诚。人们若看到他的家庭经常是丰衣足食,还会认为他非常幸运。216
霍拉修:我真想知道:这个人难道跳出了地球么?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克列奥门尼斯:最荒唐的设想就是……
霍拉修:这番讨论已经占了你我太多的时间。我可以肯定,我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已经使你厌倦了。
克列奥门尼斯:不,你使我万分快乐。你提的问题全都非常切中肯綮。有头脑的人若从未思考过这些事情,都会提出这些问题。我是有意向你读那这段文章的,因为我想它大概对你有用。不过,倘若你厌倦了这个题目,我不会使你不耐烦的。
霍拉修:你误会我了。我已经开始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了。只是在你我深入讨论它之前,我打算再把那篇文章通读一遍。这要花很长时间。读完它之后,我会很乐意继续与你讨论这个题目,愈早愈好。我知道你很喜欢美味的水果,明天你若和我一起吃饭,我会给你一个菠萝。217
克列奥门尼斯:我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因此根本无法拒绝任何这样的机会。
霍拉修:那么,再见啦。
克列奥门尼斯:再见。您的仆人时刻恭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