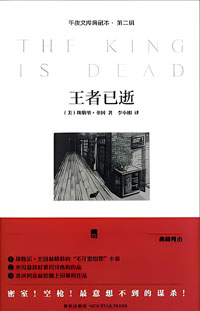“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康格问,“说下去。我很感兴趣。”
房间里一片沉默;所有人都盯着康格——他身上仍然穿着褐色的囚服。议长慢慢向前探过身去。
“进入监狱之前,你做的生意很赚钱——都是些违法的生意,但获利丰厚。而现在,你一无所有,还要在监狱的格子间里再待六年。”
康格沉下脸。
“有个任务,对于委员会来说非常重要,也需要你的特殊能力。而且,这个任务你会很感兴趣。你是个猎人,不是吗?你经常设下陷阱,藏在灌木丛中,等待晚上的狩猎游戏,对吗?我想,狩猎肯定会为你带来满足感,追捕、跟踪——”
康格叹了口气,撇撇嘴。“好吧,”他说,“先别管那个,说重点。你想让我杀掉谁?”
议长笑了,“一切还得按部就班。”他轻声说。
汽车停了下来。天色已晚,这条街上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光亮。康格看着外面,“我们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警卫伸手按住他的手臂,“来。从那扇门进去。”
康格走下汽车,站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警卫迅速跟在他身后,然后是议长。康格深深吸了一口冷空气,端详着矗立在他们面前的建筑物,却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
“我认识这个地方,以前见过。”他眯起眼睛,已经逐渐适应黑暗。突然,他变得警觉起来,“这里是……”
“没错。第一教会。”议长走向台阶,“有人在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在这里?”
“是的,”议长踏上台阶,“你知道,我们不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教堂,尤其是带着枪的时候!”他停了下来。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隐隐出现在前方,一边一个。
“行了吧?”议长抬头看向他们。他们点了点头。教堂的门敞开着。康格能看到里面还有其他士兵四处闲站着,年轻的士兵们瞪大眼睛看着圣像画。
“我明白了。”他说。
“这很有必要,”议长说,“你也知道,我们以前和第一教会的关系非常糟糕。”
“现在这样也无法改善关系。”
“但这是值得的。你会看到的。”
他们穿过大厅,进入主殿,圣坛和跪拜处都在这里。他们从圣坛旁经过时,议长几乎一眼都没往那边看。他推开一扇小小的边门,示意康格进来。
“这里,我们必须快一点儿。信徒们很快就会蜂拥进来。”
康格走进去,眨了眨眼睛。他们身处一个小房间里,天花板很低,木制镶板老旧暗淡。房间里有一种灰烬和香料闷烧的气味。他嗅了嗅,“那是什么?那个味道。”
“墙上那些容器。我不知道。”议长不耐烦地走到房间另一边,“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它就藏在这里——”
康格环顾房间,看到书籍和论文、十字架和圣像。他全身微微掠过一阵奇怪的战栗。
“我的任务涉及教会的人吗?如果是的话——”
议长转过身来,惊讶不已,“你竟然相信创教人?这可能吗?一个猎人,一个杀手——”
“不,当然不相信。他们那套关于听天由命、拒绝暴力——”
“那是怎么回事?”
康格耸耸肩,“别人一直告诉我不要跟那些人打交道。他们拥有奇怪的能力,而且你也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议长若有所思地看着康格,“你理解错了。我们打算下手的并不是教会里的人。我们早就发现,杀掉他们只会让他们的人数增加。”
“那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们走吧。”
“不,我们来这里是要找一些重要的东西。你要靠那东西才能确定下手目标。没有它,你就无法找到那个人。”议长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们可不希望你杀错人。这太重要了。”
“我不会犯错。”康格挺起胸脯,“听着,议长——”
“这次情况不同寻常,”议长说,“你看,你要追踪的那个人
——我们要派你去找的那个人——只有通过这里的某样东西才能辨认出来。那是唯一可追溯的痕迹、唯一的识别方法。如果没有——”
“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他朝着议长走过去。议长走向一边,“看,”他说着拉开一道滑动墙,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方形洞口,“在那里。”
康格蹲下来,看向里面。他皱了皱眉,“一个头骨!一具骷髅!”
“你要追踪的那个人,死于两个世纪之前,”议长说,“他的全部遗骸都在这里。你只能靠这些东西来找到他。”
很长一段时间,康格一言不发。他低头盯着墙壁凹陷处隐约可见的骨骼。要怎么杀掉一个死了几个世纪的人?要怎么追踪他、击败他?
康格是个猎人,一个活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男人。他曾经靠走私生意维持生计,用自己的飞船从辖区外偷运毛皮,他高速航行,偷偷溜进地球周围的关税线。
他曾经在月球的山脉上打猎。他曾经穿越空荡荡的火星城市。他曾经探索——
议长说:“士兵,拿上这些东西,带到车上去。别漏掉任何一部分。”
士兵蹲下,小心翼翼地爬进墙洞里。
“我希望,”议长继续对康格轻声说,“现在你会证明对我们的忠诚。公民有很多方式可以自我救赎,表现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对你来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甚至怀疑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当然,你付出的努力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两个男人彼此对视:康格身形消瘦,蓬头垢面;议长干净利落,衣冠楚楚。
“我明白了,”康格说,“我是说,我明白了这是个机会。但是,一个死了两个世纪的人怎么才能——”
“我稍后再解释,”议长说,“现在我们得快一点儿。”士兵已经把骨骼带了出来,裹在一条毯子里,小心地捧在怀中。议长走向门口,“快来,他们已经发现我们闯进这里了。他们随时会出现。”
他们匆忙冲下湿漉漉的台阶,坐进等在那里的汽车。一秒钟后,司机把车开到空中,飞过房顶上方。
议长向后靠在座位上。
“第一教会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他说,“我想你对这个也很熟悉,但我想谈谈与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
“这场运动始于20世纪——当时不断爆发战争,在其中一次战争期间,人们发起了这场运动。运动发展迅速,因为人们普遍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每次战争都会孕育出更大规模的战争,看不到尽头。这场运动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军备,没有武器,也就没有战争。没有机械和复杂的科技,也就没有武器。
“这场运动宣传,人们不可能通过制订计划来阻止战争。他们号称人类正在被机械和科学打败,这些东西逐渐不受人类控制,导致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高呼,打倒社会体制,打倒工厂和科学!如果再发生几次战争,整个世界将所剩无几。
“创教人是个不起眼的家伙,来自美国中西部一个小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只知道,有一天他突然冒出来,鼓吹一种非暴力、不抵抗的教义;不要争斗,不要为枪支纳税,除了医学之外不要进行研究。安安静静地生活,修整你的花园,远离公众事务,少管闲事。做个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一穷二白的人。放弃你的大部分财产,离开城市。至少,他所说的内容只会发展出这种结果。”
汽车开始降落,在一处屋顶上着陆。
“创教人鼓吹这种教义,或者说最初的教义。很难说后来的信徒们添加了多少自己的理解。当然,地方当局立即逮捕了他。显然,他们相信这个人可不是说着玩玩的,再也没有释放他。他被处死,尸体被秘密下葬。表面上看来,这个邪教已经灭亡了。”
议长微微一笑,“不幸的是,一些信徒声称在他去世那天之后还见过他。谣言开始流传,他能战胜死亡,他是神圣的。这些谣言逐渐扎根、发芽。到了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教会阻碍了一切社会进步,破坏社会体制,播下无政府状态的种子——”
“但是战争呢,”康格说,“战争怎么样?”
“战争?嗯,没有再爆发战争。必须承认,普遍出现的非暴力行为,其直接结果就是消灭了战争。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战争。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战争具有深远的选择意义,完全符合达尔文和孟德尔等人的学说。如果没有战争,那些无用的、没有能力的、未经培养或缺乏智慧的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发展壮大。战争的作用就是减少这种人的数量;就像风暴、地震和干旱,大自然通过这些方法淘汰不合格者。
“没有战争,低水平人类所占的比例会增大到不合理的程度。他们会威胁教育水平较高的少数人,拥有科学知识、经过悉心培养的人,有能力引领社会的人。他们对于科学或基于理性的社会系统毫无敬意。而这场运动旨在帮助他们,煽动他们。只有当科学家们能够彻底掌控一切时——”
他看了看表,猛地打开车门,“剩下的我们边走边说。”
他们穿过屋顶,周围一片漆黑,“现在你肯定已经知道这是谁的骨头,我们要追踪的那个人是谁。他就是创教人,这个愚昧无知的人来自美国中西部,死于两个世纪之前。悲剧在于,有关当局当时行动太慢了。他能找到演讲的机会,散布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他得到传教的机会,创立了他的邪教。这种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
“但如果他在传教之前就死掉了呢?如果他那些教义从未宣之于口呢?我们知道,他说出这些内容只花了片刻时间。据说他只做过一次演讲,只有一次。随后当局就把他带走了。他完全没有反抗。整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议长转向康格。
“微不足道,但那件事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他们走进建筑物里面。士兵们已经把头骨放在一张桌子上,站在周围,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显得很紧张。
康格从他们中间挤过去,走向那张桌子。他弯下腰盯着那堆骨头看,“这就是他的遗体,”他喃喃地说,“创教人。教会把这些骨头藏了两个世纪。”
“没错,”议长说,“但如今在我们手上。我们到大厅那一边去。”
他们穿过房间,走向一扇门。议长推开门,里面的技术人员抬起头。康格看到嗡嗡转动的机器,很多工作台和蒸馏瓶。房间中央有个闪闪发光的透明操纵舱。
议长递给康格一把自动枪,“关键是要记住,必须把头骨完整无缺地带回来——以便比对证明。瞄准下面——胸口。”
康格掂了掂手里的枪,“感觉不错,”他说,“我知道这种枪,以前见过,但从来没用过。”
议长点点头,“会有人指导你怎么用这把枪,怎么控制操纵舱。我们会给你所有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数据。具体地点是一个名为‘哈德逊田野’的地方,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外的一个小社区,时间大概是1960年。别忘了,你只能靠那个头骨把他辨认出来。门牙特征明显,尤其是左边的门牙——”
康格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看着两个一身白衣的男人把头骨仔细包在塑料袋里。他们把塑料袋绑好,放进透明操纵舱。“如果我搞错了呢?”
“找错了人?那就再去找到正确的目标。除非成功完成任务,抓到创教人,否则不要回来。不要等到他开始演讲,我们必须阻止这件事!你一定要提前采取行动。如果你认为已经找到了他,那就要抓住机会立即开枪。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个地区很可能是个生面孔。显然没有人认识他。”
康格迷迷糊糊地听着。
“现在你都明白了吗?”议长问。
“是的,我想没错。”康格进入透明操纵舱坐下来,把手放在操作轮盘上。
“祝你好运,”议长说,“我们会期待你的成果。从哲学角度看,人们对于一个人是否可以改变过去抱有些许怀疑。如此一来,我们也将一劳永逸地搞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
康格的手指碰了碰操纵舱的控制部件。
“顺便说一下,”议长说,“不要利用这个操纵舱去做与你的任务无关的事情。我们会持续跟踪。如果我们想让它回来,就能让它回来。祝你好运。”
康格什么也没说。操纵舱密封起来。他伸手握住操作盘,小心转动。
当外面的房间消失时,他仍然盯着那个塑料袋。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操纵舱的透明金属网外面什么也没有出现。康格思绪万千、心乱如麻。他怎么才能认出那个人?他怎么才能提前确定就是那个人?他长什么样?他叫什么名字?他演讲之前有何表现?他是个平凡无奇的人,还是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康格举起自动枪贴在自己的脸上。金属冰冷而光滑。他练着移动瞄准器。这是一把很漂亮的枪,他会爱上这把枪的。如果他在火星沙漠中能拥有这样一把枪该多好——那些漫长的夜晚,他趴在地上,冻得浑身僵硬,等待猎物穿越黑暗前来——
他放下枪,校正操纵舱的仪表读数。袅袅盘旋的水雾开始凝结,滴落下来。突然,他身边的物体开始摇动颤抖。
色彩、声响、动静通过透明的金属网渗入进来。他关掉控制器,站了起来。
他降落在一处山丘上,俯瞰下面的小镇。正午时分,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路上驶过几辆汽车。远处是一片平坦的田野。康格走向门口,来到舱外。他深深吸了一口空气,然后又回到操纵舱里。
他站在隔板上的镜子前,审视自己的外表。他把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他们没有要求他剃掉——头发也很干净。他身穿20世纪中期的服装,古怪的衣领和外套,兽皮制作的鞋子。口袋里是那个时代的钞票,这个很重要。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不需要别的,除了他的能力,他特有的精明狡诈。但在此之前,他也从未接受过这种任务。
他沿着街道朝小镇走去。
他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架子上的报纸。1961年4月5日。时间没有偏离太远。他环顾四周,一家加油站、一个车库、几家小酒馆和一家小杂货店。沿着街道走下去,还有一家食品店和一些公共建筑。
几分钟后,他踏上一家小型公共图书馆的楼梯,穿过大门,进入温暖的室内。
图书管理员抬起头微笑。
“下午好。”她说。
他也笑了笑,但没有开口,因为他说的话很可能不太对,口音也很古怪。他走向一张桌子,坐在一叠杂志旁边,粗略浏览了一会儿,然后又站起来。他穿过房间,走向墙边一个宽阔的书报架。他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
报纸——最近几周的报纸。他取了一叠放到桌边,开始迅速浏览。印刷奇特,字体古怪,有些词语很陌生。
他把报纸放到一边,继续到架子上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他把《樱桃木公报》带到桌上摊开,翻到头版。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嫌犯上吊自杀
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被县警局以参加犯罪帮会之嫌疑逮捕,今天早晨发现他死于——
他读完了这篇文章,含糊其辞,没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消息。他需要更多信息。他把报纸放回架子上,犹豫了一下,走向图书管理员。
“还有更多吗?”他问,“更多的报纸。以前的?”
她皱起眉头,“多久以前?哪些报纸?”
“几个月以前的。有更早的就更好了。”
“《樱桃木公报》?我们只有这些。你想要什么?你在找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助你。”
他沉默下来。
“《樱桃木公报》的办事处也许能找到更早的报纸。”那个女人摘下她的眼镜,“为什么不去那里试试?但如果你告诉我你要找什么,也许我能帮得上你——”
他走了出去。
《樱桃木公报》的办事处藏在一条小巷里,人行道破旧不堪。他走进里面。暖炉在小办事处的角落里发出光芒。一个大块头男人站起来,慢慢走向接待台。
“有何贵干,先生?”他问。
“旧报纸。一个月前或更早的。”
“买下来?你想买报纸吗?”
“是的。”他取出一些钱。那个男人盯着他看。
“没问题,”他说,“没问题,请稍等。”他迅速走出房间,回来时抱了一大堆东西,被压得摇摇晃晃、满脸涨红。“这些就是。”他咕哝着,“我把能找到的都拿来了。一整年的都有。如果你还想要更多的——”
康格把报纸带到外面,坐在路边开始浏览。
他要找的东西在四个月之前,去年12月的时候。那是一篇很短的简讯,他差点儿看漏了。他用微型字典查询一些古老的词语,浏览这段文字时,双手颤抖。
男子因未经许可发表演说而被捕
警长达夫称,库珀河警局特工逮捕了一个身份不明、拒绝透露姓名的男人。据称,本地区警局最近注意到这个人后,一直在对他进行监视。这是——
库珀河。1960年12月。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他站起来,甩甩脑袋,在冰冷的地面上跺了跺脚。太阳已经转到山丘那边。他微微一笑,已经找到了确切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只需回到过去,也许可以在11月,库珀河——
他穿过小镇中心地区步行回去,走过图书馆,经过杂货店。接下来没什么难事了,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他会到库珀河去,租个房间,做好准备,等待那个人出现。
他转过拐角。一个拿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正从门口走出来。康格避到一边让她过去。那个女人瞥了他一眼。突然,她脸色变得惨白,目瞪口呆。
康格匆匆离开。他回头看了看。她是怎么了?那个女人仍然盯着他,手里的东西已经全都掉在了地上。他加快速度转了个弯,走进一条小巷。他再次回头望过去,那个女人已经来到小巷入口,开始追赶他。她身旁还多了一个男人,两人一起朝着他跑过来。
他迈开大步飞快地离开小镇,轻松爬上城边的小山,甩掉了他们。他找到操纵舱,停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是他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吗?还是穿戴搭配?
他百思不得其解。太阳落山,他走进操纵舱。
康格坐在操作盘前面。他稍待片刻,双手轻轻放在控制器上。然后他把操作盘转动了一点点,严格遵循控制器读数。
一片灰色笼罩了他。但不会很久。
那个男人上下打量着他,“你最好进来吧,”他说,“外面很冷。”
“谢谢。”康格感激地走进敞开的门,来到客厅里。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煤油加热器,客厅里很暖和,有点儿闷闷的。一个身材臃肿、套着花裙子的女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她和那个男人一起审视着他。
“这个房间很不错。”那个女人说,“我是阿普尔顿夫人。这里有加热器,一年中这段时间,你可离不了这东西。”
“没错。”他点了点头,环顾四周。
“你想和我们一起吃饭吗?”
“什么?”
“你想和我们一起吃饭吗?”男人的眉毛皱了起来,“你不是外国人吧,先生?”
“不,”他笑了,“我出生在这个国家。不过在遥远的西部。”
“加利福尼亚?”
“不,”他犹豫了一下,“俄勒冈。”
“那儿是什么样子?”阿普尔顿夫人问,“我听说那里有很多花草树木。这里就光秃秃的。我本人来自芝加哥。”
“那是中西部,”男人对她说,“你可算不上外国人。”
“俄勒冈也不是外国,”康格说,“那里是美国的一部分。”男人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盯着康格的衣服。
“你的外套看起来很有趣,先生,”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
康格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不安地移动了一下身子,“这外套挺好的。”他说,“如果你不希望我住在这里,也许我最好去别的地方看看。”
他们两人都抬起手阻止他。那个女人笑着对他说:“我们只是必须小心那些红衣军。你知道,政府总是警告我们注意那些人。”
“红衣军?”他感到困惑。
“政府说他们无处不在。我们应该报告任何奇怪或不寻常的事情,任何表现不正常的人。”
“就像我这样?”
他们看起来有些尴尬,“嗯,在我看来你不像红衣军,”男人说,“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论坛报》说——”
康格心不在焉地听着。比他想象的还要容易。显然,创教人一出现他就会知道。这些人对于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都会疑神疑鬼、说短道长、议论不休,消息很快就会传开。他只需潜伏下来注意打听,也许可以到商店去,或甚至就在这里,阿普尔顿夫人的寄宿公寓里。
“我能看看房间吗?”他说。
“当然,”阿普尔顿夫人走向楼梯,“我很乐意带你看看。”
他们一起上楼。楼上要冷一点,但没有外面那么冷,也没有火星沙漠的夜晚那么冷。他对此心怀感恩。
他在商店里慢慢转悠,看着那些蔬菜罐头,还有敞开的冰柜里干干净净、闪闪发亮的冷冻鱼和冷冻肉。
埃德·戴维斯朝他走过来,“要我帮忙吗?”他问。这个男人的衣着有点儿古怪,还留着胡须!埃德忍俊不禁。
“不用,”那个男人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只是看看。”
“没问题。”埃德说。他回到柜台后面。哈克特夫人推着她的购物车走过来。
“他是谁?”她低声说,尖尖的面孔转向那边,她的鼻子动了动,仿佛嗅着什么,“我以前没见过他。”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怪怪的。他为什么要留胡须?没有别的人留胡须。他肯定有什么问题。”
“也许他就是喜欢留胡须。我有个叔叔——”
“等等,”哈克特夫人僵了一下,“那是不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红衣军——以前那个。他不是也有胡子吗?马克思。他也留着胡须。”
埃德笑了起来,“这可不是卡尔·马克思。我曾经见过他的照片。”
哈克特夫人盯着他,“你见过?”
“当然,”他脸涨得通红,“那有什么问题?”
“我真的很想多了解一下他,”哈克特夫人说,“我想,我们应该了解得更多,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
“嘿,先生!要搭车吗?”
康格迅速转过身,并把手伸到腰带上。他随即放松下来。一辆汽车里坐着两个年轻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对他们笑了笑,“搭车?当然。”
康格坐进车里,关上车门。比尔·威利特踩下油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呼啸而去。
“谢谢你们让我搭车,”康格审慎地说,“我想步行到另一个镇子去,但路程比我想象的要远。”
“你从哪儿来?”劳拉·亨特问。她是个黑皮肤的漂亮女孩,个子娇小,身穿黄毛衣蓝裙子。
“库珀河。”
“库珀河?”比尔说,他皱了皱眉,“有意思。我可不记得以前见过你。”
“怎么说?你是那里人?”
“我在那里出生。我认识那儿的每一个人。”
“我刚刚搬来。从俄勒冈。”
“俄勒冈?我倒不知道俄勒冈人也有口音。”
“我有口音吗?”
“你的遣词造句有点儿怪。”
“怎么说?”
“我不知道。他确实是这样,对吗,劳拉?”
“你这是诋毁他们,”萝拉笑着说,“再多说点儿。我对方言很感兴趣。”她看了他一眼,露出一口白牙。康格感觉自己心里一跳。
“我有演讲障碍。”
“哦,”她的眼睛瞪大了,“很抱歉。”
汽车一路行驶着,他们好奇地看着他。康格也绞尽脑汁,尽量设法问他们一些问题,而又不至于显得太过好奇,“我猜,镇子外面的人,那些陌生人,”他说,“都不怎么到这里来。”
“是的,”比尔摇摇头,“不太多。”
“我敢打赌,我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个外来者。”
“我想是的。”
康格犹豫了一下,“我的一个朋友——我认识的一个人,可能会到这里来。你觉得我在哪儿可以——”他停了一下,“有没有谁可能会见到他?为了确保他过来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我可以问谁?”
他们有点儿困惑,“只要注意着点儿就行。库珀河不是很大。”
“没错,确实不大。”
他们默默开车。康格看着女孩。也许她是那个男孩的女朋友,也许是他的试婚妻。他们这个时代有试婚制度吗?他记不起来了。但这么吸引人的女孩,这个年纪肯定已经被人追到手了。从外貌看来,她大概十六岁。如果他们能够再次见面,也许他可以问问她。
第二天,康格在库珀河的主街上走过。他路过商店、两家加油站,然后是邮局。角落里有一家饮品店。
他停了下来。劳拉坐在里面,正在跟店员说着话,笑得前俯后仰。
康格推开门。温暖的空气包围了他。劳拉正在喝加了奶油的热巧克力。他坐进她旁边的座位里,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
“不好意思,”他说,“我打扰你了吗?”
“没有。”她摇摇头。她的眼睛又大又黑,“完全没有。”
服务员走了过来,“您要点儿什么?”
康格看了看巧克力,“和她的一样。”
劳拉看着康格,她双臂交叠,胳膊肘搁在柜台上,向他微笑,“顺便说一句,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劳拉·亨特。”
她伸出手,他笨拙地握住她的手,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叫康格。”他低声说。
“康格?这是你的姓还是名字?”
“姓还是名字?”他犹豫了一下,“姓。奥马尔·康格。”
“奥马尔?”她笑了,“就像那个诗人,奥马尔·海亚姆。”
“我不知道这个人。我几乎不了解诗人。我们修复了极少数的艺术作品。通常只有教会有足够的兴趣——”他停了下来。她盯着他。他脸红了。“在我们那里。”他补充说。
“教会?你指哪个教会?”
“就是教会。”他感到困惑。巧克力来了,他暗自庆幸地喝了一口。劳拉还在看着他。
“你是个很不寻常的人,”她说,“比尔不喜欢你,但他从不喜欢任何与众不同的人。他是如此……如此平凡。难道你不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应该变得……眼界更开阔一点儿?”
康格点点头。
“他说外国人应该留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不要到这里来。但你不那么像外国人。他指的是东方人,你知道。”
康格点点头。
他们身后的百叶门打开,比尔走了进来,看到了他们,“哦。”他说。
康格转过身说,“你好。”
“嗯,”比尔坐了下来,“你好,劳拉,”他看着康格,“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康格有些紧张,他能感觉到这个男孩的敌意。“有什么问题吗?”
“不,没什么。”
他们沉默下来。比尔突然转向劳拉,“来吧,我们走吧。
”“走?”她很惊讶,“为什么?”
“走吧!”他抓住她的手,“来吧!车就在外面。”
“为什么?比尔·威利特,”劳拉说,“你在嫉妒!”
“这家伙是谁?”比尔说,“你对他有一丁点儿了解吗?看看他,他的胡须——”
她突然发火,“那又怎样?就因为他不开帕卡德车,不去库珀酒吧?”
康格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孩。他块头很大——强壮魁梧。他很可能加入了某个民兵组织。
“对不起,”康格说,“我要走了。”
“你在镇上做什么?”比尔问,“你来到这里要干什么?你为什么缠着劳拉?”
康格看着那个女孩,耸耸肩,“没什么理由。稍后再见。”
他转身打算离开,又僵住了。比尔已经走了过来。康格的手指伸向腰带。只按一半,他低声自言自语。不能更多,只按一半。
他按了下去,周围的房间发生骤变。他的衣服衬里会保护他,里面有一层塑料夹衬。
“我的上帝。”劳拉举起双手。康格咒骂了一句。他本不想让她也受这个罪,但反正效果会消失的。只有半安培,令人刺痛。
刺痛、麻痹。
他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他几乎走到转弯处,比尔才慢慢挪出来,像喝醉的人一样扶着墙。康格继续向前走去。
康格在夜色中忐忑不安地走着,一个人影出现在他面前。他停下脚步,屏住呼吸。
“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康格紧张地等着。
“谁?”那个男人又问了一遍。他手里什么东西咔嗒响了一声,一道光线亮了起来。康格挪了挪。
“是我。”他说。
“‘我’是谁?”
“康格是我的名字。我住在阿普尔顿家。你是谁?”
那个男人慢慢走向他,身穿皮夹克,腰上有一把枪。
“我是达夫警长。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你谈谈。今天大概三点,你在布鲁姆对吗?”
“布鲁姆?”
“布鲁姆饮品店。年轻人打发时间的地方。”达夫走到他旁边,用手电照亮康格的脸。康格眯起眼睛。
他说:“把那东西拿开。”
片刻停顿。“好吧。”手电照向地面。“当时你在那里。你和威利特家的男孩之间有些纠纷。对不对?你们两个因为他的女孩吵了起来。”
“我们只是讨论了一下。”康格谨慎地说。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
“我只是好奇而已。他们说你做了一些事。”
“做了一些事?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他们看见一道闪光,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昏了过去,动弹不得。”
“他们现在怎么样?”
“已经恢复正常。”
一片沉默。
“好吧,”达夫说,“那是什么?炸弹?”
“炸弹?”康格笑了,“不。我的打火机着火了。液体泄漏,烧了起来。”
“他们为什么都昏了过去?”
“因为烟雾。”
一片沉默。康格挪动了一下身子,等待着。他的手指慢慢伸向腰带。警长向下瞥了一眼,嘟哝一声。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就算了,”他说,“不管怎么说,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他后退一步,从康格旁边走开,“威利特那小子总是惹麻烦。”
“那么,晚安。”康格说。他从警长身边走过去。
“在你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康格先生。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身份证吧?”
“不,不介意。”康格把手伸进口袋,拿出钱包。
警长接过来,用手电照亮。康格在一旁看着,呼吸有点儿急促。他们在这个钱包上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历史文件、古代遗物、一切可能有关的文字记载。
达夫把钱包递了回去,“好了,很抱歉打扰你。”手电光闪了闪随即灭掉。
康格回到公寓,看到阿普尔顿夫妇正坐在电视机前,他进屋时没有人抬头看他。他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他说。阿普尔顿太太慢慢转过身。“能不能问一下——今天的日期?”
“日期?”她打量着他,“12月1日。”
“12月1日!为什么?这才11月啊!”
他们两人都看向他。突然,他想了起来。在20世纪,他们仍然使用以前十二个月的体系。11月结束后立即就是12月;中间还没有加入11.5月。
他屏住了呼吸。那就是明天!12月2日!明天
!“谢谢,”他说,“谢谢。”
他爬上楼梯。他可真是个笨蛋,居然把这个忘了。根据报纸上的资料,创教人在12月2日被抓。明天,只剩下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创教人会露面,对人们发表演说,然后被拖走。
天色温暖晴朗。康格踩在融化的雪地上,鞋底嘎吱作响。他继续行走,穿过白雪皑皑的树林。他爬上一座小山,从另一侧大步走下去,边走边打滑。
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万籁俱寂,视野中完全没有人影。他从腰上取出一根细杆,转动把手。一时间什么都没发生。随后,空气中出现一道闪光。
透明操纵舱慢慢浮现出来。康格叹了口气,能再次看到它真好。毕竟,这是他唯一的退路。
他走上山脊,双手叉腰环顾周围,心里还算满意。哈德逊田野展现在面前,一直延伸到小镇边缘。这时节遍地荒芜,覆盖着薄薄一层积雪。
就在这里,创教人会出现。就在这里,他会对他们演讲。就在这里,当局会把他带走。
然而他会死在他们来抓他之前。他甚至会死在开口演讲之前。
康格回到透明圆球那里。他推开门走进里面,从架子上取下自动枪,转动枪栓,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开火。他考虑了一会儿,要随身带上这把枪吗?
不。离创教人出现可能还有好几个小时,万一在这期间有人注意到他怎么办?等他看到创教人朝这片田野走来,再来拿枪也来得及。
康格看着架子,那个整整齐齐的包裹还在上面。他取了下来,把它打开。
他手里拿着那个头骨,把它翻转过来。他独自一人,感到全身掠过一阵寒意。这就是那个人的头骨,创教人的头骨,他现在还活着的,今天会来到这里,站在不到五十米之外的田野上。
如果他看到这东西——他自己腐朽发黄的头骨——会有何反应?已经过了两个世纪。他仍然会演讲吗?如果他看到了这个东西,这个龇牙咧嘴的古老头骨,他还会演讲吗?他会说些什么,告诉人们什么?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如果一个人能看到自己古老泛黄的头骨,难道不会觉得任何努力都是徒劳?还不如在拥有生命时尽情享受这短暂的人生。
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头骨,他会忘掉事业、忘掉那些运动,鼓吹完全相反的——
外面有什么声音。康格把头骨放回架子上,拿起枪。外面有东西在动。他迅速走到门口,心跳得厉害。是他吗?是不是创教人在寒冷中独自徘徊,寻找演讲的地方?他是否正在考虑措辞、斟词酌句?
如果他看到康格手里拿的东西,不知会说些什么!
他推开门,举起枪。
劳拉!
他凝视着她。她穿着羊毛外套和靴子,双手插在口袋里。她口鼻中呼出阵阵白气,胸口一起一伏。
他们默默对视。最后,康格放下了枪。
“怎么了?”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她指着一个方向,喘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皱起眉,她怎么了?
“怎么了?”他问,“你想做什么?”他看着她指的方向,“我什么也没看到。”
“他们来了。”
“他们?谁?谁来了?”
“他们。警察。昨天晚上,警长派出了警车,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路上也设置了路障。大约来了六十个人。有些来自镇子里,有些来自周边地区,还在后面。”她停下来喘息不止,“他们说……他们说……”
“什么?”
“他们说你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说……”
康格走进操纵舱。他把枪放在架子上,然后再次返回。他跳下去,走向那个女孩。
“谢谢。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不相信他们的说法?”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不,乔开着卡车载我过来的。从镇子里过来。”
“乔?他是谁?”
“乔·弗伦奇。水管工。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们走吧。”他们穿过雪地,爬上山脊,来到田野上。一辆小型卡车停在田野中间。一个身材魁梧的矮个男人坐在方向盘后面,抽着烟斗。看到他们两人走过来,他坐直身子。
“你就是那个人?”他对康格说。
“是的。谢谢你们前来提醒我。”
水管工耸了耸肩,“我什么都不知道。劳拉说你不是坏人。”他转过身,“也许你会想知道,还会有更多人前来。不是为了提醒你——只是好奇。”
“更多人?”康格看向小镇。雪地上浮现出一个个黑色的人影。“来自镇子里的人。这种事情不可能保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镇里。我们都会收听警方的电台;劳拉会听到,他们也一样会听到。收听了电台的人会进一步把消息传开——”
那些人影越来越近。康格甚至能认出其中几个人。比尔·威利特就在那群人里,还有一些高中男孩。阿普尔顿夫妇也在其中,跟在最后面。
“连埃德·戴维斯都来了。”康格咕哝着。
商店主在田野上艰难地一路跋涉,三四个来自镇子里的男人和他走在一起。
“所有人都好奇得要命,”弗伦奇说,“好吧,我想我得回镇子里去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卡车上全是枪眼。来吧,劳拉。”
她抬头看着康格,眼睛睁得大大的。
“来吧,”弗伦奇说,“我们走吧。你是绝对不能留在这里的,你知道。”
“为什么?”
“可能会发生枪战。他们都跑过来就是为了看这个。你也清楚这一点,对不对,康格?”
“是的。”
“你有枪吗?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弗伦奇露出一丝微笑,“他们聚集了一大群人,你知道。你不会寂寞的。”
他当然在乎,好吧!他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这片田野上。他不能被他们带走。创教人随时可能出现,踏上这片田野。他会不会就是那些镇民中的一员,静静地站在田野边上,等待着、观察着?
也许是乔·弗伦奇,也许是某个警察。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走上前来演讲。这一天公之于众的只言片语,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发挥重要作用。
康格必须留在这里,在那个人说出第一个字前就做好准备!
“我在乎,”他说,“你回镇子里去吧,带上这个女孩。”
劳拉僵硬地坐在乔·弗伦奇旁边。水管工启动卡车。“看看他们,那些人站在那里,”他说,“就像秃鹫一样。等着看某个人被杀掉。”
卡车开走了,劳拉僵硬沉默地坐在车里,感到十分害怕。康格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他飞快地跑回树林里,在树木之间穿梭,朝着山脊飞奔。
当然,他可以离开。如果他愿意,随时可以离开,只需跳进透明操纵舱,转动轮盘。但他还有任务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他必须留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刻。
他跑到操纵舱那里,打开门,从架子上拿起枪。这把自动枪会好好关照他们的。他把射击控制部件开到最大。自动枪子弹连发,会击倒他们所有人,那些警察,那些好奇的、残暴的人!
他们别想抓走他!在他们抓到他之前,所有人都会死掉。他会脱身,他会逃走。今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会死,如果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他——
他看到了那个头骨。
突然,他把枪放下,拿起头骨,翻转过来。他观察着它的牙齿,然后,走向镜子。
他举起头骨,看向镜子里面。他把头骨放在自己脸颊旁边。龇牙咧嘴的头骨斜睨着他的面庞,他的头骨紧贴着他的血肉之躯。
他露出自己的牙齿,然后明白了。
他手里拿着的,正是他自己的头骨。他就是那个要死去的人。他就是创教人。
片刻之后,他把头骨放下。几分钟时间里,他站在控制面板前面,心不在焉地随手拨动。他能听到外面汽车的声音、男人们低沉的说话声。他是否应该回到原本的时代?议长正在那里等着。当然,他可以逃走——
逃走?
他转向那个头骨。那就是他的头骨,古老泛黄的头骨。逃走?在他已经亲手捧起这个头骨的时候,逃走?
即使他把这件事推迟一个月、一年、十年,甚至五十年,那又有什么区别?时间毫无意义。他已经和一个出生在一百五十年以前的女孩一起喝过热巧克力。逃走?一小段时间,也许吧。
但他不可能真正逃离,以前没有任何人真正逃离,以后也不可能有。
唯一的区别是,他曾经亲手捧起自己的头骨、自己的骷髅。
而他们不曾。
他走出门外,穿过田野,双手空空。很多人站在周围,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他们期待一场精彩的战斗,他们知道他手里有武器。他们都听说了饮品店那次事件。
而且还有很多警察——带着枪和催泪瓦斯,爬上山脊,走进树林,越来越近。在这个世纪,战斗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中一个男人向他扔了个东西。落在他脚边的雪地上,他低头看了看。一块石头。他笑了笑。
“来吧!”其中一个叫道,“你没有炸弹吗?”
“扔个炸弹!留胡子的家伙!扔个炸弹!”
“让他们吃点苦头!”
“扔几个炸弹!”
他们开始大笑。他也露出微笑,把手伸向臀部。他们突然安静下来,看得出他打算说话。
“很抱歉,”他只是说,“我根本没有炸弹。你们搞错了。”人们一阵窃窃私语。
“我有一把枪,”他继续说,“一把很好的枪,技术比你们的更先进,但我也不打算用。”
他们感到困惑。
“为什么不呢?”有人叫道。人群边上,一个老妇人正在旁观。他突然感到震惊。他以前见过她。在哪里?
他记得。在图书馆的那一天,他转过拐角遇到了她。她注意到他后大吃一惊。当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
康格咧嘴一笑。所以他确实会逃离死亡,即使他现在自愿接受死亡。他们正在笑,笑话一个有枪却不愿意用的人。但借助科学的古怪扭曲他将再次出现,在几个月之后,在他的骨头埋葬在监狱地板下面之后。
因此,他会以某种方式逃离死亡。他会死去,但几个月之后,他会短暂地再次复活,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一个下午。然而长到足以让他们看见他,明白他还活着。知道他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复活。
然后,最终,他会再次出现,在两百年之后,两个世纪之后。
他会再次出生,事实上,出生在火星上一个做生意的小村庄里。他会长大,学习打猎和做生意——
一辆警车开到现场,停了下来。人们退后一点。康格举起双手。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奇怪的悖论,”他说,“夺走生命者将失去自己的生命。杀人者死。而奉献生命者,将再次复活!”
他们笑了起来,笑声紧张而无力。警察出现,朝他走去。他露出微笑。他已经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一切。他塑造了一个美妙的小悖论。他们会感到迷惑,会记住这个悖论。
康格微笑着等待死亡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