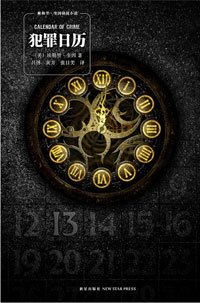保险公司代理人
这些年他每次回家都不用敲门,脚一迈上门边的毛毡门就开了。他习惯了这样,已经忘记自己安装了一个电子声控门铃。
“回来挺早的。”他妻子说道。
她马上不经意地皱了一下眉头,像是看出丈夫心事重重。这种能力百试不爽。他的情绪有一丝一毫变化她都能觉察出,但她不会直接问他任何问题,只会试图猜测是什么事情让他这么烦心。
今天,让他忧心却并不是那个卖电动玩具车的人来拜访他这件事。在公交车上,他可能担心过,但现在让他感到焦虑,甚至有点忧郁的,却是刚刚在第三层楼梯平台驻足时浮现在脑中的一件事:去年冬天,有一次他在门房室前碰巧遇到住在他们楼上的一个老太太。他揭下帽子向老太太问好,老太太说:
“麦格雷先生,您得去看一下医生。”
“我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吗?”
“不是,我压根儿就没注意您的脸色,是从您上楼的步子听出来的。这段时间您上楼脚步很沉重,走四五步就会踌躇一下。”
几个星期之后他去看了帕尔东医生,但并不完全是因为老太太的话,虽然她说的话不无道理。他该向妻子解释,他看起来满腹心事就是因为想起了这件事吗?
她还没有准备好饭菜。他不自觉地在餐厅和客厅里走来走去,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用来放小东西的喷着红漆的针线盒盖子揭开。
“你在找什么东西?”
“没有。”
他在找药。这一点一直困扰着他,让他很不安。他在想是不是真能发现什么秘密。
只是他真的没有了往常的干劲。难道他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这个阴冷的冬天,有脸色阴郁、心情不快的时候?从早上开始他就这样,并且也没有觉得这样很让人讨厌。即便是没有遭遇不幸,我们同样也可以埋怨一下,发发牢骚。
他不喜欢妻子暗地里监视着他,让实际上很清白的他感觉像是犯了什么罪。他该怎么跟她解释让她放心呢?跟她说帕尔东医生已经将她去看医生的事如实说了?
实际上,他才开始意识到,因为早上那个访客,他现在很恼怒,甚至是失落。这才是心底的小秘密,他不想向别人坦白、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小秘密。
那个自称电动玩具专家的男人,不像他在奥弗尔河岸警局见到的那些进进出出的人那么令人讨厌。他遇上了麻烦。他选择向麦格雷警长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不是随便哪个警察,而是麦格雷警长。
然而,在麦格雷警长去上司办公室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又再回到办公室时,格扎维埃·马顿已经不在了。
他没把秘密说完就离开了。为什么呢?他有急事?或者失望了?
来之前他对警长先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期待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希望能有面对面的交流。但他却碰上了一个呆头呆脑的家伙,被高速运转的散热器散发出的热气吹傻了,只知道呆呆地望着他,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还一直保持沉闷而不耐烦的表情。
可能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擦肩而过的一个背影。不一会儿,麦格雷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他在饭桌上故意谈论其他事情。
“你不觉得现在该找个女佣了吗?我们在七楼还有一个房间闲置着……”
“请她来做什么?”
“当然是做事喽。做些比较累的活儿。”
如果他慎重考虑,就不会谈论这个话题。
“饭做得不合胃口?”
“没有。只是,你太辛苦了。”
“我已经请了一个女佣每个星期过来打扫两次卫生。如果再请一个佣人,你能告诉我我每天要做什么呢?”
“你可以去散一下步。”
“一个人散步?”
“你可以找些朋友,这应该不难。”
好了!这下轮到妻子伤心了。在她看来,这就有点像是想要剥夺她最珍贵的一项特权。
“你觉得我老了?”
“我们都老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觉得……”
有些时候人们会好心办坏事。午餐结束了,他拨了一个号码,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问道:
“是您吗,帕登?”
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又做了一件很残忍的错事。他妻子正看着他,一脸惊恐,心里在念叨:难道他发现了我的秘密……
“是我,麦格雷……”
“身体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我身体很好。”
他又急忙补充道:
“我妻子也很好……听着,您现在很忙吗?”
帕尔东的回答让他觉得好笑,因为医生讲的也刚好是他想讲的,所以特别滑稽。
“彻底的安宁啊!去年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时,所有人在同一时间病了,忙得我觉都没得睡,总共不知道在床上有没有待足三个晚上。有些时候,接待室人满为患,电话响个不停。过节那段时间,有时候遇到的人呆若木鸡,有时候遇到的又是一群疯子。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够应付基本开销时,他们又都康复了。”
“我可以去见一下您吗?我想和您聊一下今天上午我在警局接到的一个案子。”
“恭候您的到来。”
“现在可以吗?”
“只要您愿意,随时都可以。”
麦格雷夫人问他:
“你确定你去不是为了自己去找他?你没有哪儿不舒服?”
“我向你发誓。”
他吻了一下妻子后就离开了,然后又折回来,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低声说:
“别太担心。我想我是刚回来时状态不好。”
他不急不忙地来到皮克布路,帕尔东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房子里面。女仆认识他,所以没有让他去接待室等,而是领着他直接经过走廊从后门进去。
“请稍等片刻,里面的病人一出来我就叫您进去。”
他看到帕尔东身着白大褂坐在里面。诊断室有些年代了,玻璃都没了光泽。
“我希望您没跟您妻子说我已经告诉了您那件事。她会记恨我一辈子的。”
“她下定决心自己照顾自己了,这让我特别高兴。但当真是一点也不用担心吗?”
“完全不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放宽到三个月之后吧,等她瘦下来几斤,她会感觉一下子年轻十岁。”
麦格雷看了等候室一眼。
“我这样直接进来没占用您病人的时间吧?”
“外面只有两个人,他们都没有什么事。”
“您认识一个叫斯泰纳的医生吗?”
“神经科医生?”
“是的。他住在当费尔—罗什罗广场。”
“我在医学院念书时听说过他,因为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后来我就没听过他的消息了。我的同门师兄弟说起过他。他是他那一届最优秀的男生之一。他以出色的成绩通过各项考试,然后成为住院实习医生,接着又做了圣—安妮岛服务部负责人。之后,他通过医学教师学衔考试。我们都预测他会成为最年轻的教师之一的。”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是他的性格。他过于看重自己的价值,会不自觉地给人一种冷酷无情的印象,甚至是傲慢。同时,他又特别痛苦,遇到任何异常情况都会产生精神方面的问题。战争期间,他拒绝佩戴黄色星形徽章,声称自己与犹太民族没有半点关系。德国人却证实事实正好相反,然后就把他送到犹太人集中营。他因此特别恼火,觉得人们因为他的出身故意为难他。这种想法其实特别荒唐,因为当时医学院有不少犹太教师。您和他有打过交道吗?”
“我今天上午给他打过一通电话。我本想从他那儿获得一点信息,但现在觉得没必要再去问他了。”
麦格雷此刻有点像他自己上午的客人,不知如何入题。
“尽管这不关您什么事,但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想法,看看您对我听到的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今天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很正常,讲话特别平缓,不夸张也不浮躁。如果我没记错,他结婚已经十二年了,一直住在沙迪伦大街。”
帕尔东点燃一根烟,很认真地听着。
“他是负责电轨列车的。”
“他是铁路工程师?”
“不是,我说的是玩具火车。”
帕尔东皱了一下眉头。
“我理解您的反应,”麦格雷继续说,“我当时听到时也吃了一惊。但是他做这件事不像是业余爱好那么简单。他是大商场玩具专区的第一销售员,另外他在节假日还负责控制陈列柜里玩具火车的运转。同时我也可以肯定,他身体状况很好。”
“他犯了什么罪?”
“没有。至少我猜测是这样。他对我说,他妻子想要杀他,并且这一想法已经萌生很久了。”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离开之前给我提供了一些细节。我只知道他在他们家放扫帚和清洁工具的壁橱里发现了一个瓶子,里面装了大量含锌磷化物。”
帕尔东听得更认真了。
“他自己分析过这个东西,他好像把所有与含锌磷化物相关的书籍都研究了一番。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份样品。”
“您想知道这是不是毒药?”
“我猜它应该有毒。”
“在一些乡村地区,人们会用毒药来灭田鼠。他有病吗?”
“时常感到不舒服。”
“他控诉谁了吗?”
“没有。他还没有告诉我他想怎样就离开了办公室。正是这一点让我烦恼不安。”
“我可以理解……他去看了斯泰纳医生?和他妻子一起……”
“不是,他一个人去的。他还在那里做了检查,那是一个月前的事了,他做检查就是想要确认……”
“确认自己神经没有问题?”
麦格雷点点头,再次点燃烟斗,然后继续说:
“我可以把他召到办公室,甚至让他在我那儿再做一次检查,因为斯泰纳医生以职业操守为挡箭牌拒绝透漏任何信息。我说我可以召他过来当然是夸张了一点,因为我没有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他来我这儿完全是出于自愿,然后向我讲述了一个有根有据的故事。他没有提出控诉,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控诉。法律没有明令禁止持有一定量的有毒物品,您看到问题所在了吗?”
“看到了。”
“他的故事可能是真的。如果我去向他的领导打听有关他个人行为的情况,我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因为大商场犹如行政机构,警察调查过的人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如果我去询问他的门房和邻居,谣言会立刻传遍整个街区……”
“您现在清楚您刚提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吧,麦格雷?您在问我对一个我从未谋面,可以说您自己也不怎么了解的一个人的看法。我只是地方上的一个医生,对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没有多少认识。”
“我记得我在您的个人图书室见过不少书籍是关于……”
“为了兴趣了解和下诊断存在天壤之别。总而言之,您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去您办公室向您讲述他的故事?”
“这是最关键之处。他继续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看起来没打算离婚。他也没要求我逮捕他妻子或者调查这个问题。当时上司叫我,我不得不出去几分钟。他就在这个时候走掉了,好像不想继续吐露内心的秘密。在您看来,这些不能说明点什么?”
“能说明很多事情。麦格雷,试想一下,如果回到我上学的那会儿,这些问题会比现在看来简单许多。不仅仅是医学,差不多所有科学都是一样。在法庭上,我们问一个专业人士,一个人是疯子还是精神正常,通常他会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您读犯罪学杂志吗?”
“读过一些。”
“那么您和我一样清楚,精神病、神经症、精神性神经症,乃至精神分裂症,这些疾病通常很难区分。如果我们再读一些海外学者的著作,就应该知道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和一个心理病态者,又或者和一个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屏障是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牢固……当然我不打算对此做一个科学的或伪科学的报告……”
“乍看起来……”
“乍看起来,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您询问的专家。比如说,电轨列车的故事,这是他的职业——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职业——但可以解释为他有点脱离现实,这一点可能导致精神性神经症。他来奥弗尔河岸警局找您,并在您面前得意地展示他的私生活,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只让一个神经科医生倾听他的故事。他去找神经科医生确认他精神正常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麦格雷还没有获得一点新的进展,因为他早就想到这些了。
“您刚刚说他一直都很平静,说话沉着冷静,看上去不带任何情绪,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任何过激的情绪,这一点看起来有利于他,但同样也可以对他不利。他早就分析了含锌磷化物,并且查阅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这一点也一样。他没有硬说他妻子快疯了吗?”
“没有这样明确表示。我记不起所有细节了。老实说我刚开始听他讲话时心不在焉。我的办公室里实在太热了,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如果他怀疑妻子有病,这同样也是一个迹象。但他妻子非常可能……”
麦格雷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真不应该插手这件事!”他咕哝道,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朋友帕尔东说。
他又立刻补充说: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管定了这事。”
“不排除一种可能,这一切仅仅是他的想象,是他自己买了这个毒药。”
“随随便便就买得到吗?”麦格雷问道。
“不是。但是他在商场可以弄到很多,比如借口用来灭鼠。”
“设想一下如果马顿先生就是您推测的这种人,那他岂不是一个危险分子?”
“他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危险分子。”
“但如果他妻子真想……”
麦格雷突然盯着医生,低声骂道:
“该死!”
随即他又笑了一下。
“请见谅。最后一句话不是对您说的。和您这里差不多,河岸警局那边也太安静了。总之就是死一样沉寂的季节。现在一个古里古怪的家伙向我提出一个请求,然后坐在我办公室,不到一会儿,就让我背负起责任……”
“您没必要负责。”
“从职业上讲是没必要。但是如果明天或者下个星期,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丈夫或者妻子,突然死了,我肯定会觉得这是我的错……”
“真的很抱歉,麦格雷,我只能帮您这么多。您希望我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斯泰纳医生,问一下他的意见吗?”
麦格雷表示同意,但是并不抱希望。帕尔东打电话到当费尔—罗什罗广场,然后电话转到斯泰纳医生现在工作的诊所。帕尔东表现得谦逊而恭敬,像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医生向一个有名的专家请教,但还是无济于事。从帕尔东的表情和对方不容置辩的声音——麦格雷之前在电话里听过他的声音,他知道帕尔东不会比他有更多的收获。
“他让我重新认清了自己的地位。”
“真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本来就应该试一试。您也别太操心了。如果所有行为异常的人都成了杀人犯或者受害者,我们会有比现在更多的活动空间和居住空间。”
麦格雷一直走到共和国大厦才上公交。奥弗尔河岸警局里,哈维尔在探员办公室里一看到警长回来就立马过来汇报情况,一脸羞愧的样子。
“他应该没在这儿见过我,不是吗?”他说,“而且我的照片也没有被刊登在报纸上啊。我长得就这么像警察?”
整个警局就数哈维尔看起来最不像警察了。
“我来到玩具专区,我根据您的描述立马就认出了他。他穿着灰色工作服,工作服上用红线绣着商场名的首字母。一辆电动火车正在运行。我看着他操控着火车。然后我对他做了个手势,问了他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完全就事问事,就像一个想要买辆玩具车给孩子的父亲。我知道这种玩具火车是什么东西,因为去年圣诞节前我给儿子买过一辆。我刚开口说了不到四句,他就打断我,小声对我说:‘去告诉麦格雷警长,派您到这儿来一点也不光明正大,他会害我丢掉工作的。’他说话时嘴唇几乎都没动,只是惴惴不安得看着在远处盯着我们的商场监督员。”
警长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实验室的检验单,上面印着几个红色大字:含锌磷化物。
麦格雷一度想撒手不管。就像他对帕尔东说的,或者帕尔东对他说的,究竟谁说的他已经记不太清了,这件事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他分内之事,如果他一再纠缠格扎维埃·马顿,只会惹来别人的埋怨,自找麻烦。
“我想派你去沙迪伦大街去向他的门房和邻居打听一下情况。记住一点,别让周围人有所怀疑,觉得警察在找他麻烦。你可以带着个电动吸尘器一家一户推销。”
哈维尔一想到要拖着一个电动吸尘器每家每户敲门,忍不住做了一个鬼脸。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装成一个保险公司代理人。”
哈维尔显然更喜欢这个身份。
“试着了解他们家的家务情况,妻子长什么样子,小区内的人怎样看待他们。如果妻子在家,你可以敲门向她推销人身保险……”
“我会尽全力的,头儿。”
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阴冷。之前警长把散热器关了,后来又忘记重启,办公室里冷得像冰窖。他扭了一下开关,犹豫着要不要去问上司的意见。不去的话,他担心自己的行动太过荒谬。他把这事告诉帕尔东时,发现自己掌握的信息少得可怜。
他慢吞吞地填烟斗,重新拿起早上搁置了的文件,但却没法再提起兴趣。一个小时过去了,黄昏到来,天空布满水汽,因而显得更加昏暗。他点亮那盏带绿色灯罩的台灯,然后起身又去调了一下再次超负荷工作的散热器。突然,有人敲门。老约瑟夫走进来,把一张卡片放在办公桌的边上,轻声说:
“是一位女士。”
老门卫肯定被她惊艳到了,所以他才会用这个称呼。
约瑟夫又说:
“我猜她应该是上午那家伙的妻子。”
他看到卡片上写着“马顿夫人”,想起了什么。称呼上面,拜访目的一栏写着:私人拜访。
“她在哪儿?”
“在等候室。我叫她进来?”
他差点儿就答应了,但最终改口说:
“不用,我自己去叫。”
他不慌不忙地穿过探员办公室,接着又经过另外两个办公室,最后来到玻璃围起来的等候室外面,站在宽敞的走廊上。天还没有完全黑,灯光看起来没有以往那么明亮,暗黄的光线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使得这里像是外省的一个小火车站。
他透过门框,感觉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玻璃鱼缸,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应该是刑警队“请”过来的,一个是拉皮条的小个子男人,一看就知道他在皮加勒区 2 工作。另外一个是体态丰满的小姑娘,悠闲自在,显然是这里的常客。
两人同时将目光投向也在等候室的另一个女人。她举止优雅,没有半点失礼之处,和这里的一切完全不搭调。
麦格雷依旧慢悠悠地走到玻璃门前,打开门说:
“马顿夫人?”
他注意到她手上挽的是鳄鱼皮包,和脚上穿的鞋子相得益彰。一条紧身套裙上面披着一件海狸皮毛大衣。
她站起来,这下所有人都懵了:一个怎么想也不会和警察有交集的人现在居然站在最有名的警察面前。
“麦格雷警长,是吗?”
另外两个人非常默契地对视了一下。麦格雷把她带进办公室,请她坐在她丈夫上午坐过的那张椅子上。
“很抱歉打扰您了……”
她脱下右手上的软面绒革手套,跷起二郎腿。
“我猜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儿?”
她首先发话,麦格雷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决定不作回答。
“可能您也会对我说保守职业秘密……”
他注意到“您也会”这三个字。这就说明她去找过斯泰纳医生。
不仅仅是态度,马顿太太的种种表现都让他震惊不已。
当然她丈夫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做事堂堂正正,生活算是很体面。马顿夫人显然也不逊色,举止高雅,不带半点矫揉造作,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半点庸俗。
他刚才在等候室就已经看出马顿夫人的鞋子做工精致,手提包奢华贵气,手套品位也不差,全身穿着都相当上档次。这不是故意炫富,也没有任何华而不实之感。她身上穿戴的所有东西应该都是出自高档名牌商店。
她看起来也是四十来岁,这一年龄段的巴黎人都一样,特别注重个人仪表。从她讲话的声音和态度,可以感觉出她是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从容不迫、应对自如的人。
“我觉得,警长先生,如果我开门见山,应该可以节省我们俩的时间。而且在您面前兜圈子也有点太自不量力了。”
警长表现得非常镇定,但这种镇定却没打乱她的阵脚,或者说她对自己的把控完美无缺。
“我知道我丈夫今天上午来拜访您了。”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不能让她一直占主动。
“他对您讲了吗?”他问道。
“没有。我见他来到了这栋大楼,我知道他肯定是来见您了。他痴迷于您侦破的案件,这些年每次谈到您他都会特别兴奋。”
“您是说您跟踪您丈夫?”
“是的。”她承认得很坦然。
突然一阵沉默,气氛有点尴尬。
“在见了他并听了他讲的话之后,您觉得吃惊吗?”
“您还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
“我可以很容易就猜出来。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了,我非常了解格扎维埃。他是非常真诚非常有勇气的一个男孩,给人的感觉特别好。您可能知道他从没有见过父母,他是由公共事业救济局抚养长大的吧?”
他微微点点头。
“他在索洛涅的一个农场长大,那里的人不让他看书,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书通通烧掉。在我看来,他很多时候都享受不到他该享有的待遇。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为他的博学感到震惊。他什么都读,什么都知道。正因为这样,别人过度地剥削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拼命工作。离圣诞节还有半年,他就开始筹备节日期间的活动,这事真把他弄得筋疲力尽。”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个银色的烟盒,但又放回去了。
“您抽吧。”他说。
“谢谢。我这个习惯特别不好。我抽烟特别厉害。我在这儿没妨碍您抽烟吧?”
他观察到她眼角有很细很细的眼角纹,这不仅没让她显老,反倒为她增添了更多魅力。蓝灰色的眼睛焕发出近视眼特有的温柔。
“您可能会觉得我们两个,我是说我丈夫和我,都特别可笑。轮流来到这里,就像来忏悔一样。其实实际情况差不多正是这样。我丈夫对我感到不安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不停工作,每天诚惶诚恐,有段时间特别消沉,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
麦格雷真希望帕尔东现在能在他旁边,没准儿医生能从她的话中察觉出什么?
“早在十月时……对,十月初……我说他看起来有点神经衰弱,需要去看看医生……”
“是您对他说他神经衰弱?”
“是的。我不能说吗?”
“您继续说。”
“我观察他很久了。刚开始,他是抱怨他们部门一个他一直都不喜欢的领导。但那是他第一次谈到部门之间的算计和密谋。之后他又开始敌对一个年轻的销售员……”
“因为什么?”
“听起来可能有些荒唐,但我可以理解格扎维埃的反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法国最出色的玩具火车专家。您可别见笑。换个说法,没人会去嘲笑一个耗尽一生只为设计内衣和减肥束身衣的人。”
他有点不懂:
“您从事内衣和紧身衣这方面的工作?”
她微笑。
“我卖这类衣服。但我刚才说的不是自己。新来的售货员总是盯着我丈夫,想从他那里学点线路设计技巧……简单点说,那个新来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想要取代他的位置……刚开始我不以为然,只是当格扎维埃的怀疑转移到我身上时,我才开始真的担心。”
“他怀疑您什么?”
“我猜他应该跟您说了。有一天晚上,他盯着我看,然后咕哝道:
“‘你想成为一个漂亮的寡妇,对吗?’
“此后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例如:
“‘所有的女人天生就是要变成寡妇的。有数据显示……’
“您看到了吧。他对我讲这些话,仿佛他感觉没有了他,我的人生会更出色更辉煌,而他就是我升华的唯一障碍……”
尽管麦格雷不带任何表情地盯着她,像是在故意对她施加压力,但是她一点也不生气。
“其他的您已经知道了。他深信我想要除掉他。吃饭时,他会将自己的酒杯和我的兑换,不仅不加任何掩饰,相反还用嘲讽的眼神盯着我。他总是等我咽了一口才吃。有时候,如果我晚回来,会发现他在厨房里到处翻。我不知道斯泰纳医生对他说了什么。”
“您没有陪他一起去?”
“没有。格扎维埃去之前跟我说过。他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挑衅。他对我说:
“‘我知道你想说服我,让我相信自己是个疯子。哦!你这一步一步的设计真是精明。等着吧,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专家会做出什么诊断了。’”
“他告诉你医生的诊断结果了吗?”
“他看完医生都一个多月了,他什么也没对我说,只是用一种自我保护的嘲讽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您明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一个人藏着秘密,而且还在心里窃喜。他会一直看着我,我总感觉他想说:‘去吧,孩子!做你想做的事。你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什么都猜到了……’”
麦格雷深吸了一口烟,问道:
“今天上午您也跟踪他了?您经常跟踪他吗?”
“不经常,我自己也有工作。平常我们一起出门,八点半从沙迪伦街出来,乘坐同一辆公交一直到金字塔路。然后我就去圣奥诺雷街的商店,而他就继续沿着勒沃利街一直走到卢浮宫商场。然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刚已经对您提过——您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两天前,他带着一种挖苦和威胁的口气对我说:
“‘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多么精明,总会有人知道的。’”
她继续说:
“我知道他指的就是您。昨天,我跟随他来到卢浮宫商场,并且在员工入口停留了一段时间,他一直都没有出来。今天上午,我又做了相同的事情……”
“您一直跟踪他到这里?”
她很直接地说是的,同时身体前倾,将烟头在玻璃烟灰缸里拧灭。
“我尽量让您大致了解情况。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回答您的提问。”
她把手放在鳄鱼皮包上,这一举动略微透漏出她有一丝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