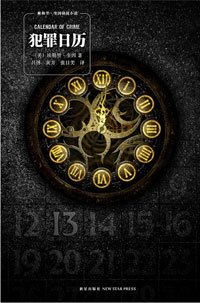电影院的那一晚
“卢卡?”麦格雷边问边把头转向两个办公室之间的传讯室。
拉波因特不单单知道警长想问什么,更清楚这个时候警长不想说太多。
“他去警察局外面接替托伦斯了,因为托伦斯对情况不是很了解……”
麦格雷没有任何暗示就换了个话题,这次,拉波因特还是能迅速地跟上他的思维。
“你呢?你怎么看?”
麦格雷除了对哈维尔一直是以你相称,一般只有在行动中,在焦头烂额时,他才会对极少数的几个人称“你”。以“你”相称总是让拉波因特非常开心,因为他感觉他们俩之间突然有某种很亲密的关系,像是在讲知心话。
“我不了解,头儿。我只是听他讲话,没有面对他,和您完全不一样……”
正是因为这样,警长才想知道他的看法。他们听到的是相同的话。但是年轻人在门后面听,没有看到说话人的表情、眼神和手势,不会被这些东西分散注意力。他就像是剧院里的女引座员,站在外面的通道上听室内的表演,引座员听到戏剧中一段段的独白时的反应和看剧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不是疯子?”
“他面对的是您,所以肯定会有点言不达意……”
拉波因特本来还犹豫要不要说这句话,他担心警长可能会误解他的意思,因为他觉得这样说好像在拍马屁。
“您再重新看您最后的几个问题,就会更理解我的意思。”
“最后有什么?”
“他应该是在撒谎。这只是我的看法。他小姨子应该知道他来这里。他也知道她知道。他不知道的是她跟踪到了这里,还在警局外面等他。我想应该是这一点让他很生气。您希望我现在就把审讯记录打出来吗?”
麦格雷摇头,然后说:
“我倒希望直到最后你都没必要打出来。”
他开始有点着急,卢卡怎么还没有上来呢?他应该不会一直跟踪他们俩到沙迪伦街。警长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吃惊。拉波因特对这一点也特别好奇。
“我想不通,”探员说,“为什么他要假装小姨子不知道他来我们这里呢?”
“他可能有他的理由。”
“什么理由?”
“他不想把她牵扯进来,不想她有一天被控告为帮凶。”
“就算她是同谋,那也只是……”
拉波因特突然不说话了,惊讶地看了上司一眼。麦格雷说那话前提就是肯定事情已经发生,格扎维埃·马顿现在处境不利。他来不及再说话,因为外面传来匆忙而短促的脚步声,肯定是卢卡回来了。他穿过探员办公室,来到警长办公室,从微开的门缝中探进半个身子。
“头儿,我可以进来吗?”
他披着一件黑色的绒布料外套,外套上还有几片细小的白色的雪花。
“外面下雪了?”
“刚开始下。雪不大,但是打在身上感觉挺疼的。”
“说说情况。”
“警察局外面的那个年轻的女人和我一样被冻得不行了,并且她还是穿着一双很薄的皮鞋,我听到她不停地跺脚。刚开始她一动不动地站在石围墙旁边,不想被人发现。尽管我只看到她的侧影,但是从她站立的姿势,我猜她应该是一直盯着这几个灯火通明的窗户。这个时候整栋楼没几个房间还开着灯。我也是盯着上面看,看着房间里的灯一个一个地熄灭了。一会儿之后,我听到从上面传来声音。我之前从没意识到我们从里面走出来时发出的声音可以传那么远。探员们三三两两从里面出来,互相道别,分手离开……
“她一点一点地朝这边靠拢,像是被您办公室的灯光吸引,并且看起来越来越紧张。我很肯定她好几次都有横穿马路冲进来的冲动……”
“难道她觉得我拘禁了马顿?”
“我不清楚。最后他终于出来了,一个人经过门口站岗的警察走了出来。他立刻环顾四周,像是在找某个人……”
“他在找小姨子。我之前告诉了他,她在外面。”
“原来是这样,现在我明白了。要想看见她可不容易。他首先往新桥方向找,但是她却站在相反的方向。他又往回走。我觉得马顿背对着她时那女的是想离开的,或者赶紧下到码头上躲起来,但她刚动一下就被他发现了。我听不清他们讲了什么。从他们的表情,我猜马顿首先是在责备她。虽然他没做什么,但是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非常生气。
她主动把手伸过去挽起他的手臂,还对他指了一下站岗的警察,然后引着他向圣米歇尔桥走去……”
“等一下,”麦格雷打断他,“她是怎么挽马顿手臂的?”
卢卡看起来有些茫然,不解警长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但正处于恋爱中的拉波因特却很理解。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像我们在街上看到的所有女人挽着丈夫或情人一样自然。他应该后来又责备了几句,但语气没那么强烈了。之后我猜想他是发现了她有点冷,所以用手搂住她的腰。两个人的身体也更加靠近。他们差不多是以同样的步子、同样的节奏向前走……”
拉波因特和麦格雷对视一眼,想着同样的问题。
“走到圣米歇尔桥,他们踌躇了一下,然后穿过车流,走进拐角的一间酒吧,这期间马顿一直搂着她的腰。酒吧吧台前坐了很多人。刚进去先得喝开胃酒。我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看着他们,没有走进去。他们俩站在账台前。服务员调好了一杯掺热糖水的烈酒,放在女人面前,但她看起来不大愿意喝。马顿坚持要她喝。最后她还是喝了,边吹边喝,而他呢,却只要了杯咖啡。”
“对了,”麦格雷问拉波因特,“他中午在餐馆喝的是什么?”
“矿泉水。”
他问这个问题还真有些费解。如果有人问麦格雷这个问题,他也肯定相信这位玩具火车爱好者既不喝红酒,也不喝烈酒。
“他们出来后,”卢卡最后说道,“就直接走向公交站台,然后站在那儿等车。我看着他们上了去奥尔良地铁站方向的车,我想我该回来向您报告一下情况。我做得对吗?”
麦格雷点头。卢卡身上的雪已经化了,因为他交代情况时就一直在烤火。
警长对他也是以“你”称呼。
“今天晚上你有安排吗?”
“没什么特别的安排。”
“我也没有。”拉波因特迫不及待地说。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该让你们俩谁去他们家外面守着。要守到大半夜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年轻的拉波因特把手举起来,像一个小学生。
卢卡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轮流监视呢?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妻子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我在蒙鲁日教堂对面的酒吧买个三明治就可以了。之后,拉波因特可以来代替我……”
“我十点钟可以过去。”拉波因特表示。
“你们可以再晚点儿。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以凌点为交接点呢?”
“我可以早点开始。既然不睡觉,我想多做点事情。”
“还有什么指示,头儿?”
“没有了,好伙计。下次上面下达报销费用的通知时,我一定把这次监视行动报上去。你们监视的两位,妻子和丈夫都来过这儿。他们俩都过来向我讲了一些他们之间的琐事。按道理说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正因为这样……”
他没有说完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该怎么说。
“可能我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知道他妻子来过。我犹豫过。但是我想……”
他耸了耸肩,显然已经被这件事弄得有些烦躁,然后他过去打开放外套和帽子的橱柜,一边咕哝道:
“不管怎样,我们等着瞧……晚安,伙计们……”
“晚安,头儿。”
卢卡又说:
“我一点钟过去。”
外面,天更冷了,冷得刺骨,细而硬的雪花絮团在路灯的光晕中看得清清楚楚。有些轻轻地飘落在人的皮肤上,像是想要深入到里面去,有些则落在睫毛上、眉毛上、嘴唇上。
麦格雷受不了这样的刺骨寒风,不敢冒着这样的冷风等公交,所以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坐在车后座缩成一团,用厚厚的外套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他以前做的所有调查和这次的调查相比,现在看来真的太简单,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游戏,但他被这件事搞得挺恼火的。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不相信自己,还打电话给帕尔东医生,还去找了局长和检察长,现在又祈求得到拉波因特的赞同。
他感觉自己陷入了僵局,不知所措。汽车绕过共和国广场时,他突然想到一个解释,这倒让他安心不少。
这次调查和以往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次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发生,他只是虚构了一件随时可能发生的罪案?
要是最后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好了!有多少犯罪行为一触即发,有些还是精心策划过的犯罪,但最后都没有真的发生?有多少人想要除掉某个人,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但在最后一刻却放弃了?
他之前查过的案子一下子全浮现在脑海中。有些案子因为缺乏有利时机,有时候是缺乏一次机会,一直都查不出结果。还有一些案子,如果一定时间内受害者没有说某句话,表明某种态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一次他不是让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人的行为重现,而是要预测犯罪者的行为,这也是案子更难做的地方。
那些关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的专著并没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
他也认识很多其他夫妻,其中有些夫妻中的其中一位会因为某个原因想要另一个人死。
之前的病例也没有什么借鉴意义,那些病例只对专业人员,或者在遇到狂躁症患者,尤其是那些以前杀过一次或几次人、悔改了又重犯的狂躁症患者时才有点价值。
出租车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路口。司机对他说:
“先生,我们到了。”
家里的门还是和往常一样开着,麦格雷看到了灯光,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家具和物件摆放在原来的地方,这些年从没变过。
麦格雷夫人看着他。夫人和以前一样,知道他很忙时从来不会问他问题。
“我们去看场电影怎么样?”他提了个建议。
“外面在下雪。”
“你怕着凉?”
“不是。去看电影我当然很开心啊。”
她猜想他应该是不想和昨天晚上一样坐在沙发上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一小时之后,他们向共和国广场和新好景大道走去,麦格雷夫人挽着她丈夫的胳膊。
格扎维埃·马顿的小姨子热妮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是在马顿惊讶地发现她在警察局外面等他时。麦格雷想不起来他们第一次相遇之后多久妻子开始挽着他的胳膊。
离电影院还有一百米左右,他还不知道今天放映的是什么电影。他问了妻子他们何时挽着胳膊这个问题。
“我知道啊,”她微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们认识三个月之后。那之前一个星期,在楼梯台阶上,你拥抱了我。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同样的地方,你都会拥抱我。一个星期二,你带我去了喜歌剧院,那次上演的是《卡门》,我穿着一件蓝色的塔夫绸料子的长裙。我还能说出我当时喷的是什么香水。一直到上出租车你都没有牵我的手,只有在扶我上车时才握住我的手。
“看完戏之后,你问我饿不饿。之后我们去了布尔瓦大道,那时布塞餐馆还在营业。
“我穿着高跟鞋,所以假装差点儿绊倒,借机抓住你的胳膊。当时我真是很胆大,大胆到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一直在发抖。而你呢,你倒是挺聪明的,装作什么也没注意到。
“从餐馆出来,我就挽着你的手,从那以后,我每次都会挽着你。”
也就是说,热妮也同样是出于习惯。所以他们,也就是她和她姐夫,经常一起这样走在路上。
这能说明他们毫不避讳。但马顿夫人真的如马顿先生所言,对这些完全知情?
他来到售票窗口买票,然后拿着两张红色电影票向入口走去。
正在放映的是一部警匪片,有枪战和打架斗殴的场景,主人公非常胆大,从窗户跳到一个敞篷车上,光天化日之下杀了司机,抢了他的车,一路狂飙,把在后面警报大作的警车甩出好远。
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至少现在,他是在娱乐放松。看电影时他可以暂时忘记马顿夫妇和那个小姨子,忘记那个叫舒沃博的哈里斯先生,还有他们两对情人中不知哪一对更多的纠结而复杂的琐碎事情。
幕间休息时他去买了点糖果给妻子,就像麦格雷夫人挽着他胳膊这一举动一样,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习惯。同样,妻子吃甜点时他就去大厅抽半斗烟,边抽烟边随随便便瞟一眼下场电影的宣传画。这也是一个习惯。
外面雪还在下。他们出去时,絮团越来越厚了,雪落到地上微微颤抖一下才慢慢融化。
他们低着头走路,不让雪花飘到眼睛里面去。明天,屋顶应该会是白雪皑皑的一片,汽车也都只能停在家里。
“出租车!”
他怕妻子着凉。他感觉她已经消瘦了不少,所以特别担心。帕尔东建议她减减肥,所以麦格雷也做不了什么。他觉得妻子会越来越瘦弱,可能还会变得不再那么乐观,心情不如以前。
车子停在他们在里夏尔·勒鲁瓦大道的家门前,他小声说:
“我凌晨一点回来,你不会不太高兴吧?”
平时,他不会问她这个问题。他只会简单地告诉她一声。而今天晚上,他却多问了这句本没必要问,甚至完全没理由问的话,他只是自己觉得有必要向她道歉。
“要我等你吗?”
“不用了。你先睡吧。我一点钟可能都回不来。”
他看着她穿过人行道,然后在包里找钥匙。
“圣皮埃尔·德·蒙鲁日教堂。”他对司机说。
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地面很滑,汽车曲折行驶后留下很宽的轨迹。
“别开太快……”
他在想:
“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感觉很快就会有事情发生?格扎维埃·马顿昨天来找他。不是一个星期前,就是昨天,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没有变化。这预示着一个悲剧已经发育成熟了吗?
吉赛尔,她也是昨天来到河岸警局的。
而她丈夫今天又来了。
他试图回忆他昨天看的关于精神病学的那本书上关于这个问题说了什么。他当时应该更认真些。书里面有好些关于病情演变的篇章,他直接跳过没有仔细看。
或者,如果真有悲剧,有一点可能会加速悲剧的产生。格扎维埃·马顿愿意明天上午十一点过来接受警察局拘留所专门医疗所的检查。
他会跟小姨子讲吗?会跟妻子讲吗?他妻子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在圣奥诺雷路的情人吗?
等到做完检查,不管结果怎样,再观察事情的进展似乎都有点太晚了。
出租车停在教堂门口。麦格雷付了车费。对面有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酒吧,里面只有稀稀疏疏三两个客人。麦格雷推门进去,点了一杯加糖加热的烈酒,他并不是想要喝点热的取暖,只是刚才有人提到过加糖加热的烈酒,所以他就点了这个。他向服务台走去时,服务员叫住他:
“您想来点筹码吗?”
“我只想看一下电话簿。”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电话簿。一想到哈里斯先生,他立马想到,马顿家有电话吗?他只是想确认一下。
他们家没有。电话簿上有很多姓莫顿的,姓马丁的,就是没有一个姓马顿的。
“多少钱?”
他来到沙迪伦街上,街上特别空旷,只有一两个窗户还有灯光。他既没有看到卢卡,也没有瞧见拉波因特,他开始有点担心。在马路中间,靠近安托万·尚坦路的地方,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里,头儿……”
是年轻的拉波因特,他缩成一团蜷在墙角,围巾盖住半张脸,手藏在大衣口袋的最里面。
“您绕过街道转角处时我就听出您的脚步声了。”
“是那里?”警长指着前面那栋黄色砖墙的楼,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是一片漆黑。
“是的。您看到门右边那个漆黑的洞了吗?”
“那应该是个死胡同,我们在巴黎,甚至是巴黎市中心经常能看那种通道。在圣马丁大街上一个类似的胡同里,我们以前抓获过一个杀人犯,那次是下午五点左右,就在离人行道上的人群几米开外的地方将他抓获的。”
“那条路通到院子里面?”
“是的。人们可以从那里进进出出而不惊动门房。”
“你去看了?”
“我每隔十分钟就去看一次。您进去时得当心。里面有一只体型很大的红棕色猫,它会悄悄钻出来,在您的腿旁边窜来窜去。我第一次进去时,它喵了一声。我生怕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睡了?”
“刚刚才睡。”
“他们做了什么?”
“我不清楚。刚才房间里面灯还亮着,这样望过去看得到有一个人站着,但是有窗帘挡着,什么也看不清。我看了窗帘一会儿,但白费力气,只看得到一个黑色的古怪的身影。可以肯定的是,房间里面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一直在里面没动。要么就是在房子最里面,从外面看不到。一楼的灯也亮着。刚开始我还没有注意到,只是后来自动百叶窗动了一下,透出几束微弱的光线,我才发现。”
麦格雷穿过马路,拉波因特跟着他。他们俩都蹑手蹑脚,以免弄出任何声响。这个巷子上面有一个三到四米长的穹顶,里面又冷又潮湿,就像个地窖。院子里面黑压压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站着不动,结果真有只猫跑过来,但没有在警长身上蹭来蹭去,而是围着拉波因特,就像一只围着主人撒娇的家猫。
“他们睡了,”探员小声说,“您面前就是之前亮着灯的那个房间。”
他踮起脚尖走到一楼的百叶窗前,凑上去看了一下,然后转身回到警长旁边。他们两个正准备转身离开,突然,一束光射过来,不是从下面这个独栋房子发出来的,而是四楼的一个房间灯亮了。
两个人都不敢动,呆呆地杵在那里,生怕已经被四楼的住户发现。他们以为有人正贴着窗玻璃往外瞧。
结果窗玻璃上什么也没有。一个黑影从窗帘后面经过。接着他们听到冲水的声音。
“原来是尿尿……”拉波因特舒了一口气,顿时安心了。
不一会儿,他们又回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奇怪的是,他们俩都一脸失望。
“他们真睡了。”
难道这就说明什么也不会发生,警长是在瞎担心?
“我在想……”麦格雷刚开口说。
这时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直接朝他们俩奔过来。他们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人行道旁边站着两个人,很大声地朝他们嚷:
“你们俩在那里搞什么呢?”
麦格雷迎过去。手电筒的光束射在警长的脸上。那个警察皱了一下眉头。
“您不会是……哦!对不起,警长先生……刚才没认出您来……”
他看了对面的大楼一眼,然后又说:
“您需要什么帮忙吗?”
“现在不需要。”
“听您差遣,我们随叫随到。”
穿风衣的两个人说完就走了,衣服上落满雪花。麦格雷转身走到拉波因特身边,他一直站在原地没动。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您说您在想……”
“啊!是的……我在想他们夫妻俩还是睡在一张床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下午哈维尔跟我说过,他们在一楼有一张沙发床,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一定有人睡在这张沙发上。就算沙发有人睡,按道理也应该是他小姨子,不是吗?”
“晚安,老兄。或许你可以……”
他在犹豫要不要干脆让拉波因特回去睡觉。傻傻地守在一个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房子前面有什么用呢?
“如果您是因为我而犹豫……”
实际上,如果不让拉波因特继续完成监视任务,他会非常恼怒。
“如果你愿意,就继续监视吧。晚安。你不想去旁边喝一杯?”
“在您来之前几分钟我刚从那个咖啡酒吧回来。那个地方在街道转角处,我坐在里面也可以监视街上的动静。”
麦格雷走到圣皮埃尔·德蒙鲁日街时,地铁的栅门已经关了,街上看不到一辆出租车。他不知道该朝贝尔福狮像那个方向走,还是经迈内路往蒙巴纳斯地铁站方向走。他选择走迈内路,因为那里有地铁站。但是立马他就拦到一辆刚送完客往回走的空出租车。
“里夏尔·勒鲁瓦大道。”
他出来时忘记带钥匙了,但是他知道门毡下面有备用的。作为警长,他从没想过把这个小秘密告诉妻子。
她正熟睡,警长怕惊扰她,所以只是开了走廊上的灯,借着一点微弱的光准备宽衣睡觉。一会儿之后,床上传来一个声音,问道:
“现在很晚了吗?”
“不清楚。差不多一点半……”
“你没着凉吧?”
“没。”
“我去给你倒一杯药茶吧?”
“不用了。我刚喝了一杯加热加糖烈酒。”
“那你待会儿还出去吗?”
这些家常他已经听了不下一百遍,但是今天晚上,他却有点震惊,因为他在思考吉赛尔·马顿是不是也曾经说过相同的话呢?
或者说,这些话她只对她丈夫讲过吗?
“你可以把灯打开。”
他只把他这边的床头灯打开,然后出去把走廊的灯关了。
“大门关好了吗?”
几分钟之后,他妻子起身去确认门是否关好了,这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或许格扎维埃·马顿也期待过夫妻之间的这种心照不宣,只是从未得到过……
他缩进温暖的被子里面,熄了灯,给了妻子一个晚安吻,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这已经成为习惯,不用费什么劲儿。
他本以为自己会很难入睡,结果他很快就睡着了。并且,如果灯突然亮了,我们会发现他睡觉时双眉紧锁,表情严肃,像是正在调查一个稍纵即逝的真相。
通常麦格雷夫人六点半准时起床,悄无声息地离开房间去厨房,他在旁边熟睡完全不会察觉。而他总是闻到咖啡的香味后才意识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个时候,里夏尔·勒鲁瓦大道上其他人家的窗户也陆续打开。巴黎的街道上,早起去上班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这一天,他不是被咖啡的香味吸引,也不是被妻子轻微的动作惊醒,而是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铃声一下子将他从夜晚的世界中拉出来。他睁开眼睛时,麦格雷夫人已经坐了起来,摇着他肩膀。
“现在几点了?”他含糊不清地说。
她摸着去按床头灯开关,灯光照在闹钟上,指针指着六点十分。
“喂!”麦格雷睡意蒙眬地拿起电话,“是你吗,拉波因特?”
“是麦格雷警长吗?”
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他皱了一下眉头。
“请问您是?”
“这里是警局求救中心,我是若弗尔警员。”
遇上特殊情况,警局求助中心会向他提供一些信息,好直接提醒他可能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次他自己都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接到这个电话他惊讶不已。
“什么事,若弗尔?是因为拉波因特吗?”
“什么拉波因特?”
“是拉波因特让您给我打电话的吗?”
“我没有收到拉波因特的消息。只是刚刚有人打电话过来,让我们通知一下您。”
“通知我什么?”
“让您现在去一趟沙迪伦街……请稍等一下!我还记下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知道了。是谁打的电话?”
“我不知道。他没有留下姓名。”
“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她还说只要一说您就会明白,并且您也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她在电话簿上找过您的电话,只是没找到……”
麦格雷的电话没有登记在电话簿上。
“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警长没有立即回答。他差点儿就想让若弗尔以他的名义给第十四区警察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个人去沙迪伦街。但是他想了一下,觉得还是算了。他坐在床边,脚在地上找拖鞋。而他妻子这会儿已经在厨房了,他听到燃气灶啪嗒啪嗒的声音,他妻子应该是在烧水。
“没有了,谢谢。”
他不解的是,为什么不是拉波因特给他打电话呢,他应该就在那里。
若弗尔说的女人是谁呢?吉赛尔·马顿?还是她妹妹?
如果是她们俩中的一个,那她肯定没有出那栋楼,因为拉波因特就在外面守着。她如果出了大楼,拉普安肯定就会发现,然后给麦格雷打电话。
又或者,马顿夫妇没有电话。
他叫了一下妻子。
“我现在要穿衣服,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电话簿,查沙迪伦街十七号的用户是谁?”
他本还想刮一下胡子,但是为了节约时间他决定不刮了,尽管他最受不了胡子拉碴就出门。
“十七号……看到了……是……”
“好的。这说明他们住的地方还是有电话的。”
“上面还有一位布萨尔夫人,是助产士。就这些。还有两分钟,你想来点咖啡吗?”
他应该叫若弗尔给他派一辆河岸警局的警车过来的,但是又想到打出租车可能更快。
麦格雷夫人早就为他叫车了。他迅速喝完咖啡,匆匆下楼,刚冲的咖啡快把他的嘴皮烫破了。
“待会儿给我打电话?”他妻子倚靠在楼梯扶手上问道。
她很少这样问。她应该是感觉到他这次比以前更加焦虑不安。
他向妻子保证:
“我尽量。”
出租车到了。他立即钻进车里,然后才发现雪已经不下了,路面上和屋顶上也看不到白色的雪迹,只有淅淅沥沥的冻雨模糊了前行的道路。
“去沙迪伦街。”
他吸了一口气,车子里面还有香水的气味。显然司机刚载过一对在酒吧过夜的情人。一会儿之后,他弯下腰捡起了一个红色的小棉球,应该是零点之后有头有脸的人物狂欢时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