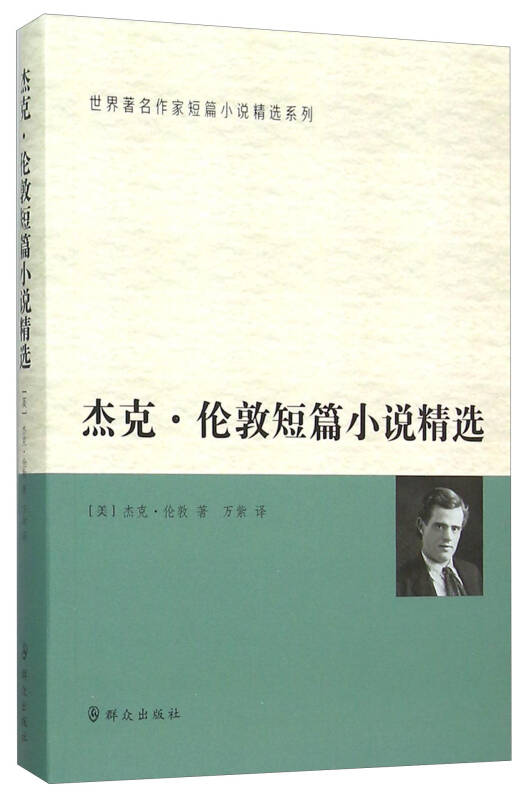她走得很快,好像发现有人在跟踪她似的。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她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踉踉跄跄。她那么疯狂,就像个突然意识到自己粗心大意的游泳者,疯狂地朝沙滩游去,因为他只有在那里才安全。
就是这样。她快要跨进门厅了,在那里,迎接她的是旅馆改造成的报社内部的特殊的庄严感;她的鞋底又踩到淡黄色石板上面粗糙的碎石;她在楼梯最下面的黄铜柱球上看到了缩小变形的自己。她的手从光滑的楼梯上划过,感受到一种身体上的满足;再往上走,等走到那个永远都不变的同一个台阶上时,她就要停下来在包里找钥匙了,而每次在找钥匙时,她都会有一种淡淡的担忧,因为她总是不能马上找到钥匙,然后就半信半疑地想着是不是把钥匙弄丢了。
她终于到家了。还没有走到客厅,但是已经在她蛰居的那个唯一的房间里了。有时候她真希望这个房间可以变得再小一些,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包裹住她了。
她把门反锁。她很累,喘着气,在镜子前停下。那是她经常停下站立的地方,她试图找到自己的影像。
以前,别人都叫她尼克,她自己也这么叫自己。但是现在,除了她自己,还有谁会这样叫呢?她对尼克这个名字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在镜子里面看到那个曾经跟着萨莱夫妇去各个驻地的自己,看到童年时候的自己,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
不,她还不是老处女。她的脸上的皱纹还不是很多。尽管她天天待在家里,但是皮肤保养得很好。她的皮肤从来都色泽暗淡,但非常细腻。多米尼克还记得妈妈总是会用细微变调的嗓音说:
“尼克脸上有勒布雷夫妇的面痣。至于那个像门一样高的发髻,则是跟她沙尤祖母学的。”
人们在街上毫不羞耻地展现着活力,多米尼克刚从这种猛烈的嘈杂声中走出来,想到一些祖先的名字,觉得好了些。这些不仅仅是名字,而且是她曾经参与过的那个世界里存活过的人的标记,而她崇拜那些人。
那些名字的音节带着色彩和香味,还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她的嘴里还有街上灰尘无以名状的味道。在多米尼克重新拥有的这个房间里,几乎所有的名字都可以通过一个东西来表示。
房间里没有座钟也没有闹钟,只有一块金子做的小手表放在床头,表壳上镶了一朵珍珠和红宝石粉做的花,这块表是沙尤祖母的。多米尼克想起雷恩郊区的一大片房子,当时所有人都称其为城堡。
“我们不得不卖掉城堡的那一年……”
作为手表配饰的是一只镶着绿色、蓝色和黄色花边的红色丝绸,丝绸上绣着母骡。是尼克绣的,她当时七八岁,在尼姆的耶稣圣天修道院上寄宿学校。
她点燃煤气,在桌子的一头放上一张纸巾当作桌布。现在街上的人应该大部分都在公寓里吃晚饭,至少那些没有出去度假的人家里是这样。但是多米尼克在安托瓦妮特·鲁埃家没有看到任何人。
她总是不停地想到安托瓦妮特,为了避免痴迷她,多米尼克想要玩思考的游戏,一半有意识,一半无意识。她以前也这么玩过。
这种游戏要求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必须要有感恩之心。譬如,每天早上,由于要忙家务,她不可能做到感恩。而从某个规定好的时刻开始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是做一个能自己叫醒自己的梦一样,她不能按照指令做梦,顶多可以慢慢地进入一种利于做梦的状态。
沙尤这个词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一个关键词,但还有其他的,譬如克莱芒蒂娜阿姨……每天上午快十一点,早上的清凉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中午的大太阳,这个时候,克莱芒蒂娜阿姨就开始感受自己皮肤的气味……
他们住在土伦附近拉塞讷的一栋别墅里……克莱芒蒂娜阿姨的丈夫——她是布列塔尼人,嫁给了一个沙比龙人——是土伦一家兵工厂的工程师……多米尼克曾在她家里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她在种满含羞草的花园里读书;在阳光的照耀下听着造船厂机器的喷气声;她只要站起来,透过一排吊车和推车,就可以看到一隅湛蓝湛蓝的海;这一切都停滞了,组成了一个非常密集的整体。但正午时听到工厂汽笛撕裂般的响声与锚泊地轮船的汽笛声遥相呼应是一种解脱。随即而来的是工人们走过平交道口时的踏步声。
克莱芒蒂娜阿姨还活着。她的丈夫很早前就去世了。她一个人一直住在那栋别墅里,和一个老佣人住在一起。多米尼克想象着自己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位,包括那只本不该继续存在的橙黄色的猫。她重新安置着每个角落……
突然,她颤抖了一下,因为她正假装着在夜间看护生病的爸爸,她觉得听到床上传来了非同寻常的叹息声。她有点不知所措,她没有看到老将军那张毛发浓密的脸,他的目光总是表现出一种冷冰冰的指责。
“给我烟斗好吗?”
他在床上抽烟,不刮胡子,很少洗脸。他仿佛是故意把自己弄得这么脏,故意要把自己弄得臭烘烘的,然后他还会带着一种着了魔的满足感说:
“我开始发臭了!承认我发臭了吧!既然这是事实,承认吧!以上帝的名义,我发臭了!”
现在,卡耶夫妇又回到了爸爸的那个房间。她再也不需要假装思考了,不需要再找幻想的主题了。对面有安托瓦妮特和鲁埃父母。在与她只有一门之隔的隔壁,那两个年轻人拉着空行李箱回来了。
他们在干吗?那些她还没有习惯的搬家具的声响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应该做这个的。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吃晚饭。为什么他们不去看电影,或者看话剧,又或者去舞厅呢?她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他们哼着舞厅的那些陈词滥调。
他们在装水桶,水龙头开得很大。他们完全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任凭水漫得满地都是。和他们在一起,她总是害怕发生类似的灾难,因为他们不尊重这些物件。对他们而言,一个物件,不管是什么,都可以被替代。这个值多少多少钱,仅此而已。但是多米尼克会因为小地毯上或者窗帘上的一个小污点而感到无比不安!他们在讲话,但是搬东西的声音太大了,多米尼克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奥古斯蒂娜已经在窗边了。她来上班了;对她来说,这是真正的上班:她几乎不厌其烦地把身体的重量压在阁楼的窗户上;她穿着一件绘有白色细小图案的黑色上衣;白色的头发在晚上紫红色的阴影下显得格外明显;她站在那里,心平气和地俯视着街道和房顶。过了很久以后,一扇又一扇的窗户旁边才挤满了人,那些人在一天结束之际来床边纳凉。
多米尼克也窥探过老奥古斯蒂娜,在那些忧伤的日子里,当镜子里显现出一副疲惫的样貌,一双有黑眼圈的眼睛,和没有色泽的嘴唇时,当她感到自己老了时。
老奥古斯蒂娜是怎么开始窥探游戏呢?她四十岁时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她在做什么呢?
毫无疑问,老奥古斯蒂娜的故事会随着她的死去而完结。多米尼克没有设想关于葬礼的任何细节。
“谁啊?”
不,她没有说出这句话。她是有这个疑问。因为有人敲门。她担心地看了看周围,想着可能是谁来敲自己的房门。她惊讶得没想到是卡耶夫妇。多米尼克才走了几步路,那人又敲了一次门。她轻轻地转动钥匙,没有发出声音,好像门没锁一样。然后她又瞥了一眼镜子,确认自己的穿着打扮没有一丝不妥。
她笑得有点抽筋,因为见到人时需要微笑。
她又回想起妈妈,妈妈的笑容里带着一种无尽的忧伤。
“笑容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能把生活变得如此美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点努力就好了!”
是阿尔贝尔·卡耶。他看上去很不好意思,也在努力微笑着。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她想:
“他是来通知我他们要走了……”
卡耶还算有家教,但还是使劲地看着多米尼克居住的房间里的一些隐蔽角落。他对什么感到吃惊吗?卡耶对她拥有其他房间却只待在这一间房里感到吃惊吗?卡耶对房间里只有家具和不配套的老旧物件感到吃惊吗?
“我们收到了我岳父母的来信。他们要从丰特奈—勒孔特过来,明天上午十一点到。”
卡耶脸红了,多米尼克感到很吃惊,他在生活中总是那么的从容不迫。她注意到他的表达方式带着孩子气:想要某个东西,又害怕遭到拒绝,然后用嘟嘴和眼神来请求对方。
他真年轻啊!多米尼克从没注意到他这么年轻!在他身上,在狡猾后面,还有某种单纯。
“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解释……我们之所以还没有搬进公寓房,是因为我的情况可能一天一个样……您懂的……我岳父母习惯了外省舒适的生活……这是我们结婚以来,他们第一次来看我们……”
她刚才没有想到要请他进来。现在,她请他进来,但他还是站在门口,她猜莉娜在门外面等他,顺便听他们谈话。
“我真的希望不会给他们留下太差的印象……他们待一两天就走,因为我岳父不能长时间不管他的生意……在此期间,您能不能允许我们使用一下客厅,就像是我们的一样……我会另外支付房租的……”
多米尼克听出“付钱”那个词就要脱口而出,但是卡耶犹豫了一下,改成“支付房租”。
“另外,我们从早到晚都不会在家……我岳父母会住宾馆……”
他以为多米尼克犹豫了,然而多米尼克是在想:
“卡耶把我当成老处女吗?他觉得我老吗?在卡耶看来,我是一个女人吗?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个谁的女人……”
她眼前又浮现出自己好几次透过锁眼看到的场景,她很苦恼。她觉得自己很丢人,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一个男人,不管是谁……但是,要知道,一个男人,譬如卡耶,可能会有那种想法……
“我妻子还希望……”
他说了“我妻子”,但他的妻子是一个还未完成的创造物,她的体型还不是很分明,就像是一种可以发声的填充布偶,有着孩子般的嘴唇,会对着一切人和物笑,露出牛奶一样白的牙齿。
“我妻子还希望,那两天房间里的布置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不用害怕……我们会恢复原貌的……我们会很小心的……”
由于刚才那些想法,多米尼克都不敢看他了。她觉得卡耶能明白……
譬如说,卡耶敢走近她吗?卡耶敢伸出手,不断深入,就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吗?卡耶应该天生就对女人的肉体感到好奇。
卡耶笑着,眼神恳求着,让人心疼。她说:
“你们想怎么改呢?”
“如果……如果您不是很介意,我想把床板去掉……哦!我习惯了……我们会买一张沙发床,然后把床垫放在地上,用我们带来的套布盖着……您明白了吗?”
就跟对面的布置一样!是不是太巧了?今天早上,安托瓦妮特·鲁埃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如果真的这么改,她家就会和对面一样了,多米尼克觉得自己明白了:他们不想只把床当成休息的工具,而是想把它变成更加肉欲的东西,他们把它和其他目的、其他姿势统一了起来。
“那么,您同意吗?”
她感觉到腋下又一次湿了,这种潮湿的热热的感觉使她睁不开眼。她快速说道:
“好吧……就这样吧……”
然后她改变了主意,但只是补充说道:
“注意别弄坏东西!”
他们会因为这个重复的命令笑话她的。他们会说:“这个老处女害怕她那四件家具和老旧的窗帘……”
“再次由衷地感谢您……我妻子会很高兴的……”
他走了。多米尼克看到客厅里一张蜗形腿桌子的大理石台面上放着一抱花,很香,正等着插在花瓶里。
“千万别把它们放在蓝色的花瓶里,那个花瓶裂了,水会溢出来的……”
卡耶微笑着。他很高兴。他快速地跑到莉娜身边。
“别怕……”
他们要整夜制造噪音了:她会听到用水桶装水的声音,洗东西的声音,拖地的声音,给家具打蜡的声音。她两次微微推开客厅的门,看到阿尔贝尔·卡耶挽起衬衣的袖子忙着做家务。
她必须紧紧地关上门,才能有一丝是在家里面的感觉。她轻轻地趴在窗台上,很随意,好像只会趴一会儿似的。她没有老奥古斯蒂娜那种静默的力量,可以坚定地在原地待几个小时。街上很宁静,基本上没人了。一个很瘦的老先生,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溜一只小狗,每次小狗停下,他也停下,不厌其烦;奥德巴尔夫妇坐在店门前;多米尼克能觉察出来他们一天都动来动去的,很热,他们只有片刻的休息时间,因为丈夫早上四点就要到哈雷。他们的保姆手里总是拿着奶,头发总是贴在脸上,坐在他们旁边,两只手臂摇晃着,眼神空洞无物。她可能只有十五岁,却有着女人很丰满的乳房,就像莉娜的一样,或许比她的还要大。谁知道是不是已经……
绝对的!和她的老板!奥德巴尔是最令多米尼克反感的男人。他那么健壮,热血沸腾,多米尼克好像能感觉到他的血液在大动脉里有力地跳动着,他的眼睛里面有一种健壮野兽般的狂妄。
有时候,从奥斯曼大街上传来一些声音:是一群在街上行走的人,他们讲话很大声,像在对着全世界说话一样,根本没有考虑到趴在窗台上或迈着小步乘凉的那些人。
灯光是赤褐色的,房子闪着黄铜般的光泽,一个红褐色的烟囱好像在流血一样。这些颜色,在黑暗的衬托下显得异常深邃;那些丝毫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好像是自生自灭的;白天结束了,一切似乎缓慢了下来,这个时候,人类有的在弱化,而物体开始呼吸,开始展现它们神秘的存在。
安托瓦妮特房间里的窗户刚刚关上。多米尼克瞄到塞西尔的黑色裙子和白色围裙。就在那一秒,她看到那张遮盖起来的神秘的床。然后窗帘就拉上了,只透出一片模糊的玫瑰色灯光,是那个刚刚放到独脚圆桌上的玫瑰色灯罩造成的。
罪犯安托瓦妮特已经睡了吗?就在她头顶,鲁埃妈妈坐在座椅上,旁边是她的丈夫。多米尼克只看到了她丈夫那双锃光发亮的拖鞋、杂色的短袜以及裤脚,他的一只脚放在窗台的扶杆上。
他们不慌不忙地聊着天。有时是这个老妇人说,多米尼克可以看到她的嘴在动;有时她不说话,转向房间里面,听丈夫说话。
多米尼克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希望人们一个一个消失。首先消失的是奥德巴尔夫妇,他们拖着椅子走在人行道上,关窗户上的铁格时还制造出嘈杂的金属碰撞声。然后是左侧四楼的皮具商苏东家里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除了知道她有一个孩子以外,多米尼克对她一无所知。多米尼克经常看到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照顾得非常好,还不停地弯下腰去亲吻他,但是他现在应该生病了,因为至少有两周没看到他来床边了,医生每天上午都会去他家。
是的,多米尼克希望一切都可以消失!她甚至想看到那些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就像冬天那样。但在这个季节,有些人是开着窗户睡觉的,因此她觉得自己能听到从那些房子里传出来的睡觉的声音。有时候多米尼克的幻觉特别强烈,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睡梦中,有人刚刚回到她那潮湿的床上。
多米尼克俯视街道,她可以看到十字路口那棵大树的一部分,一个交警恰巧正在那里无聊地散步,除了玩弄他的白色棍子,不知道做什么。同每天早上一样,那棵树上的鸟儿们恢复活力,等待最后一丝红褐色的光延伸开来,一侧的天空变成与夕阳截然不同的玻璃绿色。夜晚的柔美逐渐呈现出来时,那种活力则逐渐消散。
她不困。她很少感觉到困。卡耶夫妇的大扫除使她很生气,颠覆了她的世界。她每次听到响声就会颤抖一次,担心着同时也在想着为什么安托瓦妮特睡那么早。在经历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以后,她怎么能够睡得着,甚至平静地入睡。几天前,就在那个房间里,她的丈夫满身血汗,绝望地叫喊着寻求帮助。他的声音极小,连一只被丢在草丛里大口大口呼吸的鱼都不如。
整点钟声和半点钟声回荡在圣菲利普·杜鲁莱上空。白天所有的光亮都消散了,对面房顶的棱角上出现几只白鹭,月光马上就会从房顶后面显现出来,不过现在她还看不到。这种情景使多米尼克想起南锡的大广场,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首先亮起的是那些弧光灯投射出的一样冷冷的光,很刺眼,直穿瞳孔。
肥胖的奥古斯蒂娜回去了。她回房间了,窗户也关上了。她会重重地倒在床上。上帝啊,她穿的是什么睡衣啊?多米尼克看到她身上穿着难看的衣服,短上衣、衬裤,还有一条沾满体味的绒布衬裙。
多米尼克没有开灯。一束光通过门底下的缝隙从卡耶夫妇房间里透进来,他们的窗户是开着的,透过窗户投射到黑暗街道上形成的矩形光线更加明显。
他们熄灯时已经是一点钟了。对面安托瓦妮特房间里面玫瑰红色的灯光也熄灭了。楼上的鲁埃夫妇已经睡下了。
就剩多米尼克一个人了,她看着圆圆的月亮,那是一轮不近人情的圆月,才刚刚从距离一个烟囱上面几厘米的地方升起来。天空太明亮了,如同一块密合又亮堂的毛玻璃橱窗,多米尼克很难分辨出星星,记忆中的那些话语又响在她的耳畔:
……夜里,在沙漠深处,被一颗子弹打穿心脏而死……
只有这样的天空才能让她想到沙漠。大地、天空以及穿行在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里的月亮,都透露出一种同样的孤独……
……面对二十个狙击手组成的人墙……
她转过身。尽管很黑,她还是能猜出缝纫机的罩布上面放着的是一本做弥撒的书,封皮上裹着一块黑色呢绒保护套。这本祈祷书是她初领圣体时得到的。一张上了色的羊皮纸下面有一幅图,羊皮纸上有几个镀金字母,是她名字的首字母。
书里面的另一幅画面是葬礼。
热纳维耶芙·阿梅罗夫人,生于奥热,
虔诚地逝世于……
故事发生在安古莱姆。她爸爸那时候还只是上校。他们住在一个四四方方的浅黄色大房子里,有一个铁铸的阳台,窗帘是杏仁绿色的,窗户面向一条大道,那里有一条骑兵专走的小路,一到早上五点钟就能听到军营的号角声。
阿梅罗夫人是住在隔壁的一个寡妇。她很瘦小,迈着小碎步,别人都说:“像阿梅罗夫人一样温柔……”
她会对每个人微笑,对十五六岁的尼克更是由衷地想笑。她经常把尼克带到客厅里,然后在那里度过无聊的几小时,她好像并没有猜到这个年轻女孩子之所以情愿蜷缩在她家里,是因为她的儿子雅克。
但是多米尼克只有在雅克请假时才能看到他,因为他一直在圣西尔。他留着寸头。脸色总是很沉重。声音也是。多米尼克很奇怪像他这么年轻的一个男生声音竟然这么低沉,他嘴唇上面甚至还没有长出胡须来。但是他的声音很低沉。
“尼克……”
是的,多米尼克默默地喜欢了他三年,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心里用尽全力爱着他。
雅克知道这件事情吗?阿梅罗夫人知道多米尼克为什么天天出现在她家吗?
有一天晚上,有人邀请将军去做客。宴会上有窖藏了很久的白兰地,有利口酒,还有肉桂饼干。雅克穿着陆军少尉制服,他第二天就要去非洲。
灯罩是玫红色的,和安托瓦妮特卧室里面的一样,窗户朝向大街开着。她看到月光映照在法国梧桐的枝干上,枝干因此变得很明亮;她听到兵营里响起熄灯号。
多米尼克是最后一个出来的。阿梅罗夫人悄悄地走掉了;萨莱上校在人行道中间抽着烟等尼克。后来,雅克握着她的手时,她一阵眩晕,小声说道:
“我会永远等您的……永远……”
一种想哭的冲动涌上心头,她抽出手,然后走远,挽住爸爸的胳膊。
仅此而已。另外还有一张明信片,那是她收到来自于他的唯一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在沙漠边缘一块干涸土地上拍的。有一个貌似中国人的哨兵,还有月亮,在晦暗的月亮旁边,用水墨写着几个字,后面还加了一个感叹号:
这是我们的!
同一轮月亮照亮了安古莱姆的每个夜晚,也正是在这轮月亮下,雅克·阿梅罗在沙漠里被一颗子弹打穿心脏。
多米尼克把头伸到窗户外面一点点,她想要感受一下掠过房子的凉风,但是马上就红着脸缩了回来。隔壁窗户里传来小声说话的声音,她很熟悉的声音。原来他们还没睡!房间收拾好了,花插在花瓶里,灯熄掉了,一切都令他们鼓舞。最让多米尼克震动的是,一个雌性动物发出的虽然压抑但清晰的急促笑声。
多米尼克想睡觉了。她退到房间最里面脱衣服,尽管房间里没有灯光,但她雪白的身体在黑暗里显得楚楚动人。她赶快披上衣服,告诉自己门已经关上了。她钻进被窝时,看了对面窗户最后一眼,发现安托瓦妮特正趴在那里。
她可能睡不着。她又打开了玫红色的台灯。在灯光的映照下,多米尼克看到了那张用来睡觉的乱乱的沙发床,被脑袋压得扁扁的枕头,绣花的床单,一本打开的书,还有杯子里一支燃烧着的烟蒂。
房间里有一种无精打采的纵欲的气氛,多米尼克躲在窗扇后面,窥探着清晰地显现在月光中的安托瓦妮特。她那棕色的头发没有扎起来,散落在像牛奶一样白的肩膀上。在一件柔滑如丝的精致睡衣衬托下,她的身体显得很丰满,多米尼克以前从未在她身上发现过这种丰满。一个词蹦到她的嘴边,就一个词,“女人”,她觉得这是自己第一次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安托瓦妮特向前弯下身子,两条胳膊扶着铁栅栏,于是她的胸蜷缩着落在白白的胳膊上,两个乳房轻轻地往上动了动。多米尼克看到了她敞口的衬衣里面乳沟的黑影。下巴也是圆圆的,好像是放在一块软软的鼓出的赘肉上面。
之前姐妹俩面对面时,多米尼克断定妹妹更漂亮。但现在,她明白自己错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怒放的生命体,她刚从清凉的夜里走出来,站在永无止境的黑夜和一个泛着玫红色灯光的房间之间。就像一个悬浮着的生命体,她是为某种东西而生的,她的所有神经都向往着这种东西。这一点,多米尼克很确定。多米尼克被那双盯着天空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凄凉目光触动了,多米尼克感觉到一声叹息充斥在胸腔和喉咙里,最终经过一阵不耐烦的抽搐之后,从肉肉的、嵌满牙齿的嘴唇里释放出来。
她确信自己搞错了,她像一个笨蛋一样被牵着走,不是像个孩子,而是像个笨蛋,老处女笨蛋。她很羞愧。
她为那封信感到惭愧,那个幼稚的秘密就像小学生自娱自乐的秘密。
右侧的那个江边刺葵
在寄出信之后的这几天里,面对安托瓦妮特的镇静,多米尼克迷失在自己的推测里。她想过安托瓦妮特还没收到那封信,或许安托瓦妮特还不知道那种绿色植物的名字!
对安托瓦妮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就在刚刚,多米尼克相信自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打击——是的,她的动作里面带着某种恶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恶意,而是一种隐约的正义的本能——又或者是嫉妒?——不管是什么——刚刚,就像一个兴奋的老处女一样,她已经潦草地写好了另外一封信。她原本打算要残酷一些,用自己的笔在她的肉体上抓出道道伤痕。
您很清楚您杀了他!
她是这样写的吗?当然不是!
您杀死了您的丈夫。您很清楚。
安托瓦妮特知道这件事吗?这不是很重要!没有什么比那个活生生的肉体从泛着玫红色灯光的沙发床上下来更重要了,她在那里一动不动。窗边这个女人平静的外表下,只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向着必须要过的生活大踏步迈进的欲望。
多米尼克光着脚站着,像个罪犯一样躲在窗扇后面,她的脸变红了,她什么都不明白,关于对面发生的一切,她只看到了最表面的一些细节。今天最让她高兴的,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这些:一个危险的婆婆的出现,一个无聊的公公的外交举止,安托瓦妮特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随意,偷偷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妈妈的钞票,以及柔和的灯光,贵重的丝绸睡衣,还有插在长长象牙烟嘴里的那支香烟。
多米尼克很在意别人的生活,却忘记了要为自己的生活活着。她灼热的眼睛盯着窗边的那个女人,盯着她那双迷失在夜空里的眼睛。多米尼克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个更加活跃的生命,一个喜爱战斗的生命。多米尼克感觉到了血液在动脉里跳动,一阵眩晕袭来,她一下子倒在床上,她的头埋在软软的枕头里,以压低那撕心裂肺的无力吼叫。
她就这样待了很久,身体僵直,牙齿紧紧地咬住床单,床单都被口水弄湿了,一个想法萦绕在她的脑海。
“她在那里……”
多米尼克不敢冒险动一下,不敢转身,等待着最细小的声音结束这种苦难,然后告诉自己她已经解脱了。过了很久,卡耶夫妇准备相拥而眠了,传来长插销乏味的咯吱声。
她终于可以抬起头,转头九十度。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扇关着的窗户,窗帘灰暗的衬里,和一辆驶过的出租车。然后,她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