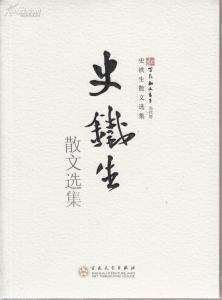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
今天学《西山经》第二山系。我念一句,你念一句。
西次二山之首,曰钤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铁。洛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多白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其木多杻橿,其鸟多鹦。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银,其下 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磬石、青碧。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陽多赤铜,其陰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其陽多黄金,其陰多铁。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泾水,其中多美玉。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其兽多牛、羬羊、白豪。有鸟焉,其状如雄鸡而人面,名曰凫徯,其鸣自叫也,见则有兵。西南二百里,曰鸟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其陽多檀楮,其中多女麻。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铜。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垩,其陰多碧,其兽多牛,麢羊。又西四百里,曰薰吴之山,无草木,多金玉。又西四百里,曰厎陽之 山,其木多、栟、豫章,其兽多犀、兕、虎、犳,牛。又西二百五十里,曰众兽之山,其上多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黄金,其兽多犀、兕。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 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黄。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蕙棠。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 其陽多金,其陰多铁,其兽多麋、鹿、牛。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莱山,其木多檀、楮,其鸟多罗罗,是食人。凡西次二山之首,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为席,其十辈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鸡,钤而不糈。
※※※
有什么要问的?
问:石涅是什么?
答:黑石脂,古人用来画眉的。
问:那时就画眉?
答:古今一样。现在说失眉瞎眼,没有眉就没眼。
问:青也是一种染料石吗?
答:是。
问:哎呀,有金银铜铁玉,又有青碧、雄黄、石涅、丹砂,这第二山系十七山中这么多的矿石?
答:这里是泾渭流域呀!泾渭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必然是气候湿润,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矿产丰富么。
问:不是常讲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吗?
答:泾渭是黄河的主要支流,讲黄河其实讲的是泾渭。
问:这里奇木怪兽似乎少了。
答:矿藏多,金克木,当然草木就少。人是以发现冶炼、利用矿藏而发达的,人一发达,怪兽肯定要远避了。
问:怎么没有石油,连煤炭也没有?
答:石油和煤炭是深地层的,当后来开发它的时候是促进了人的生活,但同时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知道潘多拉盒子吗,人类从此在污染中生存。
问:怎么只写到地,而几乎从未写到天?
答:前边不是写到天帝吗?天帝就是天上之神,有天在上了,地在下才有了草木和禽兽么,这如说母亲和孩子,那肯定就有父亲。上古人对天的认识是天无 私,比如日月星辰,不管你是人是兽,是穷是富,是美是丑,它都关照,比如风雨雷电,不管你高山深谷还是江河平原,它都亲顾。它的无私像人的呼吸一样,重要 到使你感觉不来它的重要,而你就常常觉得它的不存在。仰观天以取象,提升人的精神和灵魂,俯察地以得式,制定生存的道德法则。此书是写地理的,当然尽写到山川河流的物事。
问:白首赤足的朱厌“见则大兵”,状如雄鸡而人面的凫徯“见则有兵”,兵指战争、杀戮吗?
答:是指战争和杀戮,也可以是指专政。
问:那时也有专政?
答:有人群就有了阶级。前面的几章里多处提到“天下”“县”“郡”,应是已有了国家,一切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
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你见过冬季里村人用细狗撵兔吗?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边成百条细狗在撵,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成百只,因名分未定。有了名分,统治就要有秩序…
※※※
我就是在多少年里没有了名分,在县文工团里度日如年。
作为唱师,我不唱的时候在陽间,唱的时候在陰间,陽间陰间里往来着,这是我干的也是我能干的事情。但是,徐副县长介绍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党 的文艺工作者之后,我的光荣因演不了那些新戏,也唱不了新歌而荡然无存。在长达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的日子里,我隐瞒着我的过去,任人嘲笑和轻视,只是县文工 团的后勤杂工,即便上台,也就在一折戏结束了把幕布拉合,一折戏又开始了把幕布拉开。多少个下雪的冬夜,我在县城小酒馆里独自喝酒,以往事的记忆作下酒 菜,喝得醉醺醺而回,脚下咯咯吱吱的踏雪声是我在怨恨着那个独眼。我永远要感念着匡三,匡三当年让我的命运改变,而几十年后还是他,又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 运。
那一年的秦岭地委,那时还叫作地委,如今改为市委了,要编写秦岭革命斗争史,组织了秦岭游击队的后人撰写回忆录。但李得胜的侄子,老黑的堂弟,以及 三海和雷布的亲戚族人都是只写他们各自前辈的英雄事迹而不提和少提别人,或许张冠李戴,将别人干的事变成了他们前辈干的事,甚至篇幅极少地提及了匡三司 令。匡三司令阅读了初稿非常生气,将编写组的负责人叫来大发雷霆,竟然当场摔了桌子上的烟灰缸,要求徐副县长带人重新写。但是徐副县长就在这年秋天脑溢 血,半个身子都瘫痪了,匡三司令便说:那个唱师现在干什么?他是了解历史的,把他找出来让他组织编写啊!这我就脱离了县文工团,一时身价倍增,成了编写组的组长。
我们重新调查重新撰写,便到了三台县过风楼镇,过风楼镇已经叫作了过风楼公社,公社书记老皮,是匡三司令还在山陰县当兵役局长时秘书的表弟。老皮的 名字有点怪,后来才听说他出生时像个老头,脸上的皮很松,家里人为了好养他,故意起了难听的名字。老皮参加革命工作很早,调到哪儿都要找个固定的人为他理 发,头皮松,脸皮更松,刮脸就得把脸皮拉平,常常是拉了一个腮的皮了,整个脸就挪了位。老皮并不以为皮松有什么不好,说:老虎皮就是松的,它走路时看上去 皮就像披了一张被单。于此,他走路也讲究慢,步伐沉重。他到过风楼公社当书记已经多年,工作能力强在全县都有名,现在过风楼镇上人还在说他初来时祭风神的 事。
过风楼的风大,历来都有在立夏时祭风神的活动。老皮正好是那日上任,晚上全镇人敲锣打鼓集合在下溪滩,放了十二通火铳,老皮以书记身份出场主祭。他 先问:人带上来了没有?派出所所长回答:带上来了!派出所所长身边就站着了两个人,一个红衣红裤拿着一把木头刻成的刀,一个黑衣黑裤脸上涂了锅灰。祭风神 是要以人祭的,以往都是将装扮成黑衣黑裤的犯人带到挖好的坑前,由装扮成红衣红裤的刽子手用木刀在犯人后脖上一抹,表示砍去了人头,而将准备好的猪头羊头 抛进坑里埋掉。但老皮那时却多问了一句,他问那个黑衣黑裤的犯人:哪个村的?那犯人说:我是小学的教师。老皮说:怎么让教师当犯人呢?寻个是地富反坏右的 不好吗?!大家都觉得新任书记的建议好,可这样的活动都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参加的,再去村里找已来不及,有人就喊墓生,把墓生从人群里推出来。这墓生又 瘦又小,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墓生就装扮了犯人,穿上黑衣黑裤。黑衣黑裤太大,墓生穿上裤腰就到了胸前,他不停地挽裤腿,派出所所长说:好啦好啦,这不是 去行门户!把墓生拉去跪在了坑边。老皮很庄严地走到一张桌前,对着纸扎的风神焚香,叩拜,开始读写好的祭文。祭文一读毕,刽子手就砍犯人头了,墓生却把鞋 脱下来放在脖子上,说:叔,呵叔,你不要用劲,刀就落在鞋上。刽子手是没用劲,刀在鞋上一点,骂了句:你狗日的!把猪头羊头给了墓生,让他自己往坑里扔。墓生抱着猪头羊头说:这就是我的头?!惹得大家哄然笑了。笑声中老皮讲了一段话,所有人都记住了,那话是:我们祭风神,祈求立夏后再不要刮大风,愿今年的庄稼丰收。但是,我们要整风,整治人的风气!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促进生产,力争在三至五年,过风楼要焕然一新,改变长期落后面貌,成为我县我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这些当然是我们采编组到了过风楼公社以后才知道的,我们去的那天,老皮先派了墓生去倒流河岸口等候,要求一发现我们就立即跑去报告他。但我们已经到 了公社大院,墓生才满头大汗地跑来,手里拿着一颗桃子,报告说没有看到有穿四个兜的人呀,他是看到河畔的桃林里结了颗大桃子便给书记摘回来了。老皮把桃子 扔了,踢上他一脚,骂道:滚!我忙解释我们并没有经过河岸口,是从县城到的茶岭公社,从茶岭公社翻山过来的。我看见墓生抬起头来,扑闪着眼睛,给我笑了一 下。他笑得很好看,右嘴角上还显出个小酒窝。我说:你是谁?他说:我叫墓生。我说:什么,墓生?老皮说:他爹他娘被槍决时,他娘已经一头窝在沙坑里了却生 出了他。我哦了一声,又问:今年多大?墓生说:十七啦。我说:十七岁啦怎么倒像是八九岁的孩子?!墓生说:我不长。是他不长还是他长不大,我还要再问他, 老皮就不耐烦了,说: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墓生就不吭声了,退到一边。老皮又说:再远!墓生躲在了树后。
这是我第一次来过风楼,来了才知道过风楼并没有楼,是镇子东边三里地有两座崖,像是楼,中间是进镇里去的路,路成了风道。因为风硬,过风楼的鸡掐仗时鸡毛就全翻着,像两个毛团滚过来滚过去。羊也爱斗, 常常是主人牵了羊在路上碰见了,它们就牴起来,还会在风里各自退后几步,然后低头紧跑着冲过去,两只羊头撞在一起,合着风发出很大的响声。牵羊的人年纪都 大了,却乐意在一旁看,风把尘土吹进口鼻也不在意,待到终有一只羊被撞倒在地上,头上流着血,又爬起来往上冲,那边的主人说一句,血头羊了你还斗?这边的 主人不爱听,两人就吵起来,最后也纠缠在一起动了手脚。路过的外乡人看见了,就感慨:两个坏人长老了!过风楼实在不是个好风水的地方,庄稼低矮,树也长不 到三丈高,不是到一丈多就生横枝,便是长到桶粗了树身就开裂,往出流一种黑水。所以在镇中最高的一个山头上建了一座道观,要镇压从崖楼过来的风的煞气。但 道观里已经十多年没住道士了,只住了老皮。老皮还是要敲那口铁钟,只要钟声一起,山下镇街和四周沟岔里的村子,鸡鸣狗叫全都听不见了,墓生就会急死急活地 从山坡的石阶往上跑。
墓生脑袋小眼睛却大,啥都见过,就是没见过他爹他娘,别人说他爹是个铁匠,解放后东岭沟几户人家和农会主任打架,就是他爹给打的刀。农会主任被打死后,那几户人家被定为反革命暴乱,他爹他娘当然也被牵涉进去。槍决时,他爹求饶,说他压根不知道人家要做刀去干什么,他只是个铁匠,如果不杀他两口,他们当牛当马养活农会主任的家人。但他爹他娘还是被槍决了,他的叔抱养了他。十二岁上叔又过世,他成了孤儿,过风楼的人就认为他能活下来是替他爹他娘还罪的,说:你是牛呢还是马?你叫叫!他真的就叫了,叫的是牛声,引逗得旁边牛棚里的公牛母牛全都叫了。他学牛叫学得像,谁见了谁都让他学牛叫,叫过了,问:你该不该学牛叫?他说:该。样子很乖。因为他乖,慢慢人们就不觉得他是反革命的儿子了,喜欢使唤他,拿他取乐。
老皮曾经在别的公社当过书记,为了改变过风楼的落后面貌,组织上把他特别调来,一来就住在公社的上院。上院就是山上的道观,作为家不在镇街的干部的 宿舍,办公却在山下的院子里,称作下院。一到晚上,山上的风大,树林子起涛声,上院聒得人睡不着,又特别冷,一些干部就搬到下院去了,老皮始终住在上院, 后来把办公桌也搬上来,就在上院里办公。他不怕冷,夜里不在屋里放尿桶,还要起来两次去厕所。厕所在后院角,是在悬崖上用木头伸出去搭一个棚,人蹲在木头 上屙尿,粪落不到崖下就散了。但白天站在门外的台阶上四处看,能看得见过风楼的整个盆地,老皮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站在那里,尤其在钟声敲响后,声音在崖和林 间冲撞,他在轰轰嗡嗡的音响里俯瞰着,想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就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挥动。
老皮确实是个工作狂,从没有个上下班概念,也不理会星期天,常常是三更半夜里突然想起什么了,就给下院的办公室摇电话。办公室必须二十四小时要有值班的,让把干部叫醒到上院来开会。每次开会,他都讲一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讲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是工作布置和讨论人事安排。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大家的意见没按他的意思了,他就不表态,吃卷烟,卷烟的味道很呛,别人都吭吭咔咔的,他不咳嗽。开到最后没个结果就宣布散会,而隔一天半天了再开会,仍是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讲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讨论人事安排。若还未达到他的意思,就又是不表态,吃卷烟,宣布散会。如此三番五次,终于符合了他的意思,他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那就这么定吧。后来要再开会,凡是有决策,干部们发言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 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讲了一通,似乎这些词就在喉咙里舌头下,张嘴就来了,至于决策的事,说:书记你定吧。这时候老皮要说:那我就民主集中制啦。宣布了决策, 然后他要给大家发散卷烟,嫌卷烟味太重吃不了的,他说:拿上!把卷烟别在人家的耳朵上,说:咱们的会议开得严肃也要活泼么!于是有人就喊:墓生,墓生你进 来学几声牛叫吧!墓生有时就在院门外坐着,用玻璃片儿刮锨把,他把老皮的锨把刮得光溜溜的,磨不了书记的手,有时墓生却到山下背泉水去了不在院门外。墓生的牛叫声学不成了,这些干部就和老皮开玩笑,说:书记,你怎么精力这么过人呢?跟着你干工作,忙得上厕所尿都尿不净,这裤裆里就没干过!老皮哈哈笑,脸上的松皮就抖动着。
老皮的精力过人,传出来的是他长着重瞳眼和双排牙。他再到各村寨去,就有人暗暗观察,但他总戴着个大片子眼镜,看不清是不是重瞳,而肯定的是并没有 双排牙,只是牙不齐整,有歪后的有突前的,一口乱牙。公社伙房的炊事员最了解书记的牙不好,吃什么都往牙缝里钻,所以每次饭后他都要准备牙签。这事让县委 书记知道了,就送给了他一根老虎胡子。这老虎胡子是县委书记在省上开会时参观了老虎园得到的,老皮就特意做了个小竹筒儿装了,每吃完饭,取出来用胡子根尖 剔牙,少不了大家都要近去看稀罕,老皮是只许看,不让动。
※※※
这一天,是雨后的早晨,草里拱出了蘑菇,石头上也长了苔藓,啄木鸟敲敲这棵树又敲敲那棵树,声音很大,老皮还没有醒来。往常的老皮天一亮就起来了, 而且一开院门,也要求墓生必须就在门外,但这头一天晚上多喝了些酒,门开得迟,而墓生已经在台阶上瞌睡了。老皮用脚踢,说:醒来,醒来!墓生睁开眼,立即 用手拍打台阶,怨恨台阶让他瞌睡了,再是指头蘸了唾沫湿眼皮,要让自己清亮。老皮说:学学牛叫,一叫就灵醒了。墓生就学牛叫:哞——!墓生一叫,啄木鸟的 声没有了,四下沟沟岔岔里村里的牛都在叫,哞声像滚了雷。
墓生开始干他每日首先要干的事了,就是从书记的办公室拿了一面红旗,跑到上院后的山头上,那里有一棵婆椤树,把红旗插到树梢上。据说几百年前道观很 大,山门,牌楼,大殿,从公社下院那儿一直盖到山头,婆椤树就是道观的标志。婆椤树每年在苜蓿开花的时候它也开花,花是紫色的,结的果却是白色,一旦结了 果,镇上的人就要去看,说哪一树股上果子结得多,树股子朝着的方向庄稼便会丰收。但是,自从每日插起红旗了,差不多的三年里,婆椤树再没结果。棋盘村的刘 少康私下给王耀成说过金克木,意思是红旗上印着斧头和镰刀,斧头和镰刀属金,所以伤着婆椤树不结果了。而王耀成当时也点头称是,过后却把这话报告了老皮, 老皮拍了桌子,下令把刘少康送去了学习班,以后谁也不敢说婆椤树的事了。
插红旗是老皮来到过风楼后决定的,他学习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每日升红旗的做法,要镇上的人一抬头能看到红旗了,激发一种革命的激情。当时因婆椤树是过风楼最大的树,树身直立光溜,公社里的干部没人能爬得上去,插旗的就是一只红屁股 的猴子。那猴子是西沟村一个卖老鼠药人养的,他卖药的时候让猴爬竿烘场子,老皮组织了在全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不允许任何村民外出,那只猴子就没收 了,训练着上树插旗。可这猴子一年就病了,老皮想起祭风神时被装扮砍了头的墓生,着人把墓生叫来爬树让他看,墓生爬树竟然比猴子还快,这就是墓生最初被留 下来的原因。
墓生拿着红旗往山头跑去,他能跑,也不穿鞋,脚底有茧子,那已经不是茧子了只一层很厚很厚的死肉。别人爬树是头朝上抱着树的,他头朝下,双手在下边 使劲。爬到树梢了,把红旗插好,觉得天上的云离得很近就伸手去抓,没抓住云,倒抓下来了一节枯枝。但这枯枝不是枯枝,当他发现枯枝节处还有亮晶晶的小眼睛 时,才知道是一只竹节虫。过风楼四周的山上是有很多竹节虫,他见过有的是苔藓一样的,有的是树叶一样的,连叶面上被虫啃过的缺口和霉变的斑纹都一模一样, 可他还是第一回见到完全是枯枝的竹节虫。墓生想让老皮也瞧瞧稀罕,把枯枝竹节虫拿到了上院,老皮正在炉子上热了水洗头。墓生说:书记理发吗?老皮说:把枯 枝扔了,去搬凳子拿理发工具呀!墓生赶紧放下竹节虫,去搬来凳子拿了推子刀子,让老皮坐好了,开始理发。他说:书记,那不是枯枝,是竹节虫。老皮说:哦。 墓生说:咱这儿咋有这么多的竹节虫?老皮说:过风楼的工作之所以难搞,就是人也都会伪装么!墓生吓了一跳,他不明白书记为什么会说这话。老皮却又说:你喜 欢这虫子?墓生说:这,这我只是没见过它长成这样。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喜欢竹节虫,墓生就把竹节虫扔到院墙角去,还过去用脚踩了踩。老皮笑了一下,说:“理 发,理发!老皮的头好理,因为老皮是秃顶,墓生每次理的时候都想说书记把脸长在了头上,但他没敢说过,而给老皮刮脸就难了,老皮的胡茬很硬,简直是把头又 长在了脸上,为了能把腮帮子上的胡茬刮净,他把腮皮一拉,老皮的整个脸全移过来,墓生就有些害怕。
理过了发,老皮坐到办公桌前要办公了,点着卷烟,一支铅笔在手里转过来转过去,最后夹在左耳朵上。墓生却跑到院墙角去看他踩烂的竹节虫,看了很久,脑子里嗡嗡响,刨了土把竹节虫埋起来。也就在这次脑子里嗡嗡之后,墓生的身体开始了一些变化,这变化后来越来越严重,使他惊恐和痛苦。
老皮在敲桌子了,敲三下,这是老皮在叫他,墓生赶紧问:书记啥事?老皮说:把这张登记表送给野猪寨的村长去!墓生说:噢,噢。却把扫在一起的老皮的头发胡须包成小纸包,扔上了房顶,书记的毛发不能随便扔的。
墓生从上院跑下来去了野猪寨,沿途有人问:哎墓生书记干啥哩?墓生说:看文件哩。再问:是啥文件?墓生说:红头文件。墓生总是能把老皮的活动说给村 寨里的人,村寨里的人就可以判断老皮会不会来村寨检查工作。看红头文件那就是县委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必然要开干部会的,于是他们就趁机拿了土特产如鸡 蛋、蜂蜜、核桃、柿饼去县城或黑市上出卖,也有把自家碾出的大米拿到更深的山里与那里的人换包谷或土豆,一斤大米能换三斤包谷,也能换三十斤土豆,这样就 可以多吃一点了,肚子是无底洞,总是害饥呀!墓生也常把老皮的什么指示传达给各村寨时,发现了那些人换掉了大米背着包谷和土豆进了村巷,或是提着并没有卖 完的鸡蛋呀核桃呀柿饼呀,看见了他就往树背后躲。墓生偏就一声咳嗽,他们就露面了,恶狠狠说:墓生,知道你为啥叫墓生吗?!墓生并不生气,知道这些人是要 先把他镇住,使他不能去揭发他们,但墓生已习惯了他们这种伎俩,说:给我一把核桃。他们还真的给了他一把核桃,然后说:别多嘴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书记!墓生 说:你们有啥事?我不知道呀!
现在,墓生想起了那个枯枝竹节虫,也想起了老皮说过过风楼有些人就会伪装的话,就觉得这伙人真是了竹节虫,自己也是竹节虫了。
把登记表送给了野猪寨的村长后,墓生没有歇气又往镇街跑,他必须在黄昏前要把红旗再从婆椤树上收回来,但他的脑子里像钻了蜂,嗡嗡地响,同时想着前 边有座坟了,果然走不到半小时,路边真的有座坟,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回到山头收了红旗,叠好揣在怀里,墓生又在树上寻找竹节虫,但他再没有寻到,脑子又嗡 了一下,低声说:别出事呀。还把怀里的红旗掏出来,红旗并没有什么地方被撕破,也没有鸟把粪拉在上边,可树下到一半时手没抓住,一下子掉下去,把肚皮上划伤了。他爬起来,说了一句:咦,这是咋啦?疑疑惑惑到了上院,而老皮没有在那里熬茶。
老皮每天在工作完毕后都要熬茶的,他是在一个铁罐里熬,熬出的茶汁黑乎乎的能吊线儿,说:不喝解不了乏么!老皮在喝的时候也让墓生喝一口,墓生喝不 了,一口下喉就头晕恶心。可今个天麻麻黑了,老皮没有熬茶,还在开会哩。这阵老皮在发脾气,一定是过风楼又出了什么事,或是过风楼又要开展什么斗争呀。墓 生不敢进去,又担心老皮会突然叫他,也不敢离去,就坐在院外看四面山模糊起来,一群乌鸦呱呱呱地叫着往山下飞。
会终于开完了,参加会的人陆续出来却匆匆往山下去,最后是刘学仁,提了一个瓷罐。刘学仁每次来上院都给老皮提一瓷罐酱辣子或者盐碱的莞青片。墓生想 和刘学仁说话,刘学仁看见他没有理,好像他是风刮过来的树叶,或是一只猫。墓生就朝办公室问:书记,没啥事啦?老皮应声:你回。墓生要往山下走,刘学仁却 开了口:提上!把瓷罐让墓生提着。墓生提了瓷罐跟着刘学仁,还想问问过风楼没出什么事吧,刘学仁竟然说:跟着我吃屁呀?把瓷罐提到溪边了等我!
墓生噔噔噔往山下跑,他跑得生欢,瓷罐先是提着,为了安全,就把瓷罐还抱在怀里,没想到了下院前的那个水渠边,他一跳,跌了一跤,瓷罐就摔破了。墓 生还是在溪边等刘学仁,要把拴瓷罐的绳系儿给他,刘学仁一到,墓生说:刘干事,你脑子里有没有嗡嗡过?刘学仁说:咋啦?墓生说:脑子里一嗡嗡,人是不是就 来灾难啦?刘学仁说:这叫预感灾难。墓生说:我预感灾难啦。拿手扇自己的脸。刘学仁说:多扇几下!瓷罐呢?墓生给了刘学仁的瓷罐绳系儿,说他把瓷罐打碎 了,准备着让刘学仁骂他,也准备着多学几声牛叫。刘学仁看着他,竟然没有骂,也没让他学牛叫,说:张开嘴!墓生以为刘学仁要看他的舌苔,还说:我没你嘴 大。嘴张开了,刘学仁却把一口痰唾进去,说:让你长个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