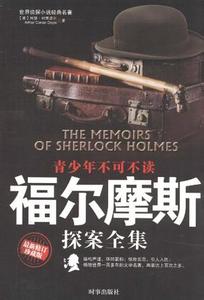第10章
他相当粗一暴地对待我的行为,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我终于拒绝和他同床,不失时机地和他大闹分离。一次他说,他认为我发疯了,如果不改变行为他就要送我去治疗,就是说进疯人院。我说他会看出我根本没疯,他或任何坏蛋都无权坑害我。同时我也承认,想到送我进疯人院我打心眼里恐惧,那样我再不可能说出事实真相了,疯子的话是任何人都不相信的。
我因此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把情况全部公开。可怎么公开,向谁公开,又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我同丈夫再次大吵大闹,以致我几乎当面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不过我保留住了细节,只简单提一下,让他几乎摸不着头脑,最后我才彻彻底底告诉了他。
开始时,他平静地劝我不要坚决回英国去,我为此争辩,激烈的言词一个接一个,像所有家庭争吵时常见的那样。他说我对待他就好像他不是我丈夫,或谈到自己孩子却好像不是他们母亲。简而言之,我不配做一个妻子;他对我已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他采取了一个丈夫或基督徒应有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同我争辩,而我对他却极为恶劣,好像他是只狗而不是个男人,是个最可鄙的生人而不是丈夫;他很不想对我使用暴力,可现在他明白必须如此,为了将来他不得不这样做,以便让我尽到自己的义务。
我的血液沸腾到极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气愤了。我对他说,我对他的合理作法以及不好的命运同样不屑一顾;至于我回英国的事,无论如何我已决定了;说到我对他不像个丈夫,对孩子不像个母亲,其中还有些事情他目前无法理解;不过我认为这样告诉他是恰当的:他既不是我合法的丈夫他们又不是我合法的孩子,因此我采取眼前的态度是有理由的。
说过这话后我承认自己同情起他来了,因他面色苍白如死人,像被雷劈一样站在那儿哑口无言,有一两次我以为他要昏过去。总之他像中风似的,浑身发一抖,脸上流下一两滴汗珠,可他又呆若木鸡,我不得不设法让他保持生气。他恢复过来后,感到恶心作呕,很快被放到床上,次日早晨发了高烧。
不过高烧退去,他又恢复正常,虽然很慢。他略有好转后,便说我用舌头给了他一个致命创伤,在要求我作出解释以前只有一件事问我。我打断他,说对不起我太过分了,看见让他病得那么重;但我要求他不要和我说解释的事,因为那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这使他更加不耐烦,困惑得无法忍受;他开始怀疑有什么秘密没说出来,可丝毫也猜不到。他唯一想到的是我还有一个活着的丈夫,但我向他保证说根本没这回事。不错,说到我的另一个丈夫,他对我而言实际已经死了,他也说过我应该这样看待,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点没担忧的。
不过我发现事情已走得太远,无法隐瞒很久了,丈夫自己给了我一个说出秘密的机会,很使我宽慰。他和我苦苦度过了三四周,但毫无结果,唯有让我告诉他我说那些话是否就为了让他生气,或它们到底有无真实的东西。我仍固执不说,什么也不解释,除非他先同意我回英国,而他说只要他活着是绝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说只要我乐意,是能够让他同意的——而且还要让他求我离开,这就更增添了他的好奇,非常迫切想知道。
最后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让她来叫我说出真情,她确实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我让她彻底打住,说整个这件事的秘密都在她身上,我是出于对她的尊重才隐瞒的。总之我不能再多说了,所以恳求她别再坚持。
听到这话她顿时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说如何想。但她把这种假定当作是我的一个心计而置之不理,为了儿子继续要求我说,如可能还让我与他合好。至于这点,我说的确是她的一番好意,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把她想知道的真情说出来,她也会认为不可能,而不再要求。最后在她的坚持下我似乎被说服,说我敢于把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告诉她——她不久会明白事实如此——只要她庄重保证,没有我的同意决不让儿子知道。
她过了很久才答应,而且是不对儿子说出主要的部分。我又作了许多准备,才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她。首先,我说她告诉我她的故事以及她在伦敦时的名字,是造成我和她儿子不幸破裂的重要原因;我当时感到震惊正由于此事。然后我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和名字,通过另外一些她无法否认的证明,确信地说我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孩子,她在新门监狱生下的女儿。她当时怀着我,才免遭绞刑,后来她流放时把我交到了某某人手中。
她的震惊是无法形容的,她也不愿相信或记得其中的细节,因立即预见到此事将给家庭带来的混乱。可一切与她讲给我的故事那么一致,她如果没告诉我,也许愿意加以否认。是她给自己封上了口,只好抱住我脖子亲一吻,哭得非常厉害,好长时间一言不语。最后她突然说到:“不幸的孩子!你为啥那么糟糕,竟然到这里来啦?并且还是在我儿子的怀里!苦命的女儿呀!”她说。“唉,我们全都毁了!嫁给你自己兄弟!有了3个孩子,两个活着,都是亲骨肉呀!我的儿子和女儿成了夫妻睡在一起!一切都乱套了,让人心烦!苦难的家庭!我们会怎样呢?说啥好呢?做啥好呢?”她就这样念叨了很久,我无力说话,即使有也不知说什么,每个字都会剌伤我心灵的。我们带着这样的惊愕先分开了,不过母亲更吃惊一些,因为这消息对她更加意外。
无疑,没过多久我们就此问题再次交谈。她好像想把亲口对我讲的事忘掉,或者以为我忘记了一些细节,这次讲的作了改动和省略。我想她把许多事忘了,使她恢复记忆,及时把整个经过告诉她,她不可能说到一边去。这时她又喋喋不休起来,惊叹着自己多么不幸。稍过片刻后,我们开始仔细商谈在对我丈夫讲述前,应先采取什么办法。可我们的一切商量有何意义?既看不到怎样度过如此难关,又不明白如何把此事向他公开才安全。不可能作出任何判断,或猜测他听到后有何心情、采取什么行为。假若他很不能控制自己,而向人们公开,我们不难看到一家人都会完蛋的。如果他最终利用法律优势,就会鄙视地把我抛弃,让我去为那点嫁妆提出诉讼。我的钱也许会在诉讼上花光,使自己成为乞丐。几个月后,我或许会看见他在另一个妻子怀里,而我自己却成了世上最可怜的人。
母亲和我一样明白这点,可总的说来我们又不知咋办。一会儿后我们作出了更严肃的决定,但不幸我们母女俩的意见截然不同,的确很不一致。母亲认为我应该把此事彻底掩埋起来,继续做丈夫的妻子,直到另外的事出现,使此事的暴露更方便一些。同时她会努力让我们合好,恢复双方的快乐和家庭的和睦。我们可仍像往常一样同床共枕,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因为,孩子,”她说,“如果这事暴露我们都完了。”
为了鼓励我这样做,她保证让我过得舒适一些,在她去世时把给我丈夫的财产尽量多留些给我。这样,如果事情以后暴露,我也能独立生存下去,并受到他公正的对待。
这个建议与我的看法不合,虽然在母亲是很合理善意的,但我的想法完全相反。
至于把此事埋在我们心底,让它保持现在这个样子,我说是不可能的。我问她怎么会想到我可以容忍和自己兄弟同床的想法。其次,我说她活着才是揭示此事的唯一证据,既然她承认我是她孩子,又看出我有理由那样做,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但如果事情没揭露她就去世,我会被看作是个冒失无礼的家伙,编造了这样一件事来摆脱丈夫,或者我还会被看作是个神经错乱的疯子。然后我告诉她,他已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疯人院,我为此多么担心,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得不像上面那样让她知道真相。
根据我对母亲说的一切,经过我所能做到的最严肃认真的考虑,我作出一个带中间一性一的决定,希望她愿意,即:她应努力说服儿子照我的意愿让我去英国,并提供足够的钱财,要么是物品要么是钞票,以便我能在那儿生活;而我们始终都要指出,他也许什么时候认为合适到英国来找我。
如此,待我走后,她就可冷冷静静地逐渐把事情告诉他,极尽谨慎。他听到后也不会震惊,大发雷霆,或做出过激行为来。她应注意不让他怠慢孩子,或者再娶,除非他听到什么我已死的消息。
这就是我的打算,理由也是对的。经过了那些事情我真的已和他疏远,深恨他作我丈夫,不可能再消除我对他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和他生活还是一种乱一伦,这一切使和他同居成了世上最令人恶心的事。我确实认为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让他对我作那种事还不如拥抱一只狗,所以想到和他同床我就无法忍受。我并非说自己把事情拖了这么久,又不下决心告诉他真相是对的;我只是在讲述当时的情况,而不是怎样做应不应该的问题。
我和母亲这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持续了很久,不可调和。我们为此进行了许多争辨,但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或改变对方的想法。
我坚持说自己很厌恶和哥哥同床,她坚持说不可能让他同意我回英国。我们继续处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意见不同的结果并非是争吵或类似的事,而是无法决定我们该怎样才能解决那可怕的破裂。
最后我决心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对母亲说了我的决定,简单说就是我亲口告诉他。母亲想到这事万分恐慌,我让她放心,说我会逐渐缓和地对他讲的,在心情最好的时候用尽可能好的方法,并且要选择最佳时刻,让他也处于好的心情中。我说自己是有把握的,如果我能够那么虚伪,假装我对他的感情比实际的多,那么我的一切计划也能成功,让双方都同意分手,还可取得较好的一致意见——虽然我不可以把他当作丈夫来一爱一,但足可以当作兄弟来一爱一。
整个这段时间,只要可能,他就极力想从母亲那里知道我那种可怕的说法——如他所称——是什么意思,即我先前提到的我不是他合法的妻子,我的孩子也不是他合法的孩子。母亲搪塞他,说她无法得到我的解释,不过发现什么事很使我烦恼,希望最终会让我说出来。同时她认真劝告他对我更温和一些,以他平常宽厚的态度赢得我的心。她说他威胁要把我送进疯人院等等,让我惊恐万分,劝他无论如何也不要一逼一得一个女人绝望。
他答应对我不再那么凶狠,并恳求母亲向我保证说他仍和以前一样一爱一我,不管生气时说了什么,他都绝无意送我进疯人院。他还要求母亲也像他那样说服我,让我们仍像过去那样生活。
我发现这一谈话立即生效,丈夫的行为马上改变,在我面前又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现在他对我可算是最温和礼貌的,我因此必须作些回报,也尽量做了。可无论怎么也显得笨拙尴尬,因我最怕他抚一摸,担心又怀上他的孩子,以致我随时都会大发脾气。这使我明白绝对必须把事情告诉他,再不能拖延,不过我这样做也极尽谨慎和节制。
他以这种改变的态度对我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我们彼此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如果我能满足于就此过下去的话,相信我们在世上活多久就能这样过多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小遮蓬下面谈话——我们用它作为进入菜园的凉亭——他非常愉快惬意,就目前的融洽和以前关系破裂造成的烦恼,对我说了一大堆好话,说他为我们有希望再不会那样多么欣慰。
我深深叹口气,说我们过去总是融洽的,为此世上再没谁比我更高兴,而我们的破裂也使我最痛苦。可我遗憾地告诉他,在我们的婚姻中有一不幸情况,我把它藏在心底,不知如何对他讲,因此感到很难过,一切快乐都没有了。
他一再要求说出是什么。我说自己不知如何开口,现在他不知道时受苦的仅我一人,但假如他知道了受苦的就是我们两人。所以对他隐瞒是我所能做的最善意的事,正由于这样我才对他保守了一个秘密;而保守这个秘密,我想迟早都会使我毁灭的。
听到这话后他万分惊讶,更坚持让我告诉他,其状态无法形容。他说如果我隐瞒,既不能说对他好心又不能说对他忠诚。我说我也这么认为,却没办法。他又提到我以前对他说过的话,说他希望那秘密与我生气时说的事无关,他已决定把一气之下的举动彻底忘记。我说我也希望彻底忘记,但不行,那影响太深太深,不可能忘记。
然后他说他决心无论如何不再和我闹矛盾,因此也不再坚持让我说出秘密,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他都默认了;他只求我同意,不管怎样都不应破坏我们平静的生活与彼此的善意。
他说这样的话最让我烦火,因我真心希望他坚持让我说出真相,以便被说服讲出来——把它埋在心底真像要我的命一般。于是我坦然回答,他不坚持我也不能说感到高兴,尽管我不知怎样说。“可是瞧,亲一爱一的,”我说,“我把事情告诉你,你有啥条件?”
“世上任何条件都行,”他说,“只要你的要求合理。”“好吧,”我说,“唔,你得亲自签字,说明如果你发现不是我的错,或者我并不愿意造成以后的不幸,那么你将不会责怪我,对我更加不好,伤害我,或让我为并非我的过错受苦。”
“这,”他说,“可是最合理的要求,不为并非你的过错责怪你。把笔墨给我。”他说。我跑进去拿来笔墨和纸,他完全照我说的写下了条件,签上名字。“唔,”他说,“还有什么,亲一爱一的?”“哦,”我说,“还有就是,你不能因为我没在知道此秘密前把它告诉你,而责怪我。”“也很合理呀,”他说,“完全照办。”他把这也写下并签了字。
“瞧,亲一爱一的,,”我说,“现在我只剩下一个条件了,就是说,由于此事只涉及到我们两人,除你母亲外对任何人你都不要提起;并且由于我和你一样与此事相关,一样无辜,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应一气之下作出什么蠢事,暗地里伤害我或你母亲。”
他有点吃惊,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但在签字前看了又看,几次犹豫不决,重复道:“伤害我母亲!伤害你!究竟是啥秘密呢?”不过他最后还是签了字。
“好啦,”我说,“亲一爱一的,你已亲自签字,我无话可说了。但你将要听到的,是任何家庭遇到过的最意外、最震惊的事,我因此请求你答应听的时候要沉着镇静,像个有理一性一的男人。”
“我会尽力的,”他说,“只要你不再让我挂虑。你这一切准备真把我吓住啦。”
“哦,那么听着,”我说,“情况是这样。我先前生气时对你说过我不是你合法的妻子,我们的孩子也不是合法的孩子。现在我得平静、善意但非常痛苦地告诉你,我是你的亲妹妹,你是我的亲一哥哥,我们都是家中这个母亲的孩子。她对这件事深信不疑,谁也无可否认或反驳。”
我看见他脸色发白,惊慌失措,说,“记住你保证的事,镇静一些。为了让你有心理准备,事前我算是最费口舌的了。”我仍让一个仆人给他拿来一小杯朗姆酒(当地常饮的酒),他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