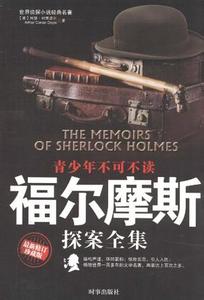第12章
他利用许多机会表达他的心情,说我对他多么体贴,待他康复后又为此送了我一个价值50几尼的礼物,如他所说,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的命。
这时他深切地向我表明,他对我怀着真诚神圣的感情,而且最完整地维护着双方的节一操一。我说我对此非常满意。他甚至对我断言,如果他和我赤身一裸一体躺在床上,也会神圣地维护我的贞一操一,正如我假若被人强一奸一他会保护我一样。我相信他,并告诉了他。可他还不满足,说有机会时他想给我一个无可怀疑的证明。
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我才有机会去布里斯托尔办自己的事。他为我雇了一辆马车想陪我一起去,此时我们的关系真的越来越亲密了。他从布里斯托尔把我送到格洛斯特,那纯粹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使我们呼吸到不少新鲜空气。来到旅店已没有房间,只有一间大卧室,里面有两张床,算是我们的幸运吧。店主领着我们看屋子,来到那个大房间很坦然地对他说,“我无权过问这女士是不是你太太,如果不是的话,你们也可以很正经地睡在这两张床上,就好像你们是睡在两个房间里。”说罢他拉起一副大帘,把屋子一分为二,实际上把床也隔开了。“瞧,”我朋友立即说,“这两张床行了;至于别的,我们是近亲,不能睡在一张床上,不过在旁边睡着是可以的。”这也使此事看起来很正派。睡觉时,他礼貌地走出屋子让我上了床,然后他才上了另一张床,躺着又和我谈了很久。
最后他又提起了经常说的话,即他可以赤身一裸一体和我睡在一起而不给我丝毫伤害,并离开自己床。“现在,亲一爱一的,”他说,“你会看到我对你多么正直,我能做到守信的,”然后他朝我的床走来。
我略为反对一下,但必须承认即使他根本没作过那些保证,我也不会有很大反对的。因此我稍作抵抗后便静静躺着了,让他到我的床上来。他上来后把我抱在怀里,我就这样和他睡了一夜,他也没做别的或提出什么,如我所说只把我抱着,整夜都这样,次日早晨起去穿好衣服,使我在他面前就像刚出生时一样清白。
这可是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或许懂得自然规律的人都会如此,因为他是一个身强力壮、充满朝气的男人。他这样做也并非出于宗教上的道义原则,而纯粹出于对我的感情,坚持说虽然我是他在这个世上最可一爱一的女人,但正因为他一爱一我,所以决不能伤害我。
我承认这是一种高尚的节一操一,可我以前从未见过,所以惊奇不已。我们像先前一样完成了余下的旅程,回到巴思,这儿他一有机会就来看我,同样经常对我温一存无比。我常和他一起睡觉,尽管我们都懂得夫妻所有那些亲一昵行为,但他从没对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且对此也很看重。我并非说我像他想的那么高兴,得承认我比他坏得多。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近两年,唯一不同的是他去了3次伦敦,有一次在那儿待了4个月。但说句公道话,他从没停止拿钱给我,总让我过得相当不错。
假若一直这样下去,我承认我们大可以自夸,不过正如明智的人所说:在自制的边缘冒险实属不佳。我们发现真是如此;这儿我又得对他说句公道话,我承认并非由他先突破防线的。那是在一个夜晚,我们俩躺在床上,暖和快乐。我想,我们比平常多喝了点酒,尽管这点酒根本不会使我们醉。我们作了一些我说不出来的傻事,我被他紧紧抱在怀里,对他说(我现在带着耻辱和恐惧重提这事),我觉得可以一个晚上解除他的约定,就一个晚上。
他立即照我的话办,之后我再无反抗,我确实也不想再反抗他了。
我们防守的贞一操一就此打破,我从一个朋友变成了刺耳难听的娼妇。早晨双方都后悔,我伤心地哭着,他表示很遗憾,可我们当时也只能这样。现在道路清除,节一操一和良心上的障碍被搬走,我们要抵抗的事也就减少了。
在这周余下的几天里我们的谈话有些单调,我看着他时脸发红,不时提出令人忧郁的问题:“我怀上孩子咋办?那时我会怎样呢?”他鼓励我,说只要我对他忠诚他也会对我忠诚的;既然事情已到这个地步(的确并非他有意),如果我怀上孩子,他会照顾好我们母女俩。这使我们两个坚定起来。我确信地告诉他假如我有了孩子,找不到接生婆我宁愿死也不会提到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保证,我真有了一定会找到接生婆的。双方的保证使我们更加坚定,后来我们一喜欢就重犯那种罪恶行为,终于像我担心的那样我真怀上孩子了。
我确信无疑后清楚地告诉了他,我们开始想办法解决,我建议把此秘密告诉房东听听她的意见,他也同意。我发现女房东对此习以为常,满不在乎,说她就知道终有这一天的,让我们心情大为好受。如上所说,我们发现她是这种事的老手,把一切承担起来,忙着找接生婆和保姆,使所有问题得到处理,极好地解救了我们,干得的确相当不错。
临产时她让我先生离开去伦敦,或假装那样。他走后她便告诉教区官员,说有一个女士要在她家中分娩,她很了解这个女士的丈夫,并假装说他名叫“沃尔特·克利夫先生”,说他是个有钱的绅士,会负责所有的问题,等等。教区官员们立刻放心了,我分娩时享受到真正做“克利夫太太”的那种荣誉,得到三四个巴思最优秀公民的太太的帮助,不过对他来说费用贵了点。我常因此对他表示关切,可他让我不用担心。
他给了我足够的钱,支付用于分娩的额外开支,因此一切事情都很不错,但我也没装着非常放肆或奢侈的样子。此外,我和过去一样明白世事,知道这种情况常不会长久,所以我尽量把一些钱存在一旁,以便“未雨绸缪”,如我所说。我让他相信,所有的钱都用在表面上我分娩的额外开支里了。
这样,加上他先前给我的钱,以及我自己的钱留下的,我分娩后一共有两百几尼。
我确实生了一个好小子,十分可一爱一。他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极其亲切热情的信,说他认为我一旦恢复就最好去伦敦,他在汉默史密斯为我订了房间,好像我只是从伦敦去的,过一段时间后我再回巴思,他愿意同我一起返回。
我很喜欢他的建议,专门雇了一辆马车,带上孩子和一个一奶一妈一喂一奶一照料他,还带了一个女仆。我就这样出发去伦敦了。
他坐自己的四轮轻便马车在雷丁接到我,让我上了他的车,仆人和孩子留在雇来的四轮大马车上。他把我带到汉默史密斯的新住处,我有充分理由对它相当满意,房间太好了。
现在我的生活的确可称为兴旺无比了,唯一欠缺的是做个妻子,而目前又不可能,所以我千方百计尽量存钱,如上所说,以防穷困的日子到来,很清楚这种事不会永久下去。养情妇的男人经常更换她们,对她们不是生厌就是嫉妒,或别的什么。有时像我这样受到良好待遇的女士们行为又不慎重,不注意维护男人对自己的珍重或自己作出的海誓山盟,被轻蔑地抛弃也是理所应当。
可在这一点上我是安全的,无意喜新厌旧,因此也没交友的习惯,没另寻它欢的诱一惑。我唯一的交往就是家中的人和隔壁一位牧师的太太,这样他出去时我谁也不去走访,他回来时总看见我在屋里。即使出去呼吸空气也一定和他在一起。
我们彼此的这种生活方式无疑是最最偶然的。他常对我说,他和我初次相识的时候,甚至就在我们第一次打破约定的夜晚,他都根本没想到和我同床;他对我总是怀着真诚的感情,一点没打算那样做。我确信地对他说我从不怀疑,如果怀疑的话,我就不会那么轻易放肆,以致产生那样的结果。一切真让人吃惊,都怪我们那晚失去自制,随一心一所一欲。从此以后我的确常说——算是对本故事读者提出的一个告诫吧——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别太随一心一所一欲,过于放肆,以免在最需要意志的关键时刻,意志无法维护我们的节一操一。
说实话,从我和他谈话的第一小时起,我便决定只要他提出就和他睡觉,但那是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又不知道得到他的其它办法。可那晚我们睡在一起,如上所说,并发展到如此地步,我才发现自己的软弱。那种欲一望无法抵抗,可是他还没提出要求我就先彻底屈服了。
然而他对我非常公正,从没因此责备我,任何时候都丝毫没表示过对我那种行为的反感,而总是说他很高兴有我作伴,就像我们刚在一起一样。
的确他没有妻子,就是说妻子对他已名存实亡,但良心的责备常把一个男人,特别是一个有理一性一的男人,从他情妇怀中夺走——他最终即这样,虽由于另外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我对自己的生活良心上也感到自责,甚至在我最为满足时也这样,但贫穷和饥饿可怕地摆在我面前,像一个恐怖的幽灵压迫着我,使我无暇往回看。都是因为贫穷我才陷入如此境地,因而害怕贫穷又使我继续留在里面;我常下决心,假如能够就彻底与此脱离,存上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可这些想法无足轻重,他一来就消失了。有他陪伴真是愉快,一点忧郁也没有,我那一切忧思都是独自一人时才产生的。
我在这种既幸运又不幸运的处境中生活了6年,给他生了3个孩子,仅第一个才活下来。这段时间我搬迁了两次,但到第6个年头又回到最初在汉默史密斯的住处。在这儿,一天上午我吃惊地收到我先生一封亲切但忧郁的信,说他病得很厉害,担心疾病再次发作。可他妻子一方的亲戚也在家里,让我和他在一起是不可行的;他对此极不高兴,希望能让我像以前一样照顾护理他。
我对这个消息十分担忧,急于想知道他怎样了。我大约等待了两周,什么情况也没听到,觉得意外,真的非常不安起来。我想,可以说在随后的两周里我几乎发狂。我特别困难的是不能直接知道他在哪里,最初只知他在岳母的住处。我迁到伦敦后,根据我给他写的信,不久才弄明如何打听他的情况。我得知他在布卢斯贝里的一座房子里,全家人都搬到了那儿,他妻子和岳母也在其中,虽然没让妻子知道她和丈夫住在一处。
我不久还得知他已临近死亡,说句实话,我也几乎因此临近死亡。我很想知道情况,一天晚上我把自己装扮成女佣,戴着圆罩和草帽来到他的屋前,好像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一个女士派来的,替男一女主人跑差事。我说我被派来了解某某先生的情况,那晚休息怎样。这样我才有了希望得到的机会,和一个女佣闲谈了很久,了解到他详细的病情,得知是胸膜炎,伴有咳嗽和高烧。她还告诉我谁在屋里,他妻子怎样,从她的话中,可知他们有希望使他妻子的一精一神恢复正常。至于先生自己,医生们说已几无希望,到早上他们以为他快死了,几乎不见好转,他们料想他熬不过下一夜的。
这消息令我忧郁不堪,开始明白兴旺的日子已到尽头,明白幸亏我做了一个好主妇,在他活着时存了些钱,因为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前景一片茫然。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有一个儿子,他是个漂亮可一爱一的男孩,近5岁了,却没吃没穿,至少我不知如何供养他。想到这些,那晚我郁郁不乐地回到家里,开始思索余生怎样度过,如何为自己找到归宿。
你可以肯定,不尽快再次了解他的病情我是无法安身的。这次我不再自己去冒险,而是派了几个假冒的通信员,这样又过两周后我发现他有了生还的希望,尽管病情仍很严重。于是我减少派人去探听情况的次数,一段时间后从邻里得知他可以活动了,随后又可以出门了。
当时我毫无疑问不久会得到他消息,开始安慰自己,以为我的情况会好转。我等了一周,两周,又大为吃惊地等了近两月,唯一听到的是他身一体恢复后到乡下呼吸新鲜空气去了。这以后又过了两月,我知道他重回到城里的住处,可他仍没给我任何消息。
我给他写了几封信,同样寄到先前的地方,却只有两三封才取走。我接着又写,显得更加紧迫,在一封信中告诉他我不得不焦急地等候他的消息,并讲述了我生活的拮据,需要付的房租,孩子吃穿困难,我的处境很不好,缺乏必须的供养,而他以前非常认真地保证过要照顾养活我的。我把信抄了一封,发现它在寄信处放了近一月也没被取走,于是设法把抄的那封信送到一家咖啡店交到他手上,我发现他常去那里。
他因此不得不作出回答,我由此明白将被他抛弃,也得知他一段时间前给我写过一封信,要求我再回到巴思去。信的内容我很快会说到。
的确,,人在生病卧床时,对这样的关系是以与原来不同的面目和眼光来看待的。我的情人已到过死神之门,临近来世的边缘,似乎对自己过去那种殷勤轻浮的生活产生应有的后悔和忧虑。别的不说,他和我的这种罪恶勾当,也仅仅是一种长久的通一奸一而已,现在显示出其本来面目,而非他原来以为的那样。此刻他带着一种正当的反感来看待这事。
我还不得不指出——以便在这种轻浮放一荡的事件中,听取女同胞们的意见——只要这种罪过之后产生了真诚的忏悔,那么有罪之人必然遭到憎恨;以前的感情显得越深,憎恨越大。结果总是如此,确实没有别的,因为不可能一方面对这罪过产生真心实意的厌恶,另一方面造成这种罪过的一爱一意又继续存在。由于对罪过的憎恨,同案犯因此被痛恨,你不可能指望别的。
我就发现是这样,虽然这个先生礼貌公正,没走向任何极端,但他在此事上不长的经历即如此。他从我最后一封信和其它信(他后来取走)中,得知我没去巴思,也没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所以他这样给我写道:
夫人:
我很意外你没收到我上月8日的信,我保证信送到了你的住处并交到女佣手上。
我不用告诉你过去一段时间来我的情况如何,我到过坟墓的边缘之后,又是如何意外受到上苍不应有的怜悯,得以恢复。在我陷入过的那种境地中,我们不幸的交往没给我的良心留下丝毫负担,这并不会使你奇怪。我不需再多说了,必须悔过的事情也必须改变。
我希望你考虑回巴思去的事。在此附上50英镑钞票,以结清你的房租并送你回
那里。我再补充一下,仅仅为了这个原因,为了不让你伤害我,我不能再见你了,希望你不要吃惊。我会给孩子应有的照顾,留下他或带在你身边都行。希望你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对你是有利的。
这封信仿佛使我遍体鳞伤,我无法形容良心的指责,因为我并非看不到自己的罪过。我又想到同哥哥继续生活下去也许伤害更少些,因在那点上双方都不知道情况,婚姻毫无罪过可言。
可这期间我从没想到自己是个已婚女人,某先生的妻子,他是个亚麻布商,虽然因情况所迫离开了我,但他无权解除我们的婚约,给我合法的再婚自一由。所以整个这段时间我不过是一名娼妇和通一奸一犯。然后我进行自责,怪自己太放肆,把先生也陷害了,而我的确是此罪的主犯。现在他产生一种自信,被怜悯地拉出深渊,而我却被留在里面,仿佛被上苍抛弃,任我继续去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