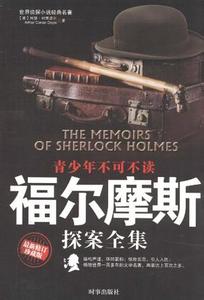第20章
那包裹是做什么用的或者为什么放在我看见的那个地方,我不得而知,可我打开它时发现里面有一套分娩用的衣物,相当不错,几乎是新的,饰带很一精一美。有一只容量为一品脱的银制小汤碗,一只小银杯和6只调羹,另外有些其它衣物,一件完好的儿童罩衣,3张丝织手帕,那只杯里和一张纸里有18先令6便士钱。
我打开这些东西时始终感到极其恐惧和害怕,尽管我一点危险也没有,那种心情无法形容。我坐下来大声哭叫道:“上帝啊,我现在成了什么啦?一个贼!唉,下次我就会被抓住,送到新门监狱去,被判处死刑!”之后我又哭了很久,我敢肯定,虽然自己很穷,但如果我由于害怕有了那个胆量,我当然是会把东西再送回去的,但这种想法一会儿后便消失了。噢,那晚我上一床睡觉,几乎没怎么睡着,心里老想着这件可怕的事,整夜以及次日整天都不知我说了啥或做了啥。然后我急于想听说关于丢失那些东西的什么消息,想了解情况如何,不管东西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也许,”我说,“会是某个像我一样的穷寡妇,她把这些东西包好准备拿去卖掉,为自己和一个穷孩子买回一点面包,而现在由于得不到本来可以买回的一点食物正挨着饿,他们心都碎了。”在随后的三四天里这一想法比任何事情都让我感到难过。
但是我自己的不幸把这一切想法压制下去,眼见我自己将会挨饿——这种情景每天越来越可怕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的心也渐渐麻木起来。我心情尤其沉重的是自己本来已经改过自新,如我所希望的已经为所有过去的邪恶行为忏悔,并且还过了几年端庄持重的隐居生活,,可现在因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我的身心竟被迫又来到毁灭之门。有两三次我跪在地上,极力祈求上帝解救我,而我只能说自己的祈求毫无希望。我不知所措,身外的一切无不可怕,身内的一切无不一陰一暗。我回想着自己过去的生活,好象并没有忏悔过;上天现在开始惩罚我,要让我变得像以前那么邪恶可耻。
假如我就此打住,也许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忏悔者,但我身内有一个邪恶的顾问,他不断怂恿我以最恶劣的手段解救自己。所以一天晚上他又以同样可恶的刺激引一诱我,说“把包裹拿走”,让我又出去看会找到什么。
我现在白天出去,不知要游荡到哪里,也不知要寻找什么,这时魔鬼在我的路上设下了一个实在可怕的陷阱,这样的陷阱我以前或以后都未遇到过。我穿过阿德斯门街时,见一个幼儿刚从一所舞蹈学校出来,正独自回家。怂恿我的家伙像个真正的魔鬼,让我去进攻这个无辜的孩子。我和小孩说话,她也和我咿咿呀呀地说着,我便牵住她的手领着她来到一条通往巴塞洛缪院的铺有石头的小巷,并把她领进那儿。孩子说那不是她回家的路,我说:“是的,好孩子,是这条路,我会把你带回家去。”孩子戴了一条有金珠子的小项链,我眼睛盯住它,来到小巷的暗处我弯下一身一子,假装把孩子松了的木底鞋系紧,同时取走她的项链,而她并没有感觉到;然后我又领着她继续往前走。瞧,魔鬼这时让我在一陰一暗的巷里把孩子杀了,以免她哭叫,但我一想到这就害怕,不愿那样做。于是我让孩子转过身又回去,说那不是她回家的路。孩子说她会回去的,这时我走进巴塞洛缪院,再转入另一条通往长巷的路,来到查特豪斯院并进入圣约翰街,接着穿过去来到史密斯菲尔德,沿切克巷进入菲尔德巷到了霍波恩桥,并混在通常经过那儿的人群中,这时便不可能被发现了。这样我在世上又迈出了第二步越轨的行为。
想到这个战利品我最初的一切想法都不存在了,我有过的那些念头也很快消失;贫穷使得我的心肠硬起来,自身的窘迫让我对其它任何事情都不顾了。上一件事并没让我有多大的担心,因为我根本没有伤害那个可怜的孩子,我只是认为孩子的父母粗心大意,让那可怜的羔羊独自回家,而我好好地谴责了他们一下,这将会教他们下次更加小心一些。
那一串珠子大约值12或14英镑。我想它先前可能是那个母亲的,因孩子戴着太大了,但也许虚荣的母亲要让孩子在舞蹈学校显得很高贵,就把它给孩子戴上。无疑她还让一个女佣去照顾孩子的,可女佣像一个不负责任的轻佻女子,也许与某个碰见的小子勾搭上了,让可怜的小孩到处乱走,最后落到我的手中。
然而我并没有给孩子造成任何伤害,甚至没有吓住她,因为我自己的心肠还不是很硬,可以说只是做了因贫穷不得不做的事情。
这以后我又多次冒险,但是我在此种行为上还是个新手,只知道按照魔鬼的指令去做,而他的确也很少不积极胆大的。有一次冒险太幸运了。当时我正在黄昏中穿过“三王廷”尽头旁的罗姆巴德街,忽然有个人像闪电一般从我身边跑过,并把手中的一个包裹正好抛在我后面,而我站着靠在小巷转弯处的一座房子的角落那儿。他把包裹丢下后便说道,“上帝保佑你,夫人,让它在那儿放一下吧,”然后跑走了。在他后面又跑上来两个人,这时有个没戴帽的小伙子立即大喊道:“站住,小偷!”眼看人们就要追上后面那两个家伙,盗贼只得丢下已偷到的东西,并且其中一个还被捉住,只是另一个跑掉了。
我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到人们把捉住的可怜家伙和追到的东西拖回来。他们很满意既弄回了赃物又捉住了小偷,就这样从我身边经过,因我似乎只是一个站在那里等人群离开的人。
有一两次我问是怎么回事,可没人回答我,我也不紧缠着他们问。等人群都走过以后我才赶紧转过身,拿起身后的东西走开了。我做这件事确实没有先前那样感到忧虑不安,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偷的,而是它们被偷后落到我手里的。我带着东西回到住处,里面有一块黑色的上等光亮绸和一块丝绒,后者只是一块约11码的丝绒的一部分,前者是一整块近50码的绸子。被抢劫的看来是一家绸布店。我说被抢劫是因为人们丢失的物品相当多,我想丝绸大约达六七块吧。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弄到这么多东西的,但由于我只是掠夺了盗贼,所以我一点顾虑也没有就拿走了它们,并为此非常高兴。
我至今运气很好,又作了几次冒险,虽然获得的赃物不多但却很成功。可是我每天都担惊受怕,唯恐什么灾祸会降临到我头上,最终使我必然被绞死。我的这种感觉太强烈了,不可忽视,它阻止我去采取行动,尽管这些行动也许会非常安全;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做,好多天来它都诱一惑着我。我经常走到城镇周围的一些村子里去,想看看路上是否会遇到什么。走过斯特普尼附近的一座房子时,我看见窗台上有两只戒子,一只是钻石小戒另一只是普通的金戒,肯定是某个粗心的女士放在那里的;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许在自己洗手的时候才会明白。
我几次从窗子旁走过去,看是否能发现屋里有没有人,我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可仍然不能确信。我马上又想到敲一下窗玻璃,好象想和某人说话的样子,如果里面有人他们必定会来到窗边,那时我就告诉他们把戒子拿开,因为我发现有两个可疑的家伙注意到它们。这是一个机灵的想法。我敲了一两下窗,没人过来,我便猛推一下方形的玻璃,轻轻把它打破,取出两枚戒子后赶紧离开了。钻戒大约价值3英镑,另一枚大约9先令。
我现在不知如何卖掉手头的物品,尤其是那两块丝绸。我很不情愿为了一点钱就把它们处理掉,像可怜不幸的盗贼通常那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也许偷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却不得不很便宜地把它卖掉。但我决心不这样做,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然而我也不很清楚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去找那个老女管家,再次把我的情况告诉给她。我尽最大努力每年为我的小儿子准时付给了她5英镑,可是最后只得终止了。不过我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她我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丈夫去世了,我无法再继续支付下去,恳求不要让可怜的孩子由于母亲不幸遭受太多的苦。
于是我去拜访了她,发现她仍然干着老行当,只是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某个绅士曾经因为自己女儿被悄悄弄走而控告她,因她好象参与进去。她差点被绞死,而为此花费的钱也几乎把她给毁了,所以她房子的家具很简陋,并且干那一行的声誉也不如从前。可是她仍然如人们所说站立起来,又由于她是一个闲不住的女人,手头还留有一些公债,她便转而成了当铺老板,过得很不错。
她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带着通常的那种乐于助人的态度对我说,她不会因为我的处境更差而对我不那么尊重。她说尽管我不能为孩子支付钱,但她仍让他受到很好的照顾,那个带他的女人也很安心,所以我在能够更好地为孩子尽点力之前用不着担忧。
我对她说我没有多少钱了,不过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如果她能告诉我如何把它们变成钱的话。她问是些什么。我取出那串金珠,说是丈夫送我的一件礼物;然后我把两包丝绸给她看,说是从一爱一尔兰带回来的,我随身带到了城里。我又给她看了那枚小钻戒。至于那一小包盘子和调羹,我自己先前已设法处理。至于我分娩用的衣物,她提出自己买下来,相信那曾是我的东西。她说自己做了当铺老板,可以把它们作为我交给她的典当物替一我卖掉,并很快找来适当的代理人;由于东西在她手头,他们毫无顾虑地买走了,还出了个好价钱。
我现在开始想到这个必要的女人在我处境不佳的时候也许能帮点忙,让我做个什么事情,因假如能够得到任何体面正当的工作我都是乐意去做的,但她又无法弄到体面正当的工作。如果我再年轻些或许她能帮助我,不过我打消了那种生活的念头,过了50岁的人早都不适合了,而我正是到了这样的年龄,并告诉了她。
她最后让我到她家里去住,直至我找到什么事做为止,这也花不了我多少钱,我便欣然接受。现在我一日子轻松了一点,开始考虑如何让人把我和最后那个丈夫生的小儿子带走,她也轻易办好了此事,只安排让我每年付5英镑——如果我能够付的话。这对我是个极大的帮助,所以我好一阵子都没有去干最近开始的那种邪恶勾当;我很愿意找到工作做,但如果没有任何熟人你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我终于找到了一些缝纫活,为女士的床垫和裙子之类的东西做些缝纫。我很喜欢这工作,干得相当努力,我就这样开始了生活。可是煞费苦心的魔鬼决心让我继续听他的使唤,不断驱使我出去走走,就是说看是否能像过去那样遇到什么情况。
一天晚上我盲目地听从他的召唤,在街上绕了很大一圈,但什么收获也没有。我不就此满足,第二天晚上又出去,在经过一家啤酒店时我看见里面紧一靠街边的一个小间的门开着,桌上放着一只银制大酒杯,这种东西在当时的酒店里用得很多。好象有些人刚才在那儿喝过酒,粗心的服务生忘记把它拿开。
我坦然地走进那个小间,把银制酒杯放到凳子的角处,在它面前坐下来,用脚碰碰地面。一个服务生立即走过来,我要了一品脱热啤酒,因天气冷。他快步走了,我听见他走下酒窖去取啤酒的声音。这时又来了一个服务生,大声问:“要啤酒吗?”我显得忧郁地说:“是的,那个服务生已为我取一品脱啤酒去了。”
我坐在那儿时听见酒店里的女老板说:“5号间的人都走了吗?”她说的是我坐进去的那间,只听服务生回答:“嗯。”“谁把酒杯拿开了?”女人问。“是我,”另一个服务生说,“在那儿。”他好象指另一个酒杯,那是他从另一小间里误拿过去的,或者要么一定就是这家伙忘了他并没有拿进去——他当然没有的。
我听到这一切时满意极了,因为清楚地看到他们并没有发现酒杯不在,而是断定它已被拿走。于是我喝完酒,要求买单,出去时说:“小心你的餐具,孩子。”我指的是他端来让我喝酒用的一品脱量的银杯。服务生说:“是的,夫人,非常感谢。”然后我走了。
我回到女管家的家,想着该试探一下她了,以便假如我不得已被暴露出来,她或许可以给我些帮助。在家里呆了一会儿后我才有了和她谈话的机会,就对她说我在这世上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秘密要告诉她,只要她很尊重我,不对外人讲。她说她已经忠诚地为我保守了一个秘密,为什么我要怀疑她再保守一个呢?我便告诉她自己遇到一个世上最奇怪的事,而我自己一点那样的意图也没有。我把酒杯的事原原本本对她讲了。“你把它带走了吗,亲一爱一的?”她问。“当然带走了。”我说,把杯子拿给她看。“可是我现在该咋办?”我问。“必须把它送回去吗?”
“送回去!”她说。“哈,如果你想去新门监狱的话。”“唉,”我说,“他们不会可鄙得不让我再把东西送回去吧?”“你不了解那些人,孩子。”她说。“他们不仅会把你送到新门监狱而且会把你绞死,根本不考虑你还回去是如何诚实。他们也许还会把损失的所有酒杯的账单拿来让你付清。”“那我该怎么办呢?”我问。“瞧,”她说,“既然你已那么巧妙地把它偷走,你就得把它留下,现在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另外,孩子,”她说,“你不是比他们更需要酒杯吗?我倒希望你每周都捡到一次这样的便宜。”
这使我对女管家有了新的看法,自从她变成当铺老板后,她周围便有了一种人,他们一个也不像我过去在那儿遇见的人那样诚实。
我到那儿不久便更清楚地发现这点,因不时看到人们带来一些剑一柄一、调羹、叉子、酒杯和所有这类物品,它们不是被典当而是完全卖掉。她什么也不问就全部买下,并且我从她的谈话中知道都买得很便宜。
我还发现她在干这一行时总是把买来的餐具熔化掉,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一天上午她来对我说她要熔化东西了,如果我愿意她就把我的酒杯也放进去,这样任何人都不会看见。我说非常愿意,于是她就称了杯子,并且按最高的银价付给我钱,而我发现她对别的顾客并不是这样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干活时感到极为忧愁,她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自己心情很沉重,手中的活不多,难以维持生活,不知如何是好。她笑起来,说我必须再出去试试运气,也许又会碰上一件餐具。“啊,母亲!”我说。“我对那个不是很懂行,如果被抓住就彻底完了。”她说,“我可以帮助你找一个女师傅,她会把你教得像她一样机敏灵巧。”这个建议使我不寒而栗,因为我至今在那些人中既没任何同伙又没一个熟人。但是我的一切端庄与畏惧都被她征服,很快我就在这个同伙的帮助下变成一个像“娼一妓一扒手”一样厚颜无耻、机敏老练的贼——不过如果她名不虚传的话,我是干得不及她一半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