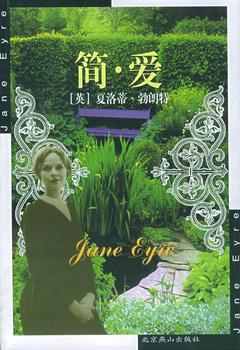斯塔福的科学智慧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论他的研究和学术抱负时表现出来的热情让她感动,他在一性一方面的天真又使她心动。
他们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了。自从那次早餐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那天早晨,在一次特别缠一绵、持续很长时间的亲一热之后,勒夫金若无其事地说:“塞莉,亲一爱一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至少不要这样见面了。”他做了一个包一皮括一切的手势。“两个成年人之间开始时很快活的事情,现在变得复杂了。”
“复杂了?”她感到愕然。“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自己就快要一爱一上你了。”
“那有什么复杂的?”
“我年纪比你大30岁。”
“确切些说,是35岁。”
“你说得对,塞莉,大35岁。简要地说:等你到35岁成熟的时候,我已经是步履蹒跚的70岁老头了。”
“别发傻了,格雷厄姆。”她以前从来不曾称呼他格雷厄姆。“等到我70岁,变成颤颤巍巍的老人时,你就是个好色的105岁的老头。”
勒夫金倾身向前,隔着桌子亲一吻她的前额。“你是一颗宝石。你可能会认为我疯了……你甚至会感到愤怒……但是最终,你会明白这样是比较明智的。”
现在她打电话找他。“格雷厄姆,”她说,“我是塞莱斯蒂纳。我想见你。”
“塞莉,你好吗?”勒夫金的声音异乎寻常地低沉。
“工作很努力。”
“我也很想见你,可是——”
塞莱斯蒂纳打断了他。“教授,我想约个时间到办公室里去见你。”
塞莱斯蒂纳刚坐下来,就马上说明她这次来的目的。她提醒他说,去年她听从了他的劝告,成了琼-阿德利教授的研究生。现在她已经学完了第一年的课程。她的研究项目是分离和描绘一种新发现的蟑螂激素——咽侧体抑制素,项目进行得很顺利。勒夫金开始用中指敲击桌子。这些他全都知道。她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看见他变得不耐烦起来,塞莱斯蒂纳突然宣布了一条使勒夫金感到吃惊的消息:一条勒夫金不知道的学院传言。据说,琼-阿德利在中西部一所大学里找到了一个终身副教授的新职位。塞莱斯蒂纳想请教他:在第4年上,如果她放弃为期6年的理科学士-博士连读课程,去追随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琼要走,我想这不能怪她,”勒夫金若有所思地说。“在霍普金斯当了3年助理教授就在其他地方获得终身任教是一次不坏的跳槽。如果你和她一起去,就意味着你得从霍普金斯的快车道上撤退下来,进入标准的研究生课程。这样你可能要损失两年时间。你有这种准备吗?”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你是唯一知道我为什么会跟琼的人。你给了我很好的忠告。可再加两年呢?”
她来请教勒夫金关于她专业生涯的事,确实很有眼光。他不是化学系的成员,在可能会失去一位非常有前途的研究生这件事情里,他没有既得利益。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在几个月之前结束了。“你在研究一项非常有希望的课题。”他说,“要是阿德利远在几百英里之外,你会发现很难在这里继续你的研究。假如她走了,我打赌他们不会再保留养虫室。那你怎么办?让她每隔几天给你运送新鲜的蟑螂?你甚至完全可能得放弃这项研究,去跟随一位新的论文导师,开始另外一个项目。那样肯定会花费你一两年的时间。塞莉,如果你与琼的研究成功了,如果你能够确定那种激素的结构,如果……”
“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塞莱斯蒂纳的急躁尽现无遗。
“我认为假如这样一个大课题能够成功的话,两年时间算不了什么,特别是,如果你能够与一位还不太有名的教授一起发表研究论文的话。”
塞莱斯蒂纳要听的就是这句话。学年一结束,她就收拾好行李,跟着琼转到她的新大学去了。
塞莱斯蒂纳假装睡着了。实际上,她一直在思考她对两所大学的选择如何影响了她与男朋友的认真交往。格伦-拉森算不上。她跟他纯粹是逢场作戏:当初在布兰纳,她决定要改变她的处一女身份,如此而已。她把那一段经历当作一次实验而不是一浪一漫的插曲。勒夫金不一样:他更像一位导师。现在与斯塔福交往,塞莱斯蒂纳忍不住把他们两个加以比较。这倒不是因为她不享受杰里的手抚一摸她的一臀一部,它的皮肤就像蛋壳一样光滑。只是他还没有学会像格雷厄姆-勒夫金那样灵巧而熟练的触一摸。不过,勒夫金是一位生物学终身教授,有多年的经验,而斯塔福只是一个博士,刚摆脱浸礼教的压抑束缚。她相信斯塔福会进步的。这只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二个夜晚。今天早晨他真的很抓紧时间。她唯一不肯定的是自己能否克服他做一爱一时一声不吭的习惯。他从小在南方浸礼教的影响下长大,那种影响根深蒂固,哪怕在一性一交前长时间互相一爱一抚的过程中,他都只使用浸礼教徒的用词来描述男一女生一殖器官,或者一性一交本身。那个词就是“它”。另一方面,塞莱斯蒂纳在格雷厄姆-勒夫金的指导影响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情人。她明确而又急切地告诉斯塔福,说明她要他下一步做什么。她挑一动情一欲地详细告诉他自己想要与他干什么。她充满激一情地叫唤,最后还嘲笑他沉默不语,对她的问题“快活吗?”只知道点头。
“天哪,你知道几点了?”塞莱斯蒂纳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拉开斯塔福身上的毯子。“已经8点40分了。在10点钟之前,你到不了实验室。我都没有时间锻炼了。”
“今天早晨你的运动量早已足够了。回床上来吧,快把毯子给我。今天早晨挺冷的。”
“不行,杰里,我们不能这样。我必须到实验室去了。我们有了一批从蟑螂身上取得的新的心侧体,我上午必须提取它们。如果我今天下午不冻干它们,琼会生气的。”
“该死的心侧体,”他恼怒地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想要你的身一体。”
“我只有一个身一体,斯塔福博士。蟑螂有两个心侧体,就是这个器官能分一泌一出我的宝贝激素。你难道一点也没有学过拉丁文吗?”
在淋浴的时候,她问:“你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多时间了?我还以为你那位康托教授要求很苛刻呢。上次你在这里……”
“你什么意思,上一次?我一共只来过一次。我真希望你没有室友。”
“莉亚怎么啦?她昨晚不睡在这里,这就已经够好的了。”
“那是昨天晚上。你以为她会经常那样吗?”他正在往她屁一股上抹肥皂。
“感觉真好,”她嘴里发出满意的咕噜声,“把肥皂递给我。我来给你抹。”
他们擦干了身一子以后,她继续说:“说真的,你怎么会有时间的?我还以为你很早就到实验室了……要么,你大肆宣扬说你们细胞研究室多么忙碌,是在撒谎?”
塞莱斯蒂纳是在化学系一次关于自旋标记的研讨会上遇见斯塔福的。演讲人是斯坦福大学的哈登-麦康奈尔(hardenmcconnell)。他发明了一种采用稳定自由基和电子自旋共振的技术,这种技术后来证明在细胞膜研究中非常有用。康托想要斯塔福了解这种技术。与许多生物学家不同,教授从来不认为仪器仅仅是输出数据的黑盒子。他坚持要他的学生了解每种仪器分析技术背后的理论。就这样,斯塔福坐在了塞莱斯蒂纳-普赖斯的身边。他对有机物的稳定自由基的特一性一几乎一无所知。自从在南罗卡莱纳大学读完二年级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碰过有机化学。他只好请教他的邻座。塞莱斯蒂纳立即注意到他的两只眼睛特别大,只是目光似乎有点散乱,好像他同时在看两个东西。他的脸很窄,嘴巴宽大,,他那双眼睛因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当天晚上,他们就在学生联合会碰面,一起喝咖啡吃甜点。两天以后,斯塔福学会了怎样与塞莱斯蒂纳做一爱一。这与他另外一次(唯一的一次)一性一接触截然不同。那是在南罗卡莱纳州的哥伦比亚,是两个童一男童女之间一次非常短暂的不成功的互相探索。斯塔福被塞莱斯蒂纳迷住了,神魂颠倒。塞莱斯蒂纳最初的感觉可以形容为很复杂的感情:斯塔福的科学智慧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论他的研究和学术抱负时表现出来的热情让她感动,他在一性一方面的天真又使她心动。她作为一性一爱一导师的新角色,更是使她兴奋不已。
“艾西要今天下午才回来。他在哈佛大学克劳斯那里作学术报告。知道克劳斯是谁吗?”
塞莱斯蒂纳摇摇头。“谁呀?”
“在我们这个研究领域里,他大概是国内最权威的人了。我很惊讶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一种肿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真了不起。另外一个肿瘤叫什么?”
“别这么说。这种肿瘤很重要,就像佩顿-劳斯的肉瘤一样。”
“他又是谁?”塞莱斯蒂纳打断了他。她不喜欢动不动就提一堆科学家的名字,尤其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在无脊椎动物生物化学界肯定没有这么个人。”
“他获得过诺贝尔奖。这就足以向你证明那个肿瘤有多么重要了。不管怎么说,艾西有一个关于肿瘤的新理论。他认为它是由于蛋白质双向通过细胞膜引起的。他曾经在我们研究小组的午餐研讨会谈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其他地方谈论这件事。去哈佛演讲,他好像还有点紧张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这是一种绝妙的想法。我猜测,他大概想看看他的竞争对手们怎么想。所以他要在讲学途中停一下,去见个什么人,哈佛大学的贝纳塞拉夫(benacerraf)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卢里亚(luria)。他们是他的朋友。他们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
“这些跟诺贝尔奖有什么关系?“
“怎么啦?”斯塔福采取了守势。“真的。他们全都获得过诺贝尔奖。”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每说起一个人的名字就要提到诺贝尔奖。”
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在穿衣服。斯塔福正要穿鞋子。他站起来,直视着塞莱斯蒂纳的脸说:“我猜这是因为我们研究小组的人最近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康托假设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所有癌症的形成,如果康托的假设正确的话,他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
“听着,杰里,关于癌症我一无所知。不过,所有的肿瘤都源于同一种机理,这好像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对,但不是不可能。艾西认为:肿瘤的形成源于某种蛋白质的结构和成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这就是这个很大的‘如果’所在。当然,他必须要测试检验它。究竟如何去检验证实,现在还没有人有最模糊的想法。我很高兴我没有研究这个。我可赌不起。如果我想要找到中意的工作的话,今年我必须再单独发表一些论文。”
“这我理解。不过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博士后研究还跟着你的博士导师呢。换个地方不是更好吗?”
“当然可以。不过,艾西很特殊。他完全可以有一个规模比现在大三倍的研究小组,就像伯克利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里的那些超级明星那样。归根结底,他与他们是同一级别的。他肯定可以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美国癌症学会那里申请到科研经费,没有问题,可他竟然还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像他这种地位的人谁还在做实验。”
“琼-阿德利就还在实验室里工作。几乎天天如此。”
“琼-阿德利?”
“是的,阿德利,”她坚定地重复道。斯塔福可以看见她的鼻孔里在冒火。
“不过,塞莉,”他试图抚一慰她,结果却弄巧成拙。“阿德利不是艾西那个级别的。她只是……”他正准备说“一个年轻的女人”,却突然换了个折中的说法,“她几年前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