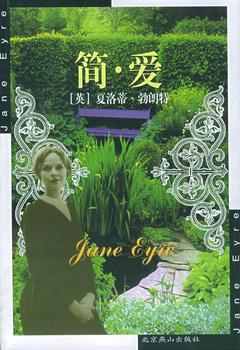你撒出了网,用猥亵的讲课和一性一感的昆虫作诱饵。你小心翼翼把那些你还没有给过分数的学生或者还不到21岁的女生扔回去。
“专题研讨”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及物动词。尽管如此,在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里,大多数研究生常常会无奈地感觉到他们是研讨会的对象,而不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用“被研讨到麻木”来描述那种过度饱和的状态。就塞莱斯蒂娜的情况而言,她每周的研讨会始于星期一下午四点钟化学系的研讨会;阿德利教授的小组研讨会在星期二午餐时间举行,历时两个小时;星期四下午四点钟是有机化学研讨会。然后是那些访问学者:诸如医学院里的生化学家、邻近的生物学大楼的发生生物学家,甚至一些到农学院去做报告的学者(农学院距离化学大楼很近,骑自行车只需10分钟就到了)。只要他们的报告可能与她的论文有关,她就必须去听。在这种压力下,研究生和博士后在挑选实际参加的报告会时,标准定得很高,就毫不奇怪了。塞莱斯蒂娜她们实验室里的人一般都不参加其研究范围以外的报告。除非研讨会的主题确实很有趣,或者不准学生缺席(每周系里的研讨会就属于这种),再不然,演讲者必须是真正的明星,或者演讲题目非常吸引人,这样才能吸引他们去参加。
格雷厄姆-勒夫金教授对于研讨会饱和综合症比大多数应邀做报告的访问学者更加敏一感,因为他不在超级明星之列。他很现实,甚至不把自己放在稍微逊色一些的明星之列。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以优秀的讲演者著称,因此受人尊敬。在生物系里,他的同事都清楚他的研究成就在信息素领域:他们把他的成果描绘成为“挺响亮的”(用这个形容词几乎隐含一着轻蔑),“还算多产”,但是“没有令人瞩目之处”。他目前的研究小组只有两名硕士生和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在霍普金斯作研究报告时,人们之所以去听,是因为他们想去听格雷厄姆-勒夫金那生动的讲课,他们并不指望听到一场有深度的科学讲座。但现在,在巴尔的摩西面700英里左右的地方,他要在一个化学系的研讨会上作报告了。琼-阿德利和她的研究小组就在这个化学系里。
勒夫金知道他为什么受到邀请。在霍普金斯大学,琼-阿德利和他保持着一种专业上的关系,它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他是一位超脱的顾问,科学事业上的知音;而她则非常聪明伶俐,但明显是个晚辈。就勒夫金而言,他们的交往不掺杂任何一性一的成分,就连一性一方面的暗示都没有。阿德利虽然比他年轻20岁左右,可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她搬到中西部去以后,他们的联系减少到圣诞节时互相寄张贺卡;偶尔交换重印的杂志,在上面写个短信之类的,只此而已。几个星期之前,,他们偶然在一个学术会上相遇了。临分手的时候,阿德利说:“格雷厄姆,什么时候请到我们那里去。”勒夫金把她的话当成客套话,没有回应,只是一笑了之。出人意料的是,几天之后,他已然在阿德利的书面邀请信里的三个研讨会日期中进行挑选了。他立即开始考虑如何让大厅里面挤满听众。在那遥远的化学系里,格雷厄姆-勒夫金这个名字和生物学家的身份是不可能成为焦点吸引大批听众的。勒夫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如何获得成功:用一性一语言添枝加叶地讲述他最近对于汗蜂的研究。
“塞莉,你一点也没有变。”勒夫金低声说,一面用手臂搂着塞莱斯蒂娜,想要亲一吻她的嘴唇。“你来接我真是太好了。”
“格雷厄姆,你也一点没有变。”塞莱斯蒂娜笑着,一面在他的脸上匆忙地没有丝毫感情地吻了一下,同时小心把他的手从身上推开。
“怎么回事?”他诧异地以嘲讽的口吻反问。“相隔两年以后,在繁忙的机场亲一吻以前的情人,有什么不妥当的?在这种地方人们互相接一吻是司空见惯的事。”
“对有些人来说,是这样。哪怕是某些前情人,对你这一位则不是这样。你不记得我们怎么会变成‘前——’?”
“塞莉,那都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了。”
“我因此老了不止两岁。”
“什么?”
“也聪明了许多岁。”
“明白了。”勒夫金原本亲一昵的声调变得实际起来。“那你为什么来接我?你对所有的贵宾都提供这种服务吗?”
“贵宾?就你?”塞莱斯蒂娜觉得带点讽刺挖苦,可能比较达意。“不,不是因为这个。”
“那好吧,是你那位教授让你来接我的。”现在他毫无疑问生气了。
“放心,格雷厄姆。琼本来想自己来接你的,可她得参加学校里的教务会。她今天晚上请你请你吃饭。其实,琼并没有要我来,是我自告奋勇地要来接你的。因为我想见你。”她又说:“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塞莱斯蒂娜加了第三匙糖。“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勒夫金注意到这一点,用匙子指着她的咖啡杯说,“仍然是个糖罐。”
“没错,”她回答,一面慢慢地搅动她的咖啡。“就喜欢吃糖来说,我仍然一如以往。你怎么样?你的白头发多了一点,不过,从演讲题目来看,你仍然是以前那个格雷厄姆-勒夫金。”
“你不喜欢我报告的标题?它还不够刺激?你认为它会吸引那些化学家来听一位生物学家演讲吗?”
“不……是的……没错,”塞莱斯蒂娜很慢地吐出这个词,音调没有任何变化。
“你什么意思?”勒夫金怀疑地问。
“没什么,我不喜欢那个标题:‘昆虫间的一夜情——汗蜂体内一性一欲抑制剂的证据’。是的,真够刺激的了。是的,它会吸引化学家来听的。毕竟,我大概是唯一了解你的化学家。”
“唯一的?琼-阿德利呢?”
塞莱斯蒂娜隔着桌子,把手放在勒夫金的手上。“格雷厄姆,我想,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琼并不了解你。”她的话音变得很严肃。“那正是我想和你谈的。”
“怎么?”勒夫金的声音听上去很古怪。
“格雷厄姆。”塞莱斯蒂娜向后靠了靠,仿佛突然想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大。“为什么你,一个56岁的教授,要勾引一个刚过法定年龄的少女?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塞莉,你怎么啦?”他悄声说。“三年前你怎么不问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我勾引你,那为什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是你到我的住所来?你怎么会——”
“与你一起到纽约去,听我的第一次歌剧?”她替他说完了这句话。“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当时并不平等吗?我并不只是说年龄的差异。”
“塞莉,你是因为怨恨而责怪我。难道最终不是我提出终止的吗?”
她回答说:“没错。最重要的词是‘最终’。你只用了12个月。”
勒夫金决定是他放弃防卫姿态的时候了。“告诉我,你为什么与一个比你大30岁的男人做一爱一,顺便提一下,他是你以前的老师。”重音落在“前”上面,听上去很刺耳。“你在我班上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成为情人。”
“格雷厄姆,不要搬弄法律。我并没有在终身教职听证会上指控你一性一騷一扰。我只想弄清楚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面对事实……”她住了口,往咖啡里又加了一点糖,慢慢地搅拌。“很抱歉,格雷厄姆,我不该生气的。”
“我也不该如此,塞莉。”他伸手把糖盅盖上。“说吧,什么事实?”
“你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不光是在课堂上。可你勾引我的时候,打破了一种信念。”
“又来了,”他打断她的话。“你只需回想一下,那次我们——”他踌躇了一下,接着往下说,“在一性一关系上变得很亲密时的情景。你在听奥尔夫的音乐——”
现在轮到她打断他了。“并且在阅读一段极具挑一逗一性一的对话,你当时正好放在那里。现在你会说那只是巧合,你想考考我拉丁文的水平。”
“不,我不会这么说的。你听音乐的时候,我只不过在摩挲你的脚趾。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制止我。”
“你会停下来吗?”
“绝对会!我甚至会给你个台阶下来。你可以说很痒。”
“我明白了。”塞莱斯蒂娜的讥讽溢于言表。“你好好想一想。你问我,一个21岁的姑一娘一,为什么……”
“女人,”他打断她。
“姑一娘一,女人——随你怎么叫。我为什么答应跟一个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的男人一起睡觉?”
“噢,我的天哪,你不是想给我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课吧,是吗?”
“我可以这么做,可我不愿意。有时候,事情是什么就什么。雪茄就是雪茄。我根本不相信我当时是在你那里寻找父亲的感觉。或许其他年轻女人会这样。我猜想还有其他的女人?”
“其他的?”
她叫了起来:“噢,格雷厄姆,别演戏了。哪怕就这一次,你诚实点好不好?你是不是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
“塞莉,没有一个人像你。”
“格雷厄姆!”塞莱斯蒂娜毫不掩饰她的愤怒。“你知道我的意思,像我一样年轻的。”
“有几个。”
“行了。我不会问你究竟有几个。有在我之后的吗?”
勒夫金盯着塞莱斯蒂娜看了一会,然后垂下眼睛。“一个。”
“我明白了。”杯子里面的咖啡已经喝完了,她加了一些糖,让女招待再来一杯。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才重新恢复某种平静。塞莱斯蒂娜重拾话题。“我猜想我在我们俩的关系中寻求的是平等的关系。我在学识上不能与你竞争,可又不想成为你情一欲的对象,至少希望你在乎我,看重我。你突然把我打发走的时候,我怨恨透了。”
“我知道,”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会有那种感觉的,在我还没开口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也希望要平等的关系。我对你的一性一吸引力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别发傻了!”塞莱斯蒂娜脱口而出。“你谈的是什么一性一吸引力?你的一性一吸引,勒夫金个人的信息素,是知识。年纪大的男人吸引年轻女一性一的是他所掌握的知识。你滥用了这一点。”
“你怎么能这么说?”勒夫金大叫起来。“我可以告诉你,你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把自己称作一性一欲的对象,这简直亵渎了我们的关系。”
“哈!”
“塞莉,你别对我‘哈’,”他苦涩地回答。“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年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纽约听歌剧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眼角观察你,而没有看舞台上唱歌的歌手。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你真不知道那一切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知道,”她平静地说。“那是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当时的一性一关系也并不丑恶,对吗?”
“是的,格雷厄姆,一点也不,在那个时候。可最终,它是丑恶的。如果我是你的唯一的话,我的感觉也许会完全不一样。可你刚才告诉我还有其他人。在我之前和之后。她们在你的生活中又代表了什么?”
勒夫金什么也没有说。他低头看着咖啡杯,右手的中指不耐烦地敲击了一下塑料桌子的桌面。塞莱斯蒂娜仍然记得这个信号:那是他数到10的方法。这一次,他敲击了那么长的时间,塞莱斯蒂娜差一点准备重复她的问题了。其实最后,也没有必要了。勒夫金用低沉的、几乎是愤怒的声音开口了。他的眼睛固定在他的杯子上,仿佛他在自言自语。
“当初在霍普金斯获得终身教授职位时,我是个很有前途的研究员。然而,授予我终身教授是因为我的教学。我始终很认真地对待讲课,在25年前,我的课就已经教得非常出色。我的研究从来没有真正地开展。我始终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至少在最初的十几年左右的时间里,可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渐渐地,我才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明星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甚至从来没有大声地对自己说过这些话。”他突然从杯子上抬起眼睛。他的眼睛很红,看上去是那样的苍老,塞莱斯蒂娜为之一震。“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些与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那天早晨塞莱斯蒂娜第二次用手触一摸勒夫金的手。“说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楚我不太可能得到我崇拜的那些科学家的承认。我的研究不重要,不足以获得他们的认可。因此我不再关注学院里的同事,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身上。我教授的课程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评价。看见教室里兴奋的面孔,听到很自然发出的笑声和好的提问,有时候还获得掌声——这些全都使我感到一种满足。然而,最终这些也不再使我满足。随着岁月的流逝,再也不了。如果我不是一直单身的话,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现在再也不够了。所以,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的学生身上。”
勒夫金凝视着咖啡杯。他用手握住它,仿佛想借此取暖。突然他把手放在口袋里面,看着塞莱斯蒂娜。“谢谢你这么耐心地听我说。”他疲惫郁闷地笑了笑。“你看,我正在向着你的问题靠拢。”
“我只对最聪明的学生感兴趣,那些我认为会成为我所向往的那种科学家的学生感兴趣。塞莉,像你这样的学生。”他再次抬起眼睛,与她的目光相遇。
她问道:“我想她们全都是女一性一?”看见他点头,她继续说:“怎么没有男生?”
“怎么没有男生?因为一性一也是很重要,而我恰巧不是同一性一恋。有什么证据比一性一更加令人信服呢?展示我的魅力,吸引那些年轻的知识女一性一,与那些年轻有魅力的男人竞争,这种想法迷住了我。你说得很对:我的信息素就是智慧。我若想证明自己还没有衰老,最有效一性一的证据就是:一位聪颖的年轻女一性一宁愿挑选我,而不是身一体诱一惑力更强的同龄人。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但却是诚实的回答。”
“格雷厄姆,为了讨论,我们姑且同意这对你来说很重要,证明你对年轻的女一性一具有魅力——”
“不,还不止是那样,”他插嘴说。“一个年轻新鲜的头脑——”
“年轻新鲜的头脑!格雷厄姆,这听上去好像是对实验对象的医学描述。”
“塞莉,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暂且跳过这个。我想要说的是:你撒出了网,用猥亵的讲课和一性一感的昆虫作诱饵。你小心翼翼把那些你还没有给过分数的学生或者还不到21岁的女生扔回去。你瞧,你捕获了塞莱斯蒂娜-普莱斯:年轻、聪明,全都有了。你一精一心策划了这一切,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被捕获了。而你?你获得了所需要的强化,以便忘记你对失去青春的恐惧,或者男一性一更年期在你体内引起的种种问题。”
勒夫金眉头皱了起来,仿佛很痛苦的样子。
她装作没有看见,继续往下说:“你抓住了我。我心甘情愿地跑到你身边。我们互相欣赏。你教给了我许多东西。我不是指我们在床第上的那些事情。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当时并没有被人利用的感觉。然后,砰!突然一声巨响!一天早晨,就在一次温馨的夜晚过后几个小时,你突然把我打发了。”
“打发了?我这么做了?不要讲得这么粗俗。”他恳求她。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就在我快活得大声叫唤过后几分钟,你对我说我们结束了。当时,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你把我当成了发泄一性一欲的对象,是你某种技巧的反应物,这种技巧是你从只有上帝才知道究竟多少个‘年轻新鲜的头脑’身上获得的。”
“塞莉……”
“不要叫我‘塞莉’。还记得你通知我你的决定时,讲的理由吗?你的,格雷厄姆,而不是我们的!说因为你快要一爱一上我了!就好像你要得什么病了似的。到目前为止,你只谈了这种关系对你有什么影响。现在我告诉你,它对我意味着什么。为了保持我的自尊,每次你跟我亲一热,抚一爱一我,亲一吻我,鼓励我取一悦你的时候,我极力说服自己有某种一性一以外的东西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必须忘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因为我必须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同龄人,是同一时代的人。或者至少是平等的,互相为对方提供些什么。我必须相信你不只是因为脸蛋、身一体或者肌肤之亲,或者是因为我驾驶执照上的年纪才和我在一起的。我必须相信你之所以在我一起,是为了与一个特殊的人在一起,与塞莱斯蒂娜-普莱斯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看重她,就像她把你看得很重一样。”塞莱斯蒂娜骤然停下来,好像她突然一精一疲力竭了似的。当她重新开口的时候,已经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口气了。“可我没有,对吗?”
“不,不是这样。你刚才并没有认真听我说话。你想要在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老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关系——“
“格雷厄姆,年龄稍大一点的男人,不是老人。”塞莱斯蒂娜开始平静下来。
“谢谢你这么更正。在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之间如何平衡呢?我的恐惧,生怕我们的关系因为你主动提出要求而终结,怎么办呢?实际上,考虑到你我之间的年龄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陷得越深,关系保持得越长,最后我的痛苦也越大。”
“你是说这就是你决定结束那一切的理由?免得你变得越来越痛苦?生怕你年龄太老了,找不到人替代我?“
“是的。”勒夫金说。“多少有点这样。”
“格雷厄姆,”塞莱斯蒂娜平淡地说,“我不相信就这么简单。”她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来。“我们走吧。我告诉琼我11点钟之前把你接到系里的。”
塞莱斯蒂娜在4点钟之前到达教学大厅。给她印象很深的是,大厅几乎全都坐满了。她最喜欢的位子是右面的走道一半的地方,坐在那里可以很快离开。现在这位子早已被人占了。她不认识那个蹲坐着的人,他不是化学系的,他占据了她的位置。显然,勒夫金的“昆虫的一夜情”吸引了很多人。塞莱斯蒂娜觉得很好奇,想看看他究竟如何演讲。她意识到她实际上从来没有听过勒夫金作研究报告。她原先一直是冲着勒夫金老师去的,是作为怀着仰慕之情的学生去的。现在,她将作为一名老练的批评家,聆听勒夫金谈论他自己的科研成果。
最初几分钟,勒夫金处于最佳状态。他指出,事实上,所有的一性一引一诱剂都是由雌一性一昆虫分一泌的。在昆虫学方面资料里,零星有些报告披露在雄一性一昆虫中存在抑制一性一欲剂存在。“‘一性一兴奋抑制剂?在雄一性一体内?’你们可能会问,”他假装很吃惊的样子,“为什么?”听众中有些学生开始窃笑,勒夫金脸上依然面无表情。他谈论猥亵的话题时总是不露声色,不鼓励无礼轻率是他的讲课风格之一。正是他不苟言笑的风度,把握有度的声调,言辞慎重的讲述,同时描述的是昆虫残暴的一性一行为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所以才在霍普金斯的讲课里,让塞莱斯蒂娜觉得难以抗拒。显然,他在课堂上魅力依旧。“我们不妨想一想人类的贞一操一带。有些种类的昆虫比我们聪明。它们不是用一条贞一操一带,而是进化出一种化学标记,加强雌一性一配偶的一性一单配一性一。”
“早期对昆虫之间抑制一性一欲剂的证据是偶然发现的。”勒夫金声明。现在他将要向听众证明这种分一泌确实存在。塞莱斯蒂娜似乎能够感觉到听众全都坐直了,仿佛有人了他们一种集体的刺激。她暗自笑了起来。一般化学报告肯定不会这样开始的。勒夫金说得对。一性一是不可阻挡的,尤其是在科学界。
“以lasioglossumzephyrum为例。”他把这个字念得很慢,一边写在黑板上。“也称作汗蜂。十多年前,堪萨斯大学的巴罗斯(barrows)报告说雄一性一的汗蜂会巡视蜂窝,勇一猛地扑向雌蜂。它之所以会这样扑向雌蜂,是由雌一性一的气味促成的。这种气味相当于一种分一泌物。巴罗斯惊诧地发现,尽管扑向雌蜂的雄蜂很多,真正与之交一配的却寥寥无几。啊哈,巴罗斯想,雌汗蜂只交一配一次。”
勒夫金的眼睛缓缓地扫视听众。场内一片寂静,他们在等待他往下讲。
“接下来是康奈尔大学的佩内洛普-库卡克(penelopekukuk)。他把一些雌蜂固定住,放在雄蜂经过的一条小河的黏土河岸上,这是汗蜂喜好的栖息地。库卡克注意到,至少有6只雄蜂会朝着被固定的雌蜂爬过去。在一两分钟里面,所有的雄蜂都会离去,只剩下一只雄蜂与雌蜂交一配。然后,他再用这同一只雌蜂再重复该实验。但是雌蜂已经失去了贞节,它现在没有吸引力了。”
“被束缚的、失去贞节的雌蜂!”多么典型的格雷厄姆用词,塞莱斯蒂娜沉思,我敢说教室里面一半的人在想奴役和束缚。怎么束缚一只汗蜂呢?
“你也许会奇怪,怎么束缚一只蜜蜂,”勒夫金继续说,仿佛他现在正在与她进行私人对话。“很简单。你只需用斯各特粘胶带粘住她的翅膀,把它粘在一根实验用的小棒上就行了。请放第一张幻灯片。”
幻灯片上出现自然状态的汗蜂栖息地;雌蜂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小木棒上。小瓶里面含有花粉、蜂蜜和水,以及一只被俘获的处一女汗蜂。第二天,另外一只处一女蜂被放进另外一只小瓶里,而前一天的牢笼里面的东西(塞莱斯蒂娜在实验中曾经鉴别过),用二氯甲烷萃取后,提供了一种fde的一性一气味。塞莱斯蒂娜不清楚fde是什么。“就是一种‘雌一性一特有气味’。”勒夫金补充说。
在积累了几百只雌蜂的fde后,人造的雌一性一汗蜂模型——包一皮裹一着黑色尼龙带的小木棒,具有了一些fde的气味。把这样一些十字架放在河岸边上,于是,这些塑料的“处一女汗蜂”释放的气味就弥漫在那雄蜂来回游弋的地方。如果那些雄蜂中有一只产生一性一冲动的雄蜂在靠近雌蜂一英寸的范围之内,面对雌蜂的时间长达5秒钟以上,它的行为就将被称为一次“盘旋”;猛扑过去与尼龙模型发生身一体接触的,被认为是假交一配。数据分析清楚地证明,一旦一只带fdc气味的尼龙处一女蜂被一只雄蜂触碰了几次以后,围着它盘旋的雄蜂的数目就会明显减少。抗兴奋剂显然是雄蜂释放的。
那种主动的反盘旋因素的分离是勒夫金个人的成就,事实证明,它直截了当,简单明了,同时也极难解释。尽管在生物学家中间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最终的化学结构清楚地证明它一点也不复杂。塞莱斯蒂娜丝毫不感到意外。她回忆起勒夫金在课堂上讲述德国化学家们第一次从蚕蛾分离出信息素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地艰难,然后又披露德国化学家最终分离出来的纯化学剂是一种很简单,早已经为人们知晓的有机醇。她当时也曾有过同样失望的感觉。勒夫金当时作了一个略微有点轻率的评论,塞莱斯蒂娜至今仍然没有忘记。“请记住,蚕蛾合成它的信息素是为了吸引另外一只昆虫,而不是吸引一位化学家,考验他的智力和勇气。我们正在谈论一性一繁殖——物种的繁衍——而不是人类智力上的愉悦。”
这天下午的听众显然并不介意化学抗兴奋剂。他们受到刺激,变得昂一奋激动,心满意足,大厅里热情的鼓掌足以证明这一点。
突然之间,塞莱斯蒂娜明白了勒夫金在机场咖啡店里面对她说的话。勒夫金的演讲报告——它并不包一皮含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内容;没有重组dna;没有蛋白质受体或者单克隆抗体;甚至于没有新颖的分析或者分光镜技术,而只是一些现代化学家全都使用的那些技术——这个讲座俘获的听众比起系里面那些雄辩的研讨会的报告,无论是出席的人数还是听众的多样化上都远胜它们。根据听众积极举手提问来看,塞莱斯蒂娜的印象是,学生们显然很欣赏勒夫金。毋容置疑,他在科学上的同行和对手不以为然。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哪一部分是来自资料——是从康奈尔大学的库卡克实验室来的,以及哪些是勒夫金和他的学生们在霍普金斯大学里完成的。
“勒夫金教授,”塞莱斯蒂娜大声问。“我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请问雄汗蜂为什么要进化出这样一种化学标记?”
勒夫金斜视着礼堂的上面。“神学?你意思是说今天神学院的学生来参加化学系的研讨会了?”这一招很聪明,这样他有时间从容地考虑如何应答。学生嗤笑着转过脸去寻找提问的人。
“抱歉,”勒夫金故意讪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是很认真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猜测。一种可能是,汗蜂首先考虑的是物种的繁殖,而不是一性一妒忌。一次交一配足以使雌蜂受一精一。标明雌蜂已经完成了它的繁殖目标,其他的雄蜂就不会再在它身上一浪一费它们潜在的生育能力,而是把它用在其他处一女蜂身上。”
“既然如此,”塞莱斯蒂娜反诘,“为什么要用‘一夜情’呢?那不是典型的描述人类行为的时髦用词吗?”
“时髦用词?我喜欢在谈论蜜蜂的前后关系时,使用这个词。”勒夫金看上去对于听众的窃笑感到很高兴。
塞莱斯蒂娜对于勒夫金无礼尖锐的反驳并不欣赏。“勒夫金教授,”她高声问道。“虽然我的用词不一定很一精一确,但是,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勒夫金迅速严厉地看了一眼塞莱斯蒂娜。他一边收拾笔记本,就像在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一样,把它们摞在一起,一边在想如何回答。这是他们在机场谈话的继续吗?如果是的话,他决定来个了断。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一夜情’。显然你不喜欢这种想法,所以你反对我用这个词。也许选择这样的题目,把它作为一场严肃的研讨会的标题,你可能认为多少有点轻率。不过,它已经起了作用,不是吗?”他把手朝挤满了听众的大厅四周挥动。“我只想到此为止:我只是用它来比喻一件短暂的事件,并不直接赋予雄汗蜂盲目求一爱一的沙文主义动机,或者表示我自己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我现在要说的是,如果你用拟人的方式看待昆虫的一性一行为的话,那么你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很快地看了一眼听众,拿起他的材料,昂首阔步地从讲台向第一排走去,琼-阿德利正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