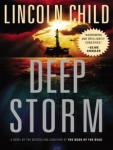“奥丽阿娜,至少您应该讲出全部事实,不要只讲一半。事实上,”他作更正地对斯万说,“那时的英国大使夫人,不知怎么搞的,会邀请我们和总统及其夫人一起出席她的晚会。大使夫人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但她好像生活在月球上,经常做这种蠢事。我们感到很吃惊,连奥丽阿娜也感到意外,再说,大使夫人对我们这些人是很了解的,她不该邀请我们参加像这样不可思议的聚会。有一个部长过去当过贼,唉,这事就算了,我们事先不知道,上了圈套,况且,应该承认,那些人那天都很有礼貌。像这样也就不错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做事经常不同我商量,她觉得那个星期应该到爱丽舍宫送一张名片。希尔贝认为这会玷污我们的名字,他这种看法可能有些过分。不过,不要忘了,即使把政治撇开不管,卡尔诺先生虽说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可他的祖父却是革命法庭的成员,一天就处死了我们十一个亲友。”
“那么,巴赞,从前您为什么每个星期都到尚蒂伊宫去吃晚饭呢?奥马尔公爵的祖父不也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吗?所不同的是,卡尔诺是一个正直的人,而菲利浦平等却是一个十足的无赖。”
“对不起,我插一句,那张照片我已经给您送来了,”斯万说,“我不明白,您怎么没有拿到。”
“这不会让我感到吃惊,”公爵夫人说,“我的仆人只把合乎他们想法的事告诉我。他们大概不喜欢圣约翰骑士团。”说完她摇了摇铃。
“您是知道的,奥丽阿娜,我去尚蒂伊宫吃饭时,并没有什么兴致。”
“兴致倒是不高,就是还带着睡衣,以防亲王留您过夜。其实,他很少这样做,他和奥尔良家族所有的人一样,一点没有教养……您知道今晚在圣德费尔特夫人家我们同谁一起吃饭吗?”德·盖尔芒特夫人问她丈夫。
“除了您知道的客人外,还有狄奥多西国王的兄弟,他是最后一刻才被邀请的。”
听到这个消息,公爵夫人脸上显露出满意神色,但话语中却表现了厌烦情绪:“唉!我的上帝,又是亲王。”
“但是这个亲王很可爱,很聪明。”斯万说。
“但毕竟不完全,”公爵夫人回答道,她像是在搜索枯肠,以便使她的思想推陈出新,“您注意到没有?最可爱的亲王并不完全可爱。没错,我向您保证!他们对什么都得要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拿不出看法,于是他们用前半生听取我们的看法,用后半生鹦鹉学舌般地在我们面前重复我们的看法。他们必须说,这个演得不错,那个演得差一些。其实根本分不出高低。我告诉您,那位小狄奥多西(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曾问我,什么叫乐队的动机。我回答他说,”说到这里,公爵夫人双眸闪出光芒,姣美的红嘴唇流出清朗的笑声,“我回答他说:‘这就叫乐队的动机。’嘿!他心里可不高兴哩。啊!我的小夏尔,”德·盖尔芒特夫人无精打采地说道,“上别人家去吃饭真是乏味透了!有些晚上,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出门!当然,死也可能同样令人讨厌,因为我们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
一个仆人进来了。就是那位和门房吵嘴的年轻未婚夫,多亏仁慈的公爵夫人出面干涉,他们才表面上和解了。
“今晚我要不要去听奥斯蒙侯爵先生的消息?”他问。
“不要去,明早再去!今天晚上我甚至不想要你待在这里。让他的仆人——你认识他——来向你报告消息,叫你去找我们好了,反正你不在。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痛快地吃一吃,玩一玩,可以在外面过夜,但是,明天早晨前我不要你在这里。”
仆人脸上漾出无限的快乐。他终于能和未婚妻在一起待好几个小时了。自从他和门房又吵了一次架,公爵夫人和颜悦色地劝他以后最好不要出去约会,以免再次发生冲突以来,他几乎见不到他的未婚妻了。想到终于能有一个晚上自由支配,他感到无比幸福,公爵夫人对此一目了然。她看到别人瞒着她偷偷享受快乐,又生气又嫉妒,心里一阵痛苦,四肢瘙痒难忍。“不,巴赞,得让他留在这里,不能让他出去。”
“奥丽阿娜,这太荒唐,您的人都跟您去了,另外,半夜里有管服装的男女仆人侍候您参加化装舞会。他在这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再说,就他一人和马马的听差是朋友,所以我宁愿把他打发得远远的。”
“听着,巴赞,不要管我,今晚上我恰恰有事要吩咐他,但说不准几点钟。您一分钟都不要离开这里。”她对那位仆人说,仆人好似泄了气的皮球。
如果说公爵夫人家纠纷不断,仆人在她府上干不多久就被辞退,那么对这一切应负责任的人却是永远也不可能辞退的,不过此人不是门房。不错,公爵夫人把重家伙交给了门房,让他干粗活,做特别累的苦差事,让他同别人吵嘴,甚至打起来。而且,他扮演这个角色时丝毫也不意识到是在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他和盖尔芒特府的其他仆人一样,非常钦佩公爵夫人待人宽厚,那些比较迟钝的仆人离开公爵府后还常回来看望弗朗索瓦丝,对她说,要是没有门房,公爵府是巴黎最好的位置。公爵夫人利用门房,就如同人们长期利用教权主义、共济会,利用犹太人是祸害的论调……一个仆人进来了。
“为什么不把斯万先生送来的东西给我拿上来?噢,对了(您知道,夏尔,马马病得很厉害),儒尔,谁去打听奥斯蒙侯爵先生的消息了?回来了吗?”
“刚回来,公爵先生。估计侯爵先生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太好了!他还活着,”公爵松了口气,喊道,“什么估计不估计的,你难道是撒旦吗?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公爵神色愉快地对我们说,“他们把他说得好像已经死了、埋了似的。一星期后,他比我还要活蹦乱跳。”
“是那些医生说他活不过今天晚上的。有一个医生还想夜里再来看他一次。他们的头头说没有必要了。侯爵先生也许现在已经死了,他全靠用樟脑油灌肠才延长了生命。”
“住嘴,蠢货,”公爵火冒三丈,喊道,“谁让你说这些的?你根本没有听懂人家对你讲的话。”
“不是对我,而是对儒尔。”
“还不快住嘴!”公爵吼道,接着转身对斯万说,“他还活着,太叫人高兴了!他会慢慢恢复的。经历这么一场危机,还能活下来,这就够了不起了。不能要求过高。用樟脑油进行一次小小的灌肠,大慨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吧,”公爵一面搓手一面说,“他还活着,还要怎样呢?经历这样一场病灾,还能活下来,这就够美的了。我甚至羡慕他有这样好的体质。啊!病人,人们总是对他们关怀备至,可对我们却漠不关心。今天上午,有一位蠢厨师,用鸡蛋黄油调汁给我烧了只羊腿,我承认,味道美极了,但正因为它太好吃,我就多吃了些,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可是人们却会像对待我亲爱的阿马尼安那样前来打听我的消息。甚至打听他消息的人太多,这会使他很疲劳。应该让他喘气嘛,不断派人去他家,会把他这个人杀死的。”
“喂!”公爵夫人见仆人退出客厅,对他说,“我不是叫你们把斯万先生送给我的装在套子里的照片拿来吗?”
“公爵夫人,那东西很大,不知能不能进得了门。我把它放在前厅了。公爵夫人要我把它拿上来吗?”
“那就算了!你们早就应该对我说嘛。不过,既然很大,那我待会儿下去看吧。”
“我还忘了告诉公爵夫人,莫莱伯爵夫人上午给公爵夫人留下一张名片。”
“什么?上午?”公爵夫人很不高兴地说,她觉得,这样年轻的女人是不允许在上午留名片的。
“将近十点钟,公爵夫人。”
“把名片拿给我看看。”
“奥丽阿娜,您说玛丽嫁给希尔贝的想法很可笑,”公爵把话题拉回到一开始说的事情上,“其实,是您自己写历史的方式奇特。如果说在这场婚姻中有谁干了蠢事的话,那也是希尔贝,他恰恰娶了一个和比利时国王血缘很近的女人,那位国王篡取了布拉邦特这个姓,可那是我们的姓。总而言之,我们和黑森家族有着相同的血缘,而且我们是长房。谈论自己肯定是愚蠢的,”他对我说,“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您,不管我们去达姆施塔特,还是去卡塞尔和黑森选侯采邑的任何地方,诸侯们每次都毕恭毕敬地后退一步,让我们这些长房子孙走在前面。”
“巴赞,您不会对我说那位曾在他们国家的军队里当过护士长,后来和瑞典国王订了婚的女人是……”
“哦!奥丽阿娜,您太过分了,您似乎不知道瑞典国王的祖父曾在波城种过地,可是,九百年以来,我们在整个欧洲一直占据首位。”
“尽管如此,如果有人在大街上喊:‘瞧,瑞典国王。’大家都会一直跑到协和广场去看他,可是,如果有人喊:‘瞧,德·盖尔芒特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是谁。”
“强词夺理!”
“此外,我不能理解,既然布拉邦特公爵爵位已经转入比利时王室,您怎么还不死心。”
仆人手中拿着莫莱伯爵夫人的名片,或者说拿着她当做名片留下的那张纸回来了。她以身上没带名片为理由,从口袋里掏出她收到的一封信,把信纸放回口袋,在写着她的名字莫莱伯爵夫人的信封上折了个角。那年流行大规格信纸,因而信封也很大,这张手写的“名片”比一般名片差不多大一倍。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莫莱夫人的简朴,”公爵夫人不无揶揄地说,“她想让我们相信她没带名片,想标新立异。但是,这些我们都见过,是不是,我的小夏尔,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况且我们自己也够标新立异的,不会不了解一个半青半黄的小妇人想的是什么。她挺有魅力,但在我看来,她羽毛还没丰满,不要以为用信封充当名片和在上午十点钟留名片的做法,能轻而易举地震惊社交界。她那老耗子母亲会向她证明,干这样的事,她们一样得心应手。”
斯万想到公爵夫人(她有点嫉妒德·莫莱夫人在社交界的成就)还真能本着“盖尔芒特精神”找到一些挖苦话来回敬这位送名片来的女来访者,不禁哑然失笑。
“关于布拉邦特公爵爵位问题,我已给您说过一百遍了,奥丽阿娜……”公爵又说。公爵夫人根本没有听他讲话,而是对斯万说:
“小夏尔,我等着瞧您的照片都等得不耐烦了。”
“哦!extinctor draconis latrator anubis。”斯万说。
“对,您用威尼斯圣乔治教堂作比较,实在高明。只是我不懂为什么要说阿努比斯?”
“拔拔尔的祖宗不像阿努比斯吗?”德·盖尔芒特先生问。
“您想看他的巴巴尔?”德·盖尔芒特夫人神态冷淡地说道,这是为了表示她本人对这个同音异义谐语也很瞧不上。“我可是两个都想看。”她进而又说。
“听着,夏尔,我们下去等车吧,”公爵说,“我们到前厅去交谈,因为我妻子不看见您的照片是不会让我们安静的。说实话,我可不像她那样迫不及待,”他又得意洋洋地说,“我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可是,再不下去,她会宁愿让我们死的。”
“我举双手赞成,巴赞,”公爵夫人说,“我们到前厅去,至少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您的书房下去,而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布拉邦特伯爵的后代。”
“关于这个爵号是怎样加入黑森家族的,我已对您讲过一百遍了,”当我们去看照片的时候,公爵说道(而我却在想着斯万给我带回到贡布雷的那些照片),“一二四一年,布拉邦特家族中有一个人同图林根和黑森的最后一代诸侯的女儿结婚,因此,更确切地说,是黑森家族的亲王爵位归并到布拉邦特家族中来了。再说,您也应该记得,我们曾用‘兰堡属于征服者’的战斗口号,这同样也是布拉邦特公爵们用的战斗口号。后来,我们用布拉邦特的武器换来了盖尔芒特的武器,这个口号才停止使用。况且,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纵然有格拉蒙家族的先例,我也不会改变看法。”
“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说,“那是因为比利时国王征服了兰堡……而且,比利时王位继承人叫布拉邦特公爵。”
“我的宝贝,您说的这个是站不住脚的,是绝对错误的。您和我一样清楚,有些爵位像是奢华的陈设,领地被人窃取了,但爵位却依然完好地存在。例如,西班牙国王就自称是布拉邦特公爵,这就意味着他的祖先也占有过布拉邦特,当然比我们要晚得多,但比比利时国王要早。他还自称是勃艮第公爵,东、西印度国王,米兰公爵。然而,他已不再拥有勃艮第、印度和布拉邦特了,正如我和黑森亲王都不再拥有布拉邦特一样。西班牙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宣称自己是耶鲁撒冷国王,但他们谁也不掌握耶鲁撒冷。”
他稍停片刻,由于“正在审理的案件”,怕提到耶鲁撒冷会使斯万尴尬,但他马上就接着往下讲了:
“您说的那些对什么都合适。我们曾是奥马尔公爵,公爵领地合法地归入了法国王室,正如儒安维尔公爵领地、谢弗勒丝公爵领地归入阿尔贝家族一样。我们并不要求恢复这些封号,正如我不要求恢复诺瓦穆蒂埃侯爵称号一样。诺瓦穆蒂埃侯爵领地曾属于我们家族,后来非常合法地成了拉特雷默伊耶家族的采邑。但是,尽管某些让与是有效的,但不等于说所有的让与都有效。例如,”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小姨子的儿子称作阿格里让特亲王,这个爵位也和拉特雷默伊耶家族的塔兰托亲王爵位一样,都来自疯女人霞娜。然而,拿破仑一世却把一个士兵册封为塔兰托亲王,当然,士兵本人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兵。但是,拿这件事和拿破仑三世册封贝里戈尔为蒙莫朗西公爵相比,前者超越的权限更大,因为贝里戈尔至少有一个姓蒙莫朗西的母亲,而那个士兵成为塔兰托亲王却全凭拿破仑的个人意志。但这并不能阻止谢·代斯当士在影射您的孔代叔叔时,问帝国检查官是不是到万森墓地去捡过蒙莫朗西公爵的爵位。”
“听着,巴赞,我巴不得跟您到万森墓地,甚至跟您到塔兰托去一趟呢。对了,我的小夏尔,刚才您给我讲威尼斯圣乔治教堂时,我就想对您说,明年我和巴赞想去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过春天。要是您能和我们一起去,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且不说看见您我有多么高兴,您想一想,您给我讲了那么多诺曼第人的征服史和古代史,您想一想,和您一起进行一次旅行,该多么美好!也就是说,就连巴赞,怎么说呢,就连希尔贝,也会得益。因为我感到,当我们参观古老的罗马教堂和那些就像文艺复兴派画家画出来的小村庄时,如果有您给我们当讲解员,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包括觊觎那不勒斯王位,都将会使我产生兴趣。现在,我们要看您的照片了。把套子拆开。”公爵夫人对一个仆人吩咐道。
“不,奥丽阿娜,今晚不要看!明天再看。”公爵哀求道。他看见照片大得吓人,早已向我做出恐惧的表情了。
“和夏尔一起看,我会感到愉快。”公爵夫人笑吟吟地说,微笑中夹杂着虚假的欲念和复杂的心理,因为她想让斯万高兴。她在说她高兴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像一个病人在说他高兴吃一只橘子一样,或者就像她一面在和朋友们偷闲,一面向一位传记作家透露她的兴趣爱好。
“他以后专门来看您一次,怎么样?”公爵说,他妻子让步了。“只要你们乐意,你们可以一起在照片前待三个钟头,”他不无嘲笑地说,“不过,这玩意儿那么大,您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卧室呗,我要随时都能看见它。”
“啊,随您的便,放在您的卧室里,我倒可以省得看见它了。”公爵说,无意中泄露了他和妻子关系不好的秘密。
“好吧,你拆的时候小心点,”德·盖尔芒特夫人吩咐仆人(出于对斯万的礼貌,她对仆人千叮万嘱),“也不要损坏套子。”
“连套子都不能损坏!”公爵双臂举向天空,对着我的耳朵说。“斯万,”他继而说,“我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可怜的丈夫,我佩服您竟找到这样大的套子。您是在哪里找到的?”
“是在照相制版店里,寄这一类东西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过,他们很愚蠢,因为我看见上面只写了‘盖尔芒特夫人’,没有写‘公爵夫人’。”
“我原谅他们,”公爵夫人漫不经心地说,她似乎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喜不自胜,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就抑制住了,马上又对斯万说,“怎么!您不说说,到底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去意大利?”
“夫人,我确信这是不可能的。”
“蒙莫朗西夫人倒是比我幸运。您同她一起去过威尼斯和维琴察。她对我说,和您在一起,她看到了许多东西,如果您不在,她是永远也看不到的,别人谁也没有谈到过,她说,您让她看到了闻所未闻的东西,即使是熟悉的东西,也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细节。如果您不在,她可能从跟前经过二十次也决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她确实比我们幸运……您拿着斯万先生装照片的大套子,”她对仆人说,“替我折一只角,今晚十点半把它送到莫莱伯爵夫人家去。”
斯万哈哈大笑。
“不过,我想知道,”德·盖尔芒特夫人问斯万,“您怎么提前十个月就知道您不能去意大利?”
“亲爱的公爵夫人,您如果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您。首先,您已经看到,我身体很不好。”
“是的,我的小夏尔,我看出您的气色不好,我对您的脸色很不满意,不过,我不是要您一个星期后就做这件事,而是十个月以后。要知道,十个月的时间够您治病的了。”
这时,一个仆人前来报告说,车已经备好了。“走吧,奥丽阿娜,上车吧!”公爵说,他早已急得跺脚了,好像他自己也是那些等人上车的一匹马。
“那么,您简单说一句,什么原因使您不能去意大利?”公爵夫人一面问斯万,一面站起来准备同我们告别。
“亲爱的朋友,几个月后我就要死了。去年年底,我看了几个医生,他们说,我的病很快就会断送我的性命,不管怎样治疗,我也只能活三四个月,这还是最长的期限。”斯万微笑地回答,这时,男仆打开前厅的玻璃门,让公爵夫人过去。
“您胡说什么呀。”公爵夫人嚷道,她停下脚步,抬起她那漂亮而忧郁的、充满着怀疑的蓝眼睛,但只停了一会儿,便又向马车走去。
她生平第一次同时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责任:一个是上马车到别人家去吃饭,另一个是向一个行将死亡的人表示同情,她在礼节细则上找不到可供遵循的原则,不知道该作怎样的选择,于是,她认为应该装出不相信存在第二个责任,这样就可以服从第一个责任,况且,此刻这第一个责任需作的努力要小一些,她想,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否定第二个责任。“您这是开玩笑吧?”她对斯万说。
“那这个玩笑就开得太有意思了,”斯万嘲弄地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您讲这个,我一直没对您讲我的病。但是,既然您问我,而且说不定哪天我就会死去……不过,我不愿意耽搁您,您要出去吃饭。”他接着又说,因为他知道,对别人来说,他们应尽的社交责任比一个朋友的死活更重要,他懂得礼貌,因而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但是,公爵夫人也懂礼貌,她也隐约地感觉到,对于斯万来说,她出去吃饭,没有他的死重要。因此,她一面继续朝马车走去,一面垂下肩说:“这顿饭无关紧要,不用管它!”但是,这话惹恼了公爵,他大声嚷道:“行了,奥丽阿娜,别在那里和斯万穷聊、哀叹个没完了!您明明知道,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一到八点就要开饭的。您应该清楚您要做的事,您的马车已等您足足五分钟了。请您原谅,夏尔,”他轻声对斯万说,“差十分钟就八点了。奥丽阿娜总是迟到,到圣德费尔特妈妈家要五六分钟呢。”
德·盖尔芒特夫人坚定地朝马车走去,最后一次同斯万说再见:“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您知道,您所说的我一个字也不信,但应该在一起谈一谈。他们可能把您吓傻了,哪天您愿意,来我这里吃午饭(对于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切都是通过请吃午饭解决的),您把日期和时间告诉我。”她撩起红裙子,把脚踩在踏板上。她正待进车,公爵看见了这只脚,大吼一声:“奥丽阿娜,您出什么洋相,倒霉鬼。您怎么还穿着黑鞋!可衣服却是红的!还不回去换那双红鞋,要不这样,”他对男仆说,“您快去叫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把红鞋拿下来。”
“可是,朋友,”公爵夫人看到斯万正和我要出大门,但想等马车出发后再离开,她看见斯万听到了公爵的话,感到很尴尬,便柔声回答道,“既然我们要迟到了……”
“不,还来得及,八点还差十分,到蒙索公园用不着十分钟。再说,有什么办法呢,即使八点半到,他们也得耐心等着,您总不能穿着红衣服、黑鞋子去吧。再说,我们不会最后一个到的,嘿,还有萨斯纳日夫妇呢,您知道,他们从来不会在八点四十分以前到。”
公爵夫人只好回卧室去换鞋。
“咳,”德·盖尔芒特先生对我们说,“可怜的丈夫,别人总是嘲笑他们,可他们毕竟还是有长处的,没有我,奥丽阿娜就穿着黑鞋去做客了。”
“这并不难看,”斯万说,“我注意到黑鞋了,但我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合适。”
“我没说难看,”公爵回答,“但是鞋子和衣服颜色一样,显得更雅致。再说,你们放心吧,到不了目的地她自己就会发现的,到时候,又该叫我回来取鞋了。那样,我九点钟才能吃上饭。再见,我的孩子们,”他轻轻推开我们说,“趁她还没有下来,你们快走吧。不是她不喜欢看见你们,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喜欢看见你们了,如果她看见你们还没走,她又要同你们讲话,本来她就很累了,再说话,那她吃饭时会累得半死的。再说,我坦率地向你们承认,我都快饿死了。上午刚下火车,午饭没有吃好,虽然有美味可口的用鸡蛋黄油调味汁烧的羊腿,但现在让我上餐桌,我决不会不高兴,决不会。啊!八点差五分了!女人就爱磨蹭!她会让我们两人都饿得胃抽筋的。她的身体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结实。”
公爵对一个濒死的人讲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的身体不好丝毫也不感到不自在,因为在他看来,他妻子的身体更重要,更使他感兴趣。因此,仅仅出于良好的教养,为了让斯万高兴,他客气地把我们送到门口后,以洪亮的嗓音高声地对着已经走到院子里的斯万喊道:
“喂,您哪,别信医生那一套。让他们的话见鬼去吧!他们都是蠢驴。您的身体好着呢。您比我们谁都活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