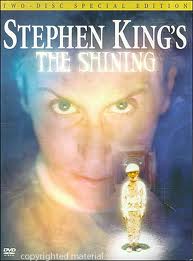这城市看上去不对劲。我努力摆脱紧张情绪,以便弄清那儿的实情——当然,我既没指望看到什么表面上的异常现象,老头子也没指望我能看见。但这里就是不对劲。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实际上却不对劲,像是一出蹩脚导演的戏,什么都没问题,但就是少点滋味。我极力琢磨出是哪儿不对劲,可怎么也琢磨不出头绪。
堪萨斯城居民众多,许多住户已在这里居住达百年之久。时光仿佛从他们身边绕过,没有触动他们。孩子们在草坪上打滚玩耍,住户们坐在夏夜清凉的前庭纳凉。那些古怪、庞大、年代悠久的房屋,由早已不在人世的古代行会工匠一块砖一块砖砌成,透着朴实无华的魅力。看到这些居民区,人们不禁纳闷,堪萨斯城有伤风化的名声是怎么得来的。古老的聚居地固若金汤,不可触及。
我避开狗、皮球和互相追逐的孩童,在居民区中巡行穿梭,一心想熟悉这里的情况。此时正值一天中的松弛休闲时分,人们到这会儿才得空喝点东西,浇浇草坪或是和邻居聊聊天。
情况仿佛就是这样。我看见前面花坛里有个女人,正在俯身侍弄花草。她穿一件太阳装,后背跟我一样干干净净。不,比我更干净,毕竟我还在夹克里塞了一团布。她和旁边的两个孩子身上显然都没有主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大热的天,甚至比华盛顿还热。我开始寻找光着背的人,穿着太阳装的女人和穿着凉鞋短裤的男人。尽管名声不好,堪萨斯城地处“《圣经》地带”,颇受清教影响,那儿的人不会像拉古纳比奇或是科勒尔盖布尔斯的人那样,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兴奋地集体脱衣。因此,即使最热的大气,成年人衣冠整齐也不足为怪。
我发现两种着装的人都有——但比例显然不对。很多孩子因为天热穿得很少,可我驱车走了几英里,只看到五个成年女人和三个成年男人光着背。
按说我至少应该看到五百个光背的人,因为正是大热天。
我顿然明白了,有些穿外套的人身上显然没有主人,但通过比例简单推算一下就能明白,足有百分之几十的人被主人控制了。
这座城市被“搞定”了,但不是以我们在新布鲁克林那样的方式“搞定”的。这座城市已经饱和了。主人不仅控制了城里的要员,而且占领了整座城市。
我只觉得一阵恐慌,恨不得立即发动汽车,直接从大街上起飞,全速驶离红区。他们已察觉我从收费站入口处的陷阱脱身了,一定在找我。或许我是惟一的自由人,驾车行驶在这座城市——周围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我努力镇静下来,作为特工,神经紧张对自己或是老板都没什么好处,也无益于摆脱困境。可我还没有完全从被鼻涕虫附身的噩梦中完全惊醒,恢复平静的确很难。
我数了十下,定定神,好理出头绪。看来我错了;它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主人渗透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我想起不足两周前的亲身经历,回忆起我们是如何招募人员,让每一个寄主都发挥作用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第二批货,堪萨斯城几乎可以肯定是第二批货运点之一,它附近肯定有飞碟着陆点。
但还是做不到呀,要将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渗透到饱和的程度,它们肯定需要不止一艘飞船,至少得有十几艘。但是如果有那么多飞船,我们的空间站一定早就通过雷达跟踪着陆轨迹发现它们了。
或许它们没有我们可以跟踪的轨道?不是像火箭一样依一定轨迹着陆,而是凭空冒出来?也许它们用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古老的“虫洞”什么的?我不清楚什么是虫洞,也怀疑是否有人清楚,可这种方法确实是一种避开雷达探测的着陆方式。我们不知道主人在工程技术方面有多大能耐,凭人类自身的标准来猜度外星主人的弱点,这样做显然不稳妥。
但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推出的是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结论,因此,在向总部汇报前我必须理清头绪。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如果鼻涕虫实际上几乎控制了整座城市的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显然它们尚未撕下伪装的面具,而是暂时让这座城市看上去仍然是自由之城。我也并不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惹人注目。
我一边想一边漫无边际地慢驶了一英里,不觉驶入广场周围的零售区。那里人群密集,又有警察,我赶紧掉头,擦着边驶过零售区,这时恰好经过一座公共游泳池。我观察着它,分析着它。
一句话,分析的结果让我陷入了矛盾之中。
大门紧闭,上面挂有牌子——“本季停业”。
一座游泳池在酷热的夏季关门停业?这意味着什么?显然游泳池已经歇业,而且也不会再开张了。然而在最赚钱的季节关闭游泳池,这决不符合经济规律,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就亏大了。
但是游泳池这种地方不太容易伪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比起游泳池停业,大热天没有人光顾泳池更引人注目。而傀儡主人向来十分注意人类的思维方式,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来设计骗局。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亲身体会!
线索一:该市收费站入口处有陷阱;线索二:穿裸背太阳装的人太少;线索三:游泳池关闭。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鼻涕虫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就连我这个被“它们”附身过的人也估量不到。
故可推断:“反冲击方案”建立在对敌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因而实施这一方案无异于用弹弓捕犀牛,自不量力。
反驳意见:我自以为看见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似乎能听到马丁内斯将我的报告撕得粉碎,克制地嘲讽我。说我关于堪萨斯城的种种猜想毫无根据,并感谢我对此所持有的浓厚兴趣,但我现在需要彻底休息,别那么神经紧张,现在,先生们——
呸!
我必须获得有力的证据,让老头子说服总统,否决官方顾问们的意见,做出理性的决断,而且我一定得马上取证。即使不考虑交通法规的因素,我也无法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缩短到两个半小时以内。
怎样才能挖掘出有力的证据?是否应该深入市中心,和人们交往,然后再告诉马丁内斯,我敢肯定几乎每一个我所见到的人都被主人控制了。怎样证明这一点?我自己又怎么会对此坚信不疑?我没有玛丽的超人天分。只要泰坦星人继续上演“一切运转正常”的剧目,我手里掌握的就只有少得可怜的情况:满城都是圆肩膀的人,而裸露后背的人则少得可怜。
没错,收费站入口处设了一个陷阱。我开始明白它们是如何彻底渗透这座城市的了,前提是有足够多的鼻涕虫。
我预感到在出口处、发射台或是市区其他出入口,也会遭遇类似的圈套。
每一个离开此地的人都将成为主人新的代理人;同样,每一位来访者皆会成为新的奴仆。
我对这一判断深信不疑,甚至不用到发射台去验证它。我曾在“宪法俱乐部”设了一个这样的圈套,结果进来的人无一逃脱。
刚才拐弯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出售《堪萨斯城星报》的报摊。我转过一个街区又折回来。停车走下来。往投币口塞了一角钱,等着报纸印出来。等待的时间异常漫长,可这是我自己神经紧张所致,感觉每一个路人都在盯着我看。《星报》的套路一贯是呆板无趣,既没什么兴奋事,也未谈及紧急事什,更没提到裸背计划。头条新闻标题为《太阳黑子风暴干扰电话通信》,副标题为《太阳静电将堪城半隔离》。配有一幅图片,三色半立体的太阳表面被宇宙黑子损毁,这幅照片注明发自帕洛马天文台。
照片很可能是捏造出来的,要么也许是从报社图书馆调出的一张真照片,上面还加上一条令人信服却不怎么有趣的说明,解释了为什么玛米·舒尔茨(本人未遭鼻涕虫附身)无法和在匹兹堡的奶奶打通电话。
报纸上的其他内容吭陴来一印正常。我把报纸夹在腋下准备有空再细看,然后转身向车子走去……就在这时,一辆警车悄然驶来,挡住了车头,一个警察下了车。
警车仿佛有凭空变出一大群人的本领,刚才街头还是空无一人,否则我决不会停车,而顷刻间周围到处是人,警察正向我走来。我暗暗将手向枪移去,我无法确定周围的绝大部分人是否同样危险,否则我早就把他撂倒了。
他在我面前停下来,和气地说道:“让我看看您的执照。”
“当然可以,警官先生。”我应声答道,“执照夹在了具箱里。”
我从他身旁走过,好让他跟在身后。我感觉他犹豫了一下,继而就上了钩。我引他绕到两车间的远端,这样我便知道他的车里有没有同伙。结果再好不过。更重要的是,车子把我和无辜的路人隔开了。
“那里就是,”我指着后备箱说,“执照在里面夹着。”
他又犹豫了一下,朝里看了看,趁着这当口,我使出一招最新才在实践中学会的新功夫。左掌一击,向他劈去,抓住他的肩膀,拼尽全力狠命一挤。
结果又是“被车撞了的猫”,只见他的身体猛地颤了一下,开始抽搐。没等他倒地,我已经上了车,一脚踩下油门。旋即,正像在巴恩斯的外间办公室一样,假面具忽然揭下,人群向我逼近。有个年轻女人用指甲死死抓住光滑的车体,被车子拖了五十多英尺才摔了下来。此时我已加速行驶,穿梭在迎面驶来的车流中,随时准备起飞,但苦于没有空间。
这时左边出现十字路口,我开了进去,却发现这一步走错了。林荫大道上空枝叶交错,让我无法起飞。下一个路口则更糟,我诅咒城市规划员把堪萨斯城建得像个公园似的。
不得已,我只好放慢速度。眼下我正以市区限速行驶,一边寻找一条足够宽阔的主干道好违规起飞。大脑在飞转,可我明白找不到这样的路。这时候,对主人的熟悉帮了忙。除了“直接会谈”外,泰坦星人骑在傀儡身上发号施令,他用寄主的眼睛看,并采用各种方式利用寄主的任何器官接收、传递信息。
我很了解这一点,于是我知道:除了附着在警察身上的那条鼻涕虫之外,其他隐藏在角落的鼻涕虫不会找我这辆车,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在场的别的主人也会寻找我,可它们只有寄主的身体条件和素质。我决定不必再理会他们,放过他们,到另一个街区去。
还有将近二二十分钟,我决定用寄主作为人证。因为被附过身,他能讲出城市里发生的事情,我一定得解救出一个寄主。
我必须捕获一个被鼻涕虫附体的男人,除掉或者杀了主人而不伤害寄主,然后把他绑架回华盛顿。眼下已经来不及作仔细规划,再去挑选这样一个人,我必须马上行动。
正想着,眼前就有个男人在街区走着。他手里拿着公文包,看样子是要回家吃晚饭。
我在他身旁停下,向他打招呼:“嘿!”
他停住脚步,“怎么了?”
我答道:“我刚从市政大厅来,没时间作解释了。上车我们再好好谈一谈。”
他又问:“市政大厅?你在说什么?”
我说:“计划有变,别浪费时间了,上来!”
他向后退着,我跳下车,向他隆起的肩膀抓去。可什么也没有,我的手抓到的只是骨头突出的血肉之躯。他开始尖叫救命。
我跳上车,飞速离开那里。过了几个街区才放慢速度,重新考虑这件事。难道我弄错了?是我神经过分紧张才会无中生有,草木皆兵吗,
绝不会!我秉承了老头子不屈不挠的意志力,面对事实,实事求是。收费站、太阳装、游泳池以及售报机旁的警察……这些事实都摆在面前——最后这一事件只能说明是偶然的巧合,不管几率多么低,我却挑中了一个尚未被主人征用的人。于是我又开足马力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浇草坪,样子既土气又过时,我有几分想放过他,可眼下没时间了,而且他穿着厚重的汗衫,可疑地隆起。要是我看见走廊上他的妻子,我就会放过他了,因为她穿着胸罩和裙子,不可能被主人附体。
我停下车,他诧异地抬起头。
我重复老话说:“我刚从市政大厅来,我们需要马上好好谈谈,上车!”
他平静地答道:“进来到屋里谈,车子太显眼了。”
我想拒绝,可他已经转身向房子走去。当我跟上去走过他身旁时,他悄声说道:“小心,那女人不是我们的人。”
“你妻子吗?”
“对。”
我们在门廊停下,他说道:“亲爱的,这位是奥基夫先生,我们要到书房谈点正事。”
她微微一笑,答道:“当然好喽,亲爱的。晚上好,奥基夫先生。天真热,不是吗?”
我应声附和,她又继续织毛衣。我们进了屋,他把我领进书房。在这女人面前,我们俩都维持着伪装,所以我只好以客人的身份先进屋。但我实在不喜欢背朝着他。
所以,他击打我脖子根的时候我早有几分提防。我打了个滚倒下去,没受什么伤。接着又滚了一下,停下来躺在地上。
在训练学校,教练用沙袋狠打倒下去试图起身的学员。我想起拳击教练以低沉的比利时口音说的话:“勇敢的人再次站起来,结果只能是丧命。要做懦夫——躺在地上反击。”
于是我躺着,用脚后跟威慑他,一有机会就反击。他向后退着,我够不着他。他没枪而我却有,但屋里有壁炉,里面拨火棒、铁锹、火钳一应俱全。他围着壁炉绕了一圈。
我刚好能够着一张小桌子。于是我翻滚过去,抄着桌子腿向他扔过去,趁他还没抓住拨火棒,桌子正砸在脸上,接着我就骑到他身上。
他的主人快要被我掐死了,主人垂死挣扎的同时,他本人也在抽搐。这时我才听到令人神经分裂的尖叫。他的妻子站在门口。我跳起来又给了她一拳,正中她的双下巴,她应声倒下,我又回到她丈夫身旁。
抬起一个浑身瘫软的人异常困难。和让他安静点相比,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把他扶起来背到肩上。他真是不轻!还好我手脚利落,身体壮实。我设法将这个笨重的家伙快步拖向车子。不知道刚才打斗的声音有没有惊扰到四邻,可是他妻子的尖叫一定把那一片半个街区的人部给吵醒了。街西边有人开门探出脑袋。但到目前为止,附近没什么人。看到车门开着,我很高兴,赶忙走过去。
接下来就让人遗憾了。一个讨厌鬼,模样酷似先前给我找麻烦的那个乳臭小儿,正在车里胡乱摆弄着操纵仪。我一边诅咒,一边把俘虏塞到后座,然后向这小家伙抓去。他向后一缩挣扎着,可我一把将他提起来扔了出去,正撞到第一个冲出来追我的人怀里。
这下我得救了,趁他甩丹小鬼的工夫,我猛地跳进驾驶席,来不及关门、系上安全带,疾驰而去。拐第一个弯时好歹把门关上了,我自己也差点从座位上飞出去。接着开上一条笔直大道,好让我抽空系好安全带。我急拐一个弯,差点撞上一辆汽车,又继续行驶。
终了驶入一条宽阔大道,我猛地按下起飞键。也许车身有几处损毁,可我来不及考虑那么多。等不及升到预定高度,我就费力地向东飞去,同时继续爬升。我手动操纵空中轿车飞越密苏里,所有推进火箭全用上了,好让车全速飞行。这回不顾一切的违规起飞让我幸免一死。在哥伦比亚上空,刚发射完最后一枚火箭,我就感到车身剧烈地震动。有人发射了一枚拦截飞弹,我想大概是超高速飞弹——讨厌的东西就在我刚才的位置炸开。
幸好再也没有飞弹射来,否则我就成了活靶子,却无力还击。这时右舷摊进器开始迅速发热,也许是因为车身几乎中弹,或许是出于机器超负荷,我只能听任它发热,祈祷机器再撑十分钟而不要散架。接着我驶过密西西比河,指针一摆,显示“危险”,我关掉右舷推进器,让空中轿车勉强用左舷推进器飞行。三百英里是最快速度,而我已驶出红区,回到自由人类的身旁。
直到那时我才有空看几眼我的乘客。他还在老地方,仰卧在地板垫上,不知道是昏过去了,还是死了。既然已经回到了自己人当中,我就无权超速行驶了,也没理由不使用自动驾驶。我叭地打开异频雷达收发器,发出请求行驶空域的信号,未等回音我就将操纵盘切换到自动驾驶挡。空管兴许在诅咒我,把我的信号记录在案。不过他们还是会接纳我进入系统。我放慢速度,又察看了一下我的证人。
他有气儿,不过还昏迷不醒。我用桌子砸他,让他脸上挂彩了,幸好骨头没断。我拍拍他的脸,又用指甲掐他的耳垂,但怎么也弄不醒他。
那条死鼻涕虫开始发臭,可我没法处置它,只好听任他继续昏迷,回到驾驶席。
计时器显示此时是华盛顿时间二十一点三十七分,还有六百多英里的路程。我全速启动一台发动机,径直向白宫老头子那儿赶去,午夜一过就会到达华盛顿。此次任务没能完成,所以老头子必定饶不了我,肯定会让我留校罚站,不放我回家。
我想碰碰运气,试着启动右舷推动器。结果不行,可能是机器受不了了,需要彻底检修。看来任何仪器转得太快都会非常危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试图和老头子接通电话。
但是电话打不通,或许是当天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颠簸太多,把它震坏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印刷电路板、晶体管等全套装备都嵌在塑料里,差不多和感应引信一样抗冲击。我只好把电话装回口袋,觉得今天已经够我受的了,不值得再为这件事大惊小怪。我转向车上的通话装置,按下紧急键,“控制台!”我呼叫道。“控制台!有紧急情况!”
屏幕亮了起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令人宽慰的是,他裸着身体出现在屏幕上。“控制台回复——福克斯十一区。你在空中做什么?自从你进入辖区,,我一直在联系你。”
“别介意!来不及解释了。”我厉声说,“给我接通最近的军线,有紧急任务!”
他看上去有些疑惑,不过屏幕闪烁着变成空白。另一幅画面逐渐清晰,显示出一座军事情报中心。我满心欢喜地看到,每个人都裸露到腰部。最前面是位年轻的警卫员,我真想亲他一下。不过我说道:“紧急军情——给我接通五角大楼和白宫。”
“你是谁?”
“没时间解释了,没时间了!我是政府特工,你就是看了身份证也认不出我的身份。赶快!”
要不是一个年长些的男人把他推开,我本可以说服他的。从帽徽上可以看出这人是飞行联队指挥官。他只说了一句:“马上着陆!”
“你瞧,长官,”我说,“我有紧急军务,你一定要帮我接通线路,我……”
“我这里才是紧急军务,”他打断我说,“所有民用机都已在三小时前着陆了。马上着陆!”
“可我得……”
“着陆!不然就把你击落。我们一直在追踪你,我马上会出动一架拦截机冲到前方半英里处阻拦你。要么着陆,要么就一意孤行,等着领教拦截机的厉害。”
“听我说,我会着陆的,可我得……”他挂断了。我张口结舌。
第一架拦截机突然出现在我前面半英里的地方,我只好着陆。
我的着陆动作但七八糟,幸而我和我的乘客都没受伤。他们向我发射照明弹,猝然下降向我扑来,我还以为要被炸得粉身碎骨呢。接着我被带进去和飞行联队指挥官本人碰面。他甚至帮我接通了电话,当然这是在心理分析小组先对我施行催眠测试、再把我弄醒之后的事了。
这时已是五区时间一点十三分,而“进攻方案”已经实行了十三分钟。
老头子听着汇报,低声咒骂着,叫我闭上嘴,早上再来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