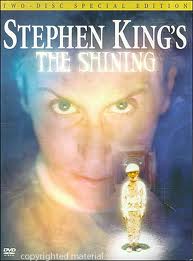我们在白宫同一间会议室会合,这让我想起几周前总统发表讲话后的耶一夜。爸爸、玛丽、雷克斯顿和马丁内斯在场,内阁成艮无一到会,取而代之的是实验室的将军、黑兹尔赫斯特博士以及吉布西上校。得知他一直被排除在这次大行动之外以后,马丁内斯急于挽回一些面子。
没有人理会他。我们的目光都投向覆盖整面墙的一幅地图上。自从热病计划的空投行动开始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天半,然而密西西比河谷一带仍旧红灯闪烁。
空投已经取得成功,我们只损失了三架飞机。但我仍感到胆战心惊。根据方程式可知,处于直接会谈范围内的所有鼻涕虫在三天前就应该被传染上了。运算表明,在最初的十二个小时内,必须接触百分之八十的鼻涕虫。这部分鼻涕虫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
如果我们的判断正确的话,很快,鼻涕虫就会以比苍蝇快得多的速度死去。
我强迫自己坐定,思忖着那些红灯到底代表几百万只病入膏肓的鼻涕虫,还是仅仅代表两百只丧命的猴子。是不是有人漏算了一位数?还是泄露了秘密?难道我们的推理在在严重的失误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
突然,正中央的一盏灯闪烁着变成绿光。大家惊得坐了起来。尽管没出现画面,但在图板上方的立体声设备里传出了声音:“这里是小石城的迪克西电台,”一个疲惫的南方口音说道,“我们急需救援。听到通话的人,请将这一消息传下去: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处于可怕的流行病之中。通知红十字会,我们已经在……的控制之下——”声音渐渐消失,不知道是因为说话者过度虚弱还是信号传输出了问题。
我激动得差点儿忘了喘气。玛丽拍了拍我的手,我这才有意识地放松下来,向后靠着坐好。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就在这时,我发现那盏绿灯的位置并不在小石城,而是在更靠西的俄克拉荷马州。又有两盏灯变绿了,一盏在内布托斯加州,一盏在北边的加拿大。这时又传来一个声音,是带有鼻音的新英格兰口音。不知这人是我么进入红区的。
“有点像大选之夜,对吗,头儿?”马丁内斯热诚地说。
“有几分像,”总统表示认同,“不过通常不可能在墨西哥得到选票。”他指了指图板。一对绿灯显示这是在奇瓦瓦。
“的确,您说得对。我想等这事情完了以后,国家就该着手整治国际事务了,对吗?”
总统没有作答,他也只好闭嘴不谈了。这让我很宽慰。总统好像在暗自思索着什么,看到我在注意他,冲我一笑,大声道:
“‘据况跳蚤会生小跳蚤,
爬到背上咬跳蚤。
小跳蚤又生小跳蚤,
永无止境咬下去。’”
我觉得这首儿歌描绘的前景太黯淡了一点,但我还是礼貌地笑了笑。总统瞅了瞅其他人,问道:“有人想吃晚饭吗?这些天来头一回觉得饿了。”
到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图板上的绿灯数量超过了红灯。雷克斯顿又让人装了两台信号器,和新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相连,一台显示大规模空投准备完成的百分比,另一台则显示计划空投的时间。时间数字不停变化,起伏不定。但在过去的两小时里,数字一直稳稳地停在东部时间十七点四十三分左右。
最后,雷克斯顿起身向众人宣布:“我打算把时间锁定在十七点四十五分,,总统先生,我先走一步,可以吗?”
“当然,先生。”
雷克斯顿转身对我和爸爸说:“两位唐·吉诃德先生,如果想去的话,眼下正是时候。”
我站起来说:“玛丽,你留下等我。”
她问:“在哪儿等?”她不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过程一点儿也不平和。
总统插话说:“我建议尼文斯夫人留下来。她早就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他微笑着盛情挽留玛丽,我对此表示谢意。
两小时后,我们进入了目标区。跳伞舱门已经打开。我和爸爸排在最后,跟在真正干活的小伙子们身后。我的手汗涔涔的,身上一股大幕拉开之前担惊受怕的恐惧的臭味。我害怕极了——我从来不喜欢跳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