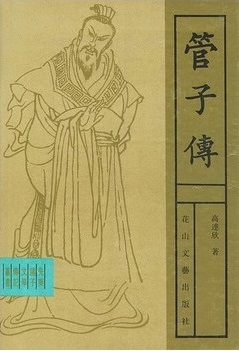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