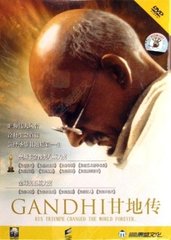若叶山的小谷城迎着融融春阳,如同鬼斧神工的翡翠一般,反射着夺目的光芒。
小谷城背依横山、金粪、伊吹三山,左靠虎姬山,右临湖水。从金粪山流出的一条玉带闪闪发光,掩映在绿叶之中的城郭,沐浴着太平的春色。小谷城依山而 建,本城就筑在山顶,次即二道城、京极苑、山王苑、赤尾苑,完美地利用了地形。这座坚固的城池,使浅井家的三代繁荣一脉相承,从祖父亮政、隐居的久政到现 在的城主长政,堪堪享受了太平。
本城的内庭里,市姬正在给长女茶茶姬叠纸鹤。市姬是信长最小的妹妹。她灵巧地动着手指,专心叠着纸鹤,秀美的脖颈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
从侧面看去,脸庞仿佛要溶化在阳光中。她长长的睫毛流露出寂寞。但那轮廓、眼睛、鼻子、脸和肤色,却完美无缺。她已是二子之母,且已怀上第三个孩子, 但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在一旁眼巴巴看着母亲叠纸鹤的茶茶姬,也如同清纯的偶人一般可爱、美丽。侍女不在房里。次女高姬在市姬的膝边爬着,不时发出咿呀 声,敲打着榻榻米。
“母亲,还没好吗?”
“马上就好。茶茶是个好孩子。乖,再等等。”
“茶茶是个好孩子。茶茶等。”
在貌美者层出不穷的织田家族,市姬是最出众者。她为了哥哥信长的霸业,才嫁到了浅井家。这个像极了母亲的茶茶姬,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市姬正想到此处,忽听院中传来说话声。
是丈夫浅井备前守长政。长政已经二十六岁。自从他父亲久政搬到二道城的山王苑隐居后,他就开始在本城观望天下诸势力的消长。当初和织田家联姻,也是一个策略,但现在,他已被市姬深深吸引了。
“对于你哥哥进京,你有什么看法?”
市姬有些意外,一时不能领会他话中的含义。她抬头看着丈夫,吃了一惊,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了困惑的影子。“哥哥怎么了?”
“唉,算了。”长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叹了口气,“茶茶还等着。你赶紧给她叠吧。”
说完,他径自走了。市姬不禁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丈夫的背影,又望望爱女。公公久政开口必称“义”。市姬知道公公的外貌看起来比丈夫温和,个性却比丈夫 激烈。提到自己的兄长,市姬实感难以判断。周围人有骂他为“大浑蛋”的,也有赞他为“平定天下之器”的,有人说他残酷无比,也有人认为他细心仁慈,甚至因 感动而流泪。信长对市姬百般疼爱,所以她十分尊重和思念信长。
同样,在嫁到德川家的德姬眼中,信长是值得尊重的父亲;嫁到武田胜赖家,后因产后虚弱而去世的养女雪姬(信长的妹婿远山堪太郎的长女)也对信长敬重有加。
“女人真是不幸,却又如此可爱。”抱着自己的妹妹和女儿时,信长真的流过泪。
关于哥哥特意在进京途中举行相扑比赛,随后又在京城赏花之事,市姬已有所耳闻。公公性情平和,言语缓慢,但听说信长长期滞留京城一事,却尖锐地提醒道:“不可掉以轻心。上总介心狠着呢。”
听说市姬的嫂嫂浓姬被信长从岐阜城叫往京城,久政丝毫不顾市姬的感受,警告道:“那些装着浓夫人日常用品的箱子实在可疑。恐怕里面装的,是用来攻打朝 仓的火枪。”这使得本准备绕道前来看望阿市的浓姬一行,最后终于没有进入小谷城。久政不屑地笑道:“前往京城的也许不是浓夫人,而是替身。”
兄长为何让公公如此疑心?市姬认为哥哥信长至少没有敌意,也不认为他有多么残酷,但久政对信长却极不信任。在久政看来,信长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他杀了亲弟弟信行,又将浓夫人的侄子斋藤义兴赶出岐阜城,然后自己大摇大摆住了进去。
“等着瞧吧,我们家也要……”
听到久政的话,市姬内心十分痛苦,长政好像也很伤心。“世间总有性情不合之人。我父亲和令兄大概就属此类。”
听到丈夫的安慰,市姬坚定地表示,万一发生这种悲剧,她一定要冒死劝谏。哥哥究竟在京城做什么?丈夫神色躲闪、欲言又止,让市姬无论如何放心不下。
“茶茶,来,叠好了。乖孩子,先在这里玩。”
市姬拍手叫过侍女,悄悄整理好衣裳,出了房间。艳阳高照。市姬猜测丈夫定在卧房陷入了沉思。她决定去问个究竟。
确如市姬所料,浅井长政正在可以望到虎姬山的小书院中,一边擦拭心爱的刀,一边沉思。
“大人,妾身可以进来吗?”
长政看了一眼市姬,没有回答,继续擦拭着手中的刀。
“哥哥在京城做了什么?”
“这……”
“妾身很担心。请您告诉我。”
长政放下刀。他看到跪伏在跟前的妻子不安的表情,内心不禁一阵疼痛。“我很清楚信长公的抱负。”
“您是指——”
“他要统一天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扫除一切障碍。阿市,这不是普通的野心,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相信只有他能平定乱世……但在外人眼中,这种鸿鹄之志过分狂妄了。”
市姬歪头看着丈夫,沉默不语。
“朝仓义景一直看不起令兄,认为他不过是旁支小卒,不知天高地厚。义景的背后,其实还有本愿寺、比睿山和将军等势力对信长的不满。义景君显然已经知道这些势力的不满,否则,他大概会立刻进京……”
“那么,我哥哥和朝仓必有一战了?”
“阿市,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惊慌。你是我长政的妻子、女儿的母亲。”
“是。”
“实际上,越前朝仓已经派老臣山崎长门守吉家作为密使,来到我们城里。”
“大人,阿市是您的妻子,请您说明自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泰然处之。”
长政点点头,又盯了她半晌,方道:“朝仓……”
“怎么了……”
“逼我毁掉和信长公订下的誓约。”
“那么……是要和哥哥作战?”
长政背过脸,点了点头:“密使自称三好余党,说准备联合甲斐的武田、本愿寺的僧侣和比睿山的武僧们,一起击败信长。否则,浅井和朝仓氏都会被信长踏 平。我借口要仔细考虑,让密使先去山王苑等候回音……”他忽然住了口。对毫不知情的妻子坦白这些事,过于残酷了。连长政自己都一片茫然,一个女子又怎能明 白呢?
正在此时,贴身侍从木村小四郎走了进来。“主公,使者希望您立刻去山王苑。”
“哦,你告诉他,我马上过去。”长政轻声回答,随即站起身,“阿市,你不必担心。我自有安排,你回孩子那里去吧。”他语气轻柔,眉宇间却愁云密布。
当长政来到父亲居住的山王苑,越前朝仓氏又派第二个使者前来拜访长政的父亲。父亲让两个使者在驿馆稍候,将儿子唤进房里:“长政,信长已攻进敦贺。”
“什么?”
“第二名使者飞马来报。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刻作决定。”年近花甲的久政表情比长政更加沉重。“我们和朝仓氏三代结盟。你究竟选择义,还是选择夫妻之情?”久政想试探儿子的心思,顿了顿又道,“必须明确答复对方。”
长政在父亲面前缓缓坐下,望着窗外的绿叶。“树叶绿了。”
“哦。很快就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了,却发生了战争。”
“父亲。”长政不再犹疑不决,脸上露出豪爽的笑容。“我想请教父亲,究竟支持哪一方,才符合我们家族以及天下的利益?”
“朝仓氏要求我们立刻出兵,截断信长的退路。他们说如果发生野战,那自当别论;如果在山间作战,他们绝对有信心打败信长……”
“父亲,甲斐的武田、本愿寺的僧侣和比睿山的武僧果真会如朝仓所料,奋起支持我们?”
“如果信长被杀,他们也就没有起来反抗的必要了。”
“为慎重起见,我才有此一问。信长死后,又有谁能平定天下?”
“这……”
“朝仓会臣服于武田,还是武田会向朝仓低头?”
“……”
“只怕好不容易建起的二条城和皇宫,又要毁于一旦。”
“长政,你是在劝我吧。你是想说,若支持朝仓家,我浅井氏将无立足之地。即使为天下苍生考虑,也不能支持朝仓,是吗?”
“父亲,正是如此。”
“我明白了。长政,既然家督之位已让与你,若我这归隐的老朽再多言,只能给家族带来混乱……但我有一事相求,是否允许我一人支持朝仓?浅井家迄今为止平安无事,正是因为背后有朝仓氏的支持。我不敢违背‘义’字。”久政伏倒在榻榻米上,老泪纵横。
按久政的想法,有越前的朝仓氏,才有北近江的浅井氏。浅井氏原本一直笼罩在佐佐木源氏的六角和京极两家的阴影之中,难以施展,全赖朝仓氏在背后支持。
“长政。”久政道,“我并非看不清时势走向,却愿为遵守义理而赴死。”
长政没有回答,他心中好像吹进了一股冷风。他并非不理解父亲的选择,只是在他看来,浅井对朝仓氏早已无须尽此义务了。朝仓氏虽然为浅井氏阻挡住六角、 京极两家势力,但浅井氏也制止了美浓斋藤道三父子对越前的渗透。岂止如此,浅井为了朝仓氏,甚至让长政的姐姐笃姬嫁给稻叶山的龙兴。龙兴被信长驱逐后,笃 姬只得回到小谷城,从此深居简出,过着愁苦的日子。浅井氏和朝仓氏的交往不过是各取所需,既然时势变了,此事也该重新考虑。
“长政,你难道不明白为父的心情呜?”
“儿子明白……”
“既明白,你还要阻止我?”
长政沉默了。家族中还有许多不喜欢信长的老臣,例如远藤喜右卫门、弓削六郎左卫门等。但长政认为,信长无论如何也不致败给朝仓义景,但那岂不是要将父亲送到信长刀下受死吗?
“父亲,你难道不能放弃这种想法吗?”
“使者说此事刻不容缓。按常理,决策拖延,胜仗也能变成败仗。”
暖暖的熏风轻轻抚摸着肌肤,长政突然生起莫名其妙的怒气。所谓的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当初他和市姬订下婚约时,朝仓义景不也无耻地加以干涉吗?
由于朝仓的阻碍,三年后他才好不容易和市姬成婚。一向以脾气暴躁著称的信长在那三年间毫不动怒,下决心要朝仓、浅井、织田三家结为同盟。
他当然是考虑到小谷城是从岐阜进京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想避免与浅井、朝仓两家为敌。倘若朝仓义景能够乖乖地进京,肯定不会发生这次战争。正是义景器量狭窄、不识时务,才导致战火又起。
“儿子明白了。我尊重您的意见。”阳光明媚,长政却备觉悲愁,声音有些漠然。
“啊,你同意了?”
“是。长政也是铁骨铮铮的武士,不愿意被人讥讽因儿女情长,将父亲送到别人的屠刀下。”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谁也不知哪一方会取胜。”
“当然……”
“长政,让我一人去即可。如果朝仓得胜,父亲会努力让你和市姬平安无事。你并未支持朝仓,若老天有眼,你仍会平安无事。你认为如何?”
“父亲!”长政满脸通红,“您平常总教导我们要忠于义理,这不像您说的话……真正的武士,应该超越生死胜败。胜也好,败也罢,决不退缩。与父亲共同出生入死,才是儿子应尽的义务。”
“哦?唉……我本以为你不会同意的。”
“父亲,无论此次战争结果如何,阿市都不应受到任何谴责。请您不要责怪她。”
“那是当然。她既然嫁过来了,就是我们浅井家的人。我的心胸怎会如此狭窄?我们马上将山崎长门叫来如何?”久政脸上堆满笑容,高兴地拍掌叫过侍童,“请朝仓家的使者到这里来。这次信长是自投罗网。”
久政十分讨厌信长,对这次战争有着必胜的信心。
山崎长门来了。他抬起苍白的脸,眼神紧张,仿佛想窥透父子二人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天气不错!”他干咳一声。久政探出身道:“长门,备州已决定和我一起突袭信长。”
“这……这……”刚过不惑之年的长门听到此话,顿时笑容满面,“如此,我们必赢。二位既已下了决心,我不妨实言相告。其实我家主公这次拒绝进京,完全是个策略,是和义昭将军商量之后才决定的。”
“将军……”长政惊讶地插嘴道。
长门微笑着点点头:“信长若性急,就会很快前去进攻越前。那时他就成瓮中之鳖了……哈哈,果然被言中。”
“将军一直……”
“不错。他不止一次写密信给我家主公,要求讨伐信长。”
“噢?”长政如同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目瞪口呆。这忘恩负义的、阴险的将军!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越前敦贺郡,叶原之北的木牙岭脚下。
从漫长的冬天苏醒过来的山脉绿意盎然,满山的翠绿中遍布着星星点点的枯叶色旗帜,迎风飘舞。二十日从近江坂本城出发的织田军,二十五日进入敦贺城,与家康的三河军汇合。织田大军气势如虹,越过木牙岭,就可直捣朝仓家的老巢一乘谷。
敦贺城前方是金崎城,朝仓义景的堂弟、号称天下无敌的朝仓景恒驻扎于此。他企图凭借手筒山和金崎城,阻住织田与德川盟军的去路,但一触即溃。
“他们善于野战,但若是在山间作战……”他原本这样想。但对方如遮天蔽日般压过来,连百姓都为其气势折服:“好威武的军队!”
朱红色的丈八长枪营,排成四列向前推进的火枪营,还有如下山猛虎一样的骑兵,如开放在北国荒野上的鲜花般耀眼。他们很快制服了守城的士兵。
“织田军的确非比寻常。”
“相比之下,朝仓简直不值一提。”
“天下大势已定吗?”
大军仅一天即攻占了金崎,第二日越过了手筒山,推至木牙岭。无论从一乘谷增派多少援军,已退到山顶的残兵败卒已无立锥之地。
织田的先锋是柴田胜家,紧跟其后的是明智光秀。德川军则在织田军的左侧,他们沿着海岸,步步紧逼,同样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看到先头部队柴田已经控制了通往木牙岭的道路,信长跳下武田信玄赠给他的骏马“利刀黑”脱下战服,命令全军造灶做饭,然后走到队伍中。
“叫光秀来。”信长一边擦拭额头的汗水,一边吩咐道,“迈过关卡,即是最后一战了。光秀熟悉这里的地理位置,把他叫来。”
森三左卫门的长子森长可心领神会地走开了,不一会儿,他带着光秀一起过来。光秀好像刚刚摘下头盔,稀疏的鬓角还热气腾腾的。他来到信长座前,单膝跪下。
“光秀,过关后,不得离开我半步。”
“您是说……”光秀依然一口重重的腔调,不解地望着信长。
“哈哈哈,你是否认为我有防范之心?”
“不不,不敢。”
“撒谎,你的眼神已经流露此意。不必担心,虽说你本是义景的家臣,我信长也决不会鸡肠小肚,对你起疑心。”
“主公恕罪,在下多虑了。”
“光秀,我明天要一举拿下一乘谷。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前来治理越前?”
光秀没有立刻作答。任命治理越前之人的确事关重大。信长究竟在想些什么,竟先找自己商量如此重要的事情?也难怪光秀疑心,当初他作出一番估量后,认为投靠信长毫无指望,因此直奔朝仓家。
他曾追随怪僧随风,并与之拜望过竹之内波太郎,央波太郎推荐他到信长处,但见到信长后,他却不习惯信长的粗暴之气,转而投向朝仓氏。
信长对教养和传统嗤之以鼻。这对以教养为荣的光秀来说,实在难以忍受。越前的朝仓义景乃是个风雅之士。他住在一乘谷,始终保持着优雅的生活格调。永禄 二年八月,朝仓义景甚至特意邀来京都众公卿,在阿波贺河原举行了曲水宴。大觉寺义俊、四过大纳言秀远、飞鸟井中纳言雅教等都列席了,义景在筵席上作诗一 首:
旧日花水流,
山中一叶秋。
不知何处在?
心中凉意愁。
这种风雅之举吸引了富有教养的光秀,终于使得他前去投奔。但一段时间后,光秀却颇为失望。义景虽懂风雅,却不果敢;虽有风骨,却不刚强。
就在此时,流亡中的足利义秋(后来的义昭)在细川藤孝的陪伴下前来拜访义景。倘若义景行事果断,就该趁机拥义秋进京,讨伐松永久秀,但有此实力的义景却未采取行动。
细川藤孝失望地带着义秋离去,光秀也绝望了。他方明白,风雅与果决不能并存。只有果决之人才能平定天下……他再三考虑后,和藤孝一起将义秋带至信长 处,并从此成了信长的家臣。信长对光秀甚是欢迎,立刻给他八万石俸禄,委以统军之职。光秀对信长感恩涕零的同时,又不无惭愧之意。
“你曾在越前待过,应该了解那里的民风。”
“是。在下以为先锋官、武艺超群的柴田公最为合适……”
话音未落,信长已哈哈大笑:“我不喜欢你这种回答,我不喜欢呀,光秀。”
“那么,主公以为——”
“为什么不说你自己?我心中早已有底了,但一乘谷难治理。你认为新城建在何处为宜?”
“在下……认为最好建在北庄(福井)。”
此时,帐外忽然喧哗起来。似有探马急报。信长和光秀不禁都侧耳倾听。马蹄声盖过了喧哗声,在帐外停下了。
“来者为谁?”只听侍卫问道。
“小谷城浅井备前守的使者。烦请通报信长公。”答话者声音粗犷。
信长心中叹息一声。听到使者自报家门,他有不祥之感,一股无名怒火从胸中直冲向头顶,仿佛蔚蓝色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照以前的脾气,他无疑会立刻大 声呵斥,甚至可能跳出去,二话不说,对使者一顿拳打脚踢。但现在,他却紧闭双唇,强压怒火。与其发火,不如思考对策——现在的身份使得他不能不注意分寸。
光秀神色凝重地盯着信长。忽然,信长纵声大笑起来。此时,森可成走了进来:“小谷城的浅井备州……”
“让他进来!”信长打断他,怒喝道,转过头看了看光秀,“停止进攻。将众将召集到这里来。还有,别让松永久秀跑了。”
松永久秀腹中韬略万千,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京城掀起波澜。所以信长这次出征特意带上他。
浅井长政的使者小野木土佐随森长可走了进来,和正要出去的光秀擦肩而过。土佐满头大汗,面如土色。阳光却灿烂明媚,如在嘲笑营营奔走的世人。
“小野木土佐,你不必说,我已知道了。把誓书拿出来吧。”信长用爱刀砰砰敲击着地面。
“请允许鄙人说完。”土佐驳道,“大人首先违背了浅井、朝仓和织田三家的誓约,进攻朝仓。我浅井氏一向忘利重义,决不与您同流合污。两家的交情也到此为止。现奉还誓书,从此兵戎相见。此是我家主公口信。”
“哈哈哈……”信长狂笑起来,“土佐,不要发抖,我不会杀你。回去告诉备州:井底之蛙安知鸿鹄之志?”
“这是誓书。”
“好,沙场上见吧!来人,给使者呈上热汤。”
土佐看了一眼信长,昂首挺胸走了出去,脸色依然灰暗。
信长站了起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前方马上就要遭遇越前的精锐部队,背后的浅井却突然截断了他的退路。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正如他一直暗自担心的那样。
“主公,何事?”光秀显然已将命令传达下去,木下秀吉率先跑了进来。
藤吉郎改名秀吉,是因为在攻打伊势北岛时,其敢于吃苦的勇气受到了信长的赞扬:“简直可以和朝比奈三郎义秀媲美。”于是将义秀的名字倒过来,成为秀义,又考虑到此“义”字与将军义昭的“义”相同,避讳起见,改义为“吉”。
“猴子!浅井这个浑蛋投靠了朝仓。”
听信长这么一说,连一向干练沉稳的秀吉也不禁叹道:“可惜!”
织田大军已攻进越前,并故意将敌人从一乘谷中引诱出来。若就此撤退,对方定会趁势追击,而退路又已被熟谙地形的浅井军主力切断。这不仅仅是浅井和朝仓两家在施暗手,将军义昭也藏在幕后,不知天高地厚地策划阴谋……但现在才明白,有些为时已晚。
“那么……主公有何打算?”
信长没有回答。他紧皱着眉头,怒眼圆睁,来回践踏着脚下的嫩草。
森三左卫门进来了。紧接着是丹羽长秀、佐佐成政,最前线的柴田胜家也穿着被血染红的战服走了进来,道:“主公,听说浅井那个浑蛋倒向了朝仓。”
信长还是没有回答。无论如何,进退必须十分谨慎……想到这里,怒火又熊熊燃烧。他将最宠爱的妹妹嫁给了长政,替他们击退了宿敌六角氏,而且发誓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保证浅井氏平安无事,一向性情急躁的信长还不厌其烦地劝说长政,但没想到他仍在节骨眼上反戈一击……
佐久间右卫门也气呼呼地走了进来。紧跟在他后边的,是右翼大将前田利家,他手中还提着血迹未干的马辔头:“主公!怎么办?”接下来是坂井右近和德川家康。看到家康,信长心中更是隐痛难当。
当明智光秀受命将松永久秀带过来后,信长终于抬头扫了众将一眼,道:“你们大概也听说了。值此关键时刻,却有人倒戈。”
众人一时陷入沉默,帐内一片死寂,甚至可以听见帐外溪流的声音。
“若我信长被区区朝仓击败,简直是奇耻大辱!如今只能顺应天意。众将听令:立刻进攻一乘谷,如果武运长久,则先击溃朝仓,随后回师讨伐浅井;如果武运衰败,则慨然赴死。”
“是!”胜家道,“踏平一乘谷!”
“正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就在众人纷纷表示赞同时,与信长相对而坐的家康猛地一挥军扇,起身道:“织田公,请慢。”
“滨松,有何异议?”信长逼问道。
家康缓缓点头道:“这不像是织田公的作风,目光太短浅了。”
众将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到家康身上,帐外又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众人忽而看看家康,忽而看看信长。因为照信长的禀性,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倾听别人意见的。他作出决定后,从未有人驳斥或表示反对。家康却不慌不忙,直接提出异议。
信长顿时弹了起来,“且说来听听。我如何目光短浅了?”
“嗯……”家康表情十分镇静,直视着信长,“浅井长政特意派人前来返还誓书之事,您如何看待?”
“那是只懂义之小者的无知之举。”
“若您这样认为,我不敢苟同。”
“滨松莫非认为长政这种行为背后,另有深意?”
家康注视着信长,轻轻摇了摇头:“我并无此意。即使他另有企图,我们也不能轻信。我只是想请您不要忘记他正直的本性……他分明是认为,若不归还誓书,内心则无法平静。”
信长哦了一声,神色渐渐缓和:“你不妨直言。我洗耳恭听。”
“信长公,您的敌人并非仅仅朝仓一家。如长期与之对峙,京城和岐阜城都将危在旦夕。不如佯装攻击,实则立刻撤兵。依家康看,浅井父子可能并未将退路堵死。”
“……”
“正直之将大都擅长持久战,更不用说他们已经返还誓书,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若您对此有后顾之忧,那就由我家康殿后,我军一边观察朝仓军的动向,一边向京都方向撤退。”
信长点点头,大声笑道:“众位,你们认为滨松的意见如何?”
“主公。”秀吉首先开口道,“正如滨松所言。在下也认为应立刻撤退。”
“胜家,你呢?”
“在下反对。如果我们将朝仓氏连根拔起,浅井军将不战而溃。如因惧怕朝仓辈而撤退,今后将无威严可言。”
“利家呢?”
“在下和木下的看法一致。”
“久间呢?”
“在下赞成柴田的见解。”
“哈哈哈……”信长笑道,“久秀有何看法?”
久秀朝信长笑道:“任凭大人裁定。”
家康转头看着信长:“请速作决断。浅井的使者已飞马回小谷城了。”
如此一说,信长才终于下定决心。不愧是家康,关键时刻总能稳如泰山。如立刻撤退,浅井父子也许刚刚引兵出城。
“好!我们改日再来,”信长吼道,“改日再来取他项上人头。这不算什么耻辱!我信长志在天下。”
“主公所言极是!”秀吉首先跪伏在地,“但不能让滨松大人一人担此重,给秀吉也分派军务。”
信长和家康对视了一眼。如此时无人主动请命,信长对家康将有愧于心。只有这只猴子,能够在最危急之时主动请缨。与其说他是有勇气,倒不如说是不断磨砺自身。真是世事洞明之人!
“能否漂亮完成任务?”
“请相信我秀吉的智谋。”
“你这猴子,倒不谦虚。那好,滨松,我们京城相见吧。”
众将长舒一口气,跟在信长身后。他们十分清楚腹背受敌后,继续滞留此地的危险处境。织田军远道而来,不熟悉地形,撤退必十分艰难,必须主动寻求活路……但既然有家康和秀吉殿后,情况又不一样了。
信长回到金崎城,安排好撤退事宜,身边只留森三左卫门和松永弹正,准备越过朽木谷。众将陆续出帐去了,只剩木下秀吉和家康二人,秀吉走到双手紧握的家康面前,单手拄地道:“滨松大人,您今天的话,秀吉铭记在心。”
“我不过为了提醒织田公。”
“啊呀,若是没有巨大的勇气,如何说得出那番话?这样一来,主公就获救了。”秀吉说到这里,脸上浮出笑容,又道:“也请您先撤退吧!”
家康不禁惊讶地重新打量了一眼秀吉。连信长都感觉困难重重的撤退,眼前这小个男子竟能独自殿后?
“木下,你应已听到我对织田公许下的诺言。你且看我家康是如何击退朝仓军的追击。”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秀吉微笑着低头致谢,“鄙人已铭记在心,却不能不拒绝。请您赶紧撤退吧!”
家康不禁再次打量起眼前的秀吉来。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的笑容世所罕见,仿佛俏皮的顽童,身材矮小,骨骼纤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个男子,居然对信长说他是智谋之源……
“木下,你的意思是,我们继续留在此处只会妨碍你?”
“不敢不敢!”秀吉笑道,“只是朝仓那帮浑蛋在追击时,若惊扰了滨松大人,秀吉可能会受到主公的斥责。”
“哦?”家康的眼神好似要窥透对方,“你是想说织田氏中自有可用之才?”
“不敢不敢!”秀吉又笑了,笑声甚是清脆,“您这么年轻,又如此重义气如此勇猛无畏,您与我家主公一样重要,万一发生意外,将是天下之痛。因此请把这里交给我,请您快些撤退吧!”
“你的褒扬令我羞愧难当。但你这样一说,我更不能率先撤退……”
“请您不要犹豫,快些撤退吧!”
“如你稍有闪失,恐怕会独力难支。你能保证万无一失?”
“哈哈,”秀吉爽朗地大笑起来,“这次战斗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在下是为了您的安全,才请您先撤退的。”
“哦,这话倒有些意思。”
“滨松大人,在下不过一介足轻武士之后。”
“我听说过你的家世。”
“正因为是足轻武士之后,才对生命并不那么看重。无论什么样的战斗,都要抱着必死之心去作战,即使战死了,也毫无怨言。但您出身名门,不能像我这样随 随便便行动。”秀吉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语调。无论开始时语气多么殷勤、恭敬,最后总会变成一流的说教。家康沉默地盯着秀吉的嘴唇。
“我现今虽算略居人前,但也不过领有近江今滨地区的三万石领地,下属不过七百人。凭此微薄之力去对抗足足有八十万石供给的越前大军,即使粉身碎骨,也 决不后悔。在下出身低微,能够拥有三万石领地,已经十分知足了。但滨松大人却正相反。您已经拥有三河、远江,其势如旭日东升,领地迅速扩张。现在的俸禄虽 然只有六十万石,但明天之势,谁可逆料?如让您去打这场领有三万石之人就足以应付的战争,万一发生不测,不但我家主公会被世人笑话,就是在下,到了阴间也 会受到谴责。所以,请您无论如何听我一言。”
家康似听非听,依然紧紧注视着秀吉那不可思议的嘴唇。
“好,那就依你,家康先撤退了。我走若狭的小滨,越过针田,出鞍马。若是顺利通过,你就可以放心撤退。”
“鄙人万分感激。那么我们京都再会。”
家康站起身,秀吉也快步跟了过去,一边轻松地弹去战服上的灰尘。
往常,战斗中的信长凶神恶煞、斗志昂扬,但撤退时,他却开起玩笑来。“世间有‘京城沦陷’一说,我信长大概是第一次尝到了‘金崎城沦陷’的滋味。久秀,你大概后悔此时不待在大和城吧?”
因为让柴田、佐久间、丹羽和前田分别带领军队撤退,信长手下还不到三百骑兵。越过朽木谷后,他们将从江州高岛郡向京都方向进发。信长一路上谈笑风生。看到树上的嫩叶,他会忽然会心微笑,偶尔还会眯缝起眼睛欣赏山色,不时话带讽刺,却也语气柔和,不似战斗时那般叫嚣。
“信长公是怀疑我松永弹正的品性。”
“哪里哪里。你的智谋海内无双,所以我才不让你离我左右。”
和信长并辔而行的松永久秀任凭狂风吹乱了斑白的鬓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正是他智勇双全,除掉了将军义辉,又平息了三好三人众的叛乱,想要称霸京 城。他根本没想到会被信长打败,受其控制。正如信长所言,如果久秀此时留在京城,无疑会不失时机分兵给浅井氏,以袭击岐阜城,他自己则可以从大和城向和 泉、摄津一带推进,从而消灭信长在京都的势力。
久秀和信长,都失算了。但令久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性格倔强、急躁的信长既然如此了解他的心思,为何迟迟不杀掉他呢?
“织田公,既然久秀如此不值得信任,不如索性取了我项上人头吧。”
“哈哈哈……像你这种人,即使没有了头,仍然是要算计的。”
“哦?”
“有时,毒草能治病。你就是这种毒草,因而我要让你活着。听好了,久秀,若我什么时候掉以轻心,你随时可以取我性命。”
“大人真会开玩笑。这么一说,久秀更无颜立足了。”
“你还谈何颜面?入水,你是深渊里的河童;在山,你是只狡猾的老狐狸……”正说着,信长突然大声叫着“三左”,将与他隔了两三骑的森三左卫门叫到身 边。人马已经进入近江山中,正向朽木谷逼近。岩石点缀在茂密的树丛中,可以看到狭窄的山路尽头,朽木信浓守元纲的官邸。“你先前去,让朽木元纲为我安排住 宿。”
“是。”森三左卫门领着十六个贴身侍卫,纵马而去,踏上荆棘丛生的狭窄山路。
昨晚,亦即二十七日夜,信长在佐柿城受到了粟屋越中守的热情款待。他似乎认为在这里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森三左卫门的身影消失后,松永久秀竟在马背上呵呵地笑起来。
“久秀,笑什么?”信长问道。
久秀立刻恢复严肃的表情,转头道:“深渊的河童、山中的狐狸?可是照我这老狐狸的看法,朽木元纲不会轻易让我们过了这朽木谷。”
“你是说元纲也要背叛我?”
“正是。元纲虽是佐佐木、浅井氏的敌人,对您却尤为不满。如果他和浅井家勾结,在此对付您,那么……”
“停!”没等久秀说完,信长就挥手让队伍停止前进。久秀所说不无道理。信长让秀吉殿后,撤出敦贺城后,一直在思索应于何处,以及如何才能击败浅井、朝仓的联军,根本无暇去琢磨朽木元纲的心思。
“久秀!”信长又恢复了战斗时的声音和雄姿。他目光如炬,紧紧盯住久秀,头脑中已经在盘算接下来的战役部署了。“你现在明白我带你在身边的用意了吧?”
“您是说……”
“三左回来后,就轮到你这只老狐狸出动了。”
久秀笑道:“在下明白。”
“你知道?”
“是。既然进是死,退亦死,我早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闻名大和城的老狐狸,怎会被朽木谷的小狐狸打垮?”
“真是无毒不丈夫啊,哈哈哈!”
夕阳西下,晚霞灿然,两侧的悬崖直指苍穹,他们要在这里和敌人一起迎接天明了。
“织田公,”久秀皱起眉头,正色道,“我会用尽方法让元纲前来归顺。若他同意,我会带他的人质前来迎接您。倘若我没回来,定是与朽木同归于尽了。那时,您再另谋他路吧。”
信长轻轻点了点头:“久秀,不必担心。你若认为我信长竟然无能到会被朽木这种鼠辈算计,那你可以和朽木联起手来取我性命。”
松永弹正微微笑了。信长对他无半点信任。即便如此,久秀仍然下定决心要前去劝说朽木归顺。
不久,就看见森三左卫门从暮色苍茫的山间小路上气喘吁吁纵马回来。“主公,元纲披挂整齐,好像在暗中调兵,不肯给我们开门。”
“知道了,知道了。”信长面向群山狂笑起来,“不必担心。这里有只更精明的老狐狸。”
松永久秀面带笑容地看着森三左卫门从马背上跳下:“稍后你们就可见识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了。”
“哦,你的口气还真不小。”信长猛地调转马头,指着朽木官邸的方向,怒喝道:“前进!”
久秀收起笑容,对三名侍从道:“跟我来!”其势仿佛要与朽木决斗一般。
看到久秀远去的背影,信长又高声笑了。万一久秀失败……这种担心对于信长来说是多余的,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他不相信自己这样的人物会在这里丢掉性命。
前往朽木府邸的松永久秀也是同样的心情。连义辉将军和三好乱党都能对付,怎会说服不了朽木这个鼠辈,而让信长取他的性命?
但信长还是有点害怕,并非基于理性,而是来自闪电般的直觉。这种直觉往往能让他看透世事的真相。如果自己身上有致命的弱点,那就任由久秀和朽木前来取自己的人头,这种话虽然充满了必胜的自信,但又刺耳可恨。
等着瞧吧,我久秀要现出你信长所无之能!久秀策马扬鞭,迅速来到朽木府邸门前。
“什么人?”三个全副武装的家丁,挺起长枪,挡住了久秀。
久秀眯缝起眼打量着周围:“辛苦了。”
他缓缓抬头望着门前的那颗大榉树,“哦,这棵树的年龄不小了,大概有六七百年了吧。”
挺枪而立的家丁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怔怔地站着:“您从哪里来?”
“哦,我?告诉朽木元纲,多谢他重兵把守。我松永弹正久秀从织田阵中前来拜望,快去通报!”
“什么?”家丁们简直难以置信,但被久秀的气势镇住,纳闷地进去禀报了。
久秀也不下马,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暮色。门内处处挂起灯笼,点燃火把,好像要防止信长夜间来袭。颧骨凸出、胡须飘飘的朽木元纲大步流星出得门来。
“朽木元纲吗?”
“正是。听说松永弹正前来。”
“今天真乃佳日。信长公和浅井长政,对你的好意都心领了。信长公既然来到此处,你还是派令郎前去迎接为宜。”
“哼!”朽术元纲果然大怒。他听说信长和浅井长政已经分道扬镳,才与长政联手对付信长。松永久秀的话太不入耳。但浅井长政和信长对他朽木的好意心领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朽木。”久秀表情严厉,在随从的搀扶下慢慢下了马,“你难道认为没有必要迎接信长公吗?”他拍打着护腿甲,面带笑容走向元纲,“这就要怪贵方考虑不 周了。朽木氏本是近江源氏佐佐木氏的分支,这次浅井长政和信长公联手欲过朽木谷,贵方既然全副武装,保护他们路上的安全,为何不尽表忠心呢?”
“你是说这次翻越朽木谷的行动是织田、浅井两家商议的结果?”
“嘘——这是秘密,不得随便道出。京城的将军有异动,因此要立刻回京。有密使从浅井过来……”
朽木元纲的表情顿时变得复杂。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事情正好相反。本来是讨伐对象的信长,却前来感谢自己保护他——朽木懵了。
久秀哈哈笑了:“老朽总是喜欢多嘴。其实信长公不过是让我前来致谢,请你多多关照,仅此而已……至于出迎之事,还是请你自己定夺吧。”
元纲焦躁地打量着四周,慌慌张张地吩咐:“来人,快取坐垫来。”
“不,时间不早了,我还得先回去。”
“请稍候。”
“你准备听老朽的建议,派令郎前去迎接了吗?啊呀,我可能是小肚鸡肠,他们虽然提出要借宿,但想到朽木过去毕竟是佐佐木一族……那就不太合宜了。”
老狐狸果然狡猾。首先扰乱对方的思维,然后不断暗示,直到对方信以为真。这时,下人搬来了椅子。
“生火。”元纲吩咐道,“要照亮山路,让信长公看清楚这里……”
元纲一边说一边歪头考虑了一会儿,又道:“还是出迎为好。请您稍候。”
“哈哈哈……如果要派人去,老夫便安心等候。应该是令郎吧?”
“正是。我会令长子和次子前去迎接。”
“太好了。无论如何,将来的天下非信长公莫属。你的好意信长公定然铭刻在心。美酒和洗澡水就不必了,准备些开水就好。”
“不不……我会一并准备齐全。”
“太周到了。久秀再次表示谢意。我们明日就进京。京城里的布谷鸟已经开始鸣叫了吧。”
“应该如此,应该如此……”
元纲一边应着,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忙着吩咐手下准备出迎。久秀不做声,只轻轻地抚摸着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