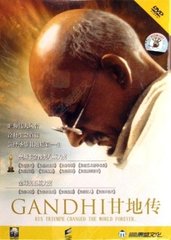信康的身影消失了,减敬依然跪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信康和胜赖的身影。在减敬心中,胜赖是个值得依赖的主子,信康则是个可怕的敌人。 从年龄上看,信康不过是个孩子。他曾问自己,为什么那样怕信康,却发现理由十分模糊。信康那犀利的眼神,让人想到展翅飞翔的鹰。
它在空中傲然盘旋,一旦地面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降落下来,不由分说地将猎物撕碎。好不容易等到了胜赖的亲笔信,他觉得应该立刻离开冈崎城,固然有遗 憾,但若继续留在城中,就有可能被鹰的利爪撕碎。再也不能轻举妄动了,必须装出害怕信康的样子,让城内的人以为他只是个胆小的郎中。
“减敬先生,你怎么了?”阿琴终于发现了蜷缩在房间里的减敬。
“这……我坏了少主的心情……”
减敬故意心惊胆战地想要站起来,却又缩下了,“阿琴,请……请向夫人求情,求她替我向少主道歉。拜托了。”
“你怎么了,减敬先生?”
“我的腰扭了,只能爬着过去。少主……少主大概还在生气,我很害怕……”
阿琴看了看周围,悄悄扶起了他。减敬指着夫人的卧房,又颤抖起来。
阿琴依言将他扶到筑山夫人房中,减敬立刻示意筑山夫人屏退其他人。其实无须减敬示意,他一走进卧房,下人立刻习惯性地离开了。
半刻之后,减敬从房中走了出来,脸色苍白地离开了御殿。该做的都已做了。信康既已视减敬为敌人,为了信康能与胜赖联手,减敬对筑山夫人说,离开冈崎恐是唯一一途。令减敬吃惊的是,他说完后,筑山夫人居然非常顺从——她的心已经飞到了甲斐。
菖蒲被信康的真意感动,将一切都坦白了。同样,减敬若如实诉说自己的一片苦境,想必胜赖也不会阻止他回去。但他还是装作战战兢兢的样子,仿佛荒原上的野草般摇摇晃晃向城门走去。
在冈崎做探子,每一天都处于生死线上。减敬感到全身如同虚脱,但现在不容如此。他走出筑山御殿的大门,暗暗提了一口气。日色偏西,凉风习习。还有一刻就要入夜。减敬一边想象着今夜的星星该有多么美丽,一边告诫自己,天黑之前这一刻万不可疏忽大意。
出了大门,减敬立刻转身向本城走去。倘若信康的人想要杀他,也绝不会在本城,而应该在护城河边,或者住处的入口等处。因此,减敬认为走之前还应再见一 次大贺弥四郎。弥四郎的住处现在城内,减敬觉得一生最危险的时刻,应该在弥四郎家里度过,那里是最安全的。“这弥四郎,白捡了堆好果子。”
谁都不可能识到此话中的意味。减敬大步走进大贺弥四郎的宅门。
弥四郎刚刚往吉田城搬运完粮草,回到家中。“减敬?来得正好。进来进来。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吧?”
“您最近公务繁忙,不敢前来打扰。”
“哦?我们今日畅谈无妨。我公事已毕,正好要歇息歇息。你今日就在敝处用饭,我吩咐下人去做。”弥四郎说完,屏退了下人。
“家康终于要开始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了。”弥四郎压低声音,笑道。
“大贺大人。”减敬眼神凌厉,“我想于今夜离开冈崎。”
“噢,为何?”
“我被信康识破了。”
“哪一事?你的风流韵事,还是……”弥四郎表情扭曲地笑了,“你太沉迷于与夫人的情事。”
减敬故意轻轻咂了咂舌:“关键时刻到了。密函已送到夫人处。”
“已送到了?”
“主公完全接受了夫人的条件。您也将成为一城之主。在此之前,切不要有任何差错。”
减敬逼近了一步,弥四郎如释重负般拍了拍胸脯。
“我眼前仿佛再现了一个家族衰败的古老故事。”大贺弥四郎一边轻轻摇着扇子,一边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夫妻不和,导致后庭之乱……这是德川家破灭的征兆。你说呢,减敬?”
“您的结论为时尚早,大贺大人。”
“不,在命运面前,人无能为力……我终于明白了。坦率说,主公来冈崎城监督城池修缮时,我大大吃了一惊。我担心我们的事……也许主公意识到了命运正佑护我们。”
减敬对此不置可否,他平静地坐着。
“吉田、滨松二城,本就不是主公的。我以为他回到冈崎是要巩固自己的霸业,若是那样,我们可就完了。但他修完城池,突然决定远征骏府,如果不是他被天魔迷惑,又能作何解释?”
“是。”
“骏府本来就不成问题。主公也说要立刻从骏府撤回,他还说之后进攻山家三方众的战斗将直接决定德川家的命运。减敬,你回甲斐后,立刻向胜赖公禀报此事。这是一份很好的礼物。”
“只有这一份礼物?”
“还有,你且听我说。”弥四郎白皙的脸颊轻轻扭了扭,那是他自信十足的表现,“在进攻山家三方众时,他会率先进攻长筱城,必须让他在那里陷入长期的拉锯战。这样必然带来粮草上的不足,到那时,他就会向我要粮草,我则会告知胜赖公。”
“哦。”
减敬使劲点点头,用眼神表示心领神会。世间之事真是无奇不有,他不得不佩服弥四郎的心机。
“胜赖公一直在等待那一刻,然后就可亲自发兵冈崎。我不是说他要攻打冈崎城,但我觉得他可能中途需要你引路。”
“言之有理。”
“到夜间,他来到城门前,就说是主公从长筱返回了……你届时大声呼喊,让城内的人听见。胜赖公就可大摇大摆进得冈崎城,不损一兵一卒。”
减敬将视线转向灯火通明的庭院。暮色浓重,马厩上空可以看到星星的光彩。现在出城还为时尚早,减敬又向前挪了挪。“您认为信康会听我们的吗?他那种个性,即使我们进了城,他也要和我们决一死战。”
“还有一件礼物。”
“噢,洗耳恭听。”
“我会向主公建议,一定要让少主初征。他年纪轻轻,必然一口应允……他不在城内,一切不就结了?”弥四郎说完,眯起了眼睛。
弥四郎的妻女和下人们端来饭食时,减敬又装作郎中的样子,给弥四郎按摩颈部。
该做的都已做了,减敬已经明白了家康今后的动向,弥四郎的计策简直让他拍案叫绝。而对家康而言,冈崎既是根本之地,又是粮草的来源。让信康出征,武田家就可以不动一刀一枪得到冈崎城,还可以顺便将信康扣作人质。那样一来,桀骜不驯的家康,也只能在武田面前俯首称臣。
“好热的天,来,再喝一杯。”弥四郎道。
仍像弥四郎做足轻武士时一样,他的妻女亲自给减敬斟酒。
“不敢当。夫人斟酒简直是对我的惩罚。”减敬摆手拒绝了。但他却吃了四碗米饭。他隐隐感到弥四郎家里并不安稳。还是迅速离开为上策,他不由想起了夜色 下漫长的山路。他要尽可能不被人当作甲斐的探子,而认作一个小心翼翼的郎中。惹怒了信康,便如露如气……某一天,当他突然重回冈崎时,人们会发现他已是一 员威风凛凛的武将。
“感谢您的好意,我待得太久了。就此告辞。”减敬恭敬地说道。
一直在享受着美酒的弥四郎忽然抬眼道:“那么,我们届时再见。”他站起来,特意从抽屉中取出些盘缠交给了减敬。
室内的烛光照亮了夜色,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蛙声。弥四郎妻女送减敬离开了。出了弥四郎的宅子,减敬故意装出醉醺醺的样子,摇摇晃晃前往城门。
“我是郎中减敬,刚从大贺大人府里出来,请打开城门。”
他出了城门,朝着和自家相反的方向,疾风般飞跑起来。跑了几里路程,确认身后没有追兵,他终于放下心来时,忽然传来了吆喝:“站住!”松树后面的阴影中突然闪出一个男人。
“这……您有什么事?”
“你是郎中减敬吧?”
“是……是。”
“甲斐的奸细,野中五郎重政奉少主之命,前来取你性命。”
减敬吓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拔腿如燕子般向原路跑去。
“站住,你这个懦夫。”重政立刻追了上去。
野中五郎重政并不知减敬是熟知冈崎所有秘密的奸细。他更不可能想到,家康欣赏的大贺弥四郎竟是减敬的同谋。
“站住!减敬,哪里跑?”重政越追越近,减敬大声喊叫:“请放过我……拜托了!拜托……救命呀!”减敬故意挥舞着双手,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救命啊……野中杀人啦。”
既然已被信康识破,即使被杀了,也要在路人心中留下一点疑惑。
“浑蛋,哼!”看到减敬如此胡闹,重政几乎要放弃了。杀了这个郎中,又有什么用?这厮大概再也不敢在冈崎城出现了,只要告诉信康已经杀了他,不就可以了?正想到此处,减敬突然向右拐去,消失在路旁的松树林里。再向前跑,就进城了。
“救……救……救命!”减敬不知重政还会不会追上来,又发出了哀鸣。
重政一听到那声音,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怒气,“浑蛋!”重政将手中的刀掷向他。
“啊!”刀正好砍中减敬腿部,留下了三四处伤,他摇摇晃晃跑了几步,和刀一起向前栽去。
不知何时,月亮出来了。前面的山坡露出了红土,左侧的丘陵上仿佛有一丛野玫瑰,闪着白光。
“唉!”减敬倒下去,不禁咬牙切齿,暗恨自己不中用。究竟是三河武士的本领厉害,还是甲斐武士的心机厉害,早已一目了然。
重政慢慢走了上来。他在离减敬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捡起地上的刀。“减敬!”
“是……是……是。”减敬望着月亮,故意全身颤抖。他不可能用武力战胜重政。他发誓至死也要掩饰真实身份和目的,这是一场激烈的意志的斗争。减敬希望 自己的意志能够战胜重政的武力。“大人!野中大人,你且……饶……饶命,啊,血!”仔细看去,减敬膝盖周围的土地已经被鲜血染黑了一大片。
“小人……小人减敬,是小人治好了筑山夫人的病……不想冈崎恩将仇报……这么残忍……这么残忍的报复……野中大人……”
野中重政默默地站在减敬身边,半晌无语。他的心中既有怜悯,又有憎恨,是放他一条生路,还是杀了他……就算不杀他,身负多处刀伤的减敬还能逃脱吗?信康说减敬是甲斐的奸细,但野中重政却看不出。但如就此放了减敬,让他在附近农家养伤,重政就是在欺骗少主。“减敬……”
“是……是。请饶……饶命,野中大人。”
“我没说要饶你。你为何会惹得少主如此生气?”
“那……那真是没办法。小人收养的那个女子菖蒲,说成是我自己的女儿,少主认为我欺骗了他……”
“是甲斐人吗?”
“不,小人祖父是从大明过来的,小人……我出生在堺市。只不过在甲斐住过……甲斐的人对我很是冷淡残酷。所以,小人准备将菖蒲带回堺市,不想在冈崎停留,才酿成了今日的不幸。”
说完,减敬在月光下呜呜哭泣起来。他几乎绝望了。大腿失血过多,他不时有晕眩之感。
野中五郎重政在信康身边是仅次于平岩七之助亲吉的人。减敬垂死的样子被他看在眼里。为了减轻减敬的痛苦,重政也许会举起手中的刀。减敬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最后的搏斗。
“哦,原来是在前往堺市的途中,停留于冈崎……”
“后来,筑山夫人患病,吩咐我为她治疗,没想到会酿成今天的结局。女儿被夺走……我自己也……野中大人,你如果可怜小人,就饶了小人……小人已经没有力气了。”
野中重政还是默默地站着:“减敬,你不是郎中吗?”
“小人是郎中。”
“既然是郎中,就知道你还有救没救了。还是闭眼等死吧。”
“不!不!那……大人,大人!”
“不要动。你一动,只能徒增痛苦。”重政一边说,一边提起刀。
“啊……啊……杀人了!”减敬用尽最后的力气在土丘上爬着。不可思议的是,现在支撑着他的不是为主子胜赖献身的意识,而是不愿输给眼前这个人的好胜心。
看到减敬痛苦的样子,重政想赶紧取他的性命,“减敬,不要动。我不会让你再痛苦。”
“杀人了,啊……无情的畜生!救命!”
“不要动。如果我砍偏了,痛苦的只能是你,懂吗?”
“啊……畜生!不……野中大人,我有东西交给你。这是我减敬拼着性命赚得的……”减敬颤抖着将手伸进口袋,掏出钱袋来。钱币叮当散落在地上。
“这……这个给你……只能给你这些,野中大人!饶命。这样……这样的话……”
野中重政背过脸,举起了手中的刀。
“啊——”减敬知道那刀冲着自己的脖子而来,不禁蜷缩成一团——刀正中头部。
这一瞬间,减敬感觉自己似是赢了。像这样悲惨死去的人,难道不是甲斐武士的佼佼者吗?像这样有器量的人,在三河找得出吗?血如泉水般涌了出来。他发出 一声悲鸣,双手紧紧抓住刀。“啊……啊……杀人!畜生!啊……恶魔!爷爷到地府,你一定会有报应的。啊……啊……”减敬紧紧地抓住刀刃,视线渐渐模糊起 来,面目狰狞。
重政猛地抽出了刀,减敬的身体突然向前扑倒。
“嘿!”重政又是一刀。减敬的头颅顿时飞了出去,落在四五尺远的土丘上,仍然圆睁着双眼,盯着虚空,嘴唇仿佛在嘲弄什么,向上翻着。白牙反射着淡淡的月光。鲜血喷涌而出。重政走到头颅边上,没有双手合十,而是狠狠踢了一脚。
重政缓缓地擦着刀,周围又恢复了平静,只听得蛙声一片。他插刀入鞘,从腰间掏出布条,抓住减敬发丝零乱的头颅,高举起来。“真是一副奇妙的表情,减 敬。像在生气,又像在微笑。来生一定要变得大胆些。”面无表情地说完,重政用布条缠住头颅,挂在腰间。信康大概在焦急地等待他回去。他没再看一眼死尸和钱 币,双手抱胸,大踏步走了。
重政正要跨进城门,忽听身后有一匹马呼啸而来。“我是能见松平次郎右卫门重吉,开门!”
下人一边踉踉跄跄跑过去牵过马缰,一边吆喝起来:“能见松平……”
野中五郎重政跑了过去:“我是野中重政。发生何事了……”
松平重吉跳下马背:“哦,原来是你。少主还好吗?”
“很好。”重政边说边将腰间的头颅藏了起来。
“哦,太好了。滨松来了使者,少主要初征了。平岩亲吉怎样?”
“他仍然一心侍主。”
“太好了。亲吉必须立刻去滨松,本多作左来代替他。”
“会发生大战吗?”
“嗯。让亲吉率兵进攻二俣城,你召集起年轻武士,我来统率他们……主公是如此吩咐的,才匆匆赶来……”重吉顿了顿,又道:“大战就要来临。五郎,你要多召集些年轻武士。”
正说着,月光下的城门吱呀吱呀打开了。
“我马上去向少主察报。”
“拜托。”
重政目送着重吉远去,立刻向信康的内庭走去。
信康正在菖蒲房中,他还没有杀小侍从。为了母亲的声誉,必须杀掉她!他虽然已下了决心,却轻易找不到杀人的借口。
信康来后,小侍从忍着刀伤之苦,挣扎着下床来给信康请安。“给少主添麻烦了,少主亲自前来,奴婢担当不起。请少主不要担心。”
听到这话,信康觉得自己真的遇到了与母亲、德姬、菖蒲截然不同的烈女子,他内心反而不安起来。世间竟有这种女子,如果这个女子不知道母亲的秘密,真应该放在身边爱护有加,他不禁困惑起来。正在此时,野中重政回来了。
“如何?”他问道,忽然看到重政腰间减敬的头颅,“跟我来。”
他起身离开菖蒲的房间,他不想让菖蒲看到。
“少主,请到院里来。”
“哦。”
“减敬的首级马上就要成为少主初征的祭品……”
“什么,初征……”
“能见的松平重吉已经带来命令,他入城了。”说完,重政方才思量将减敬的首级葬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