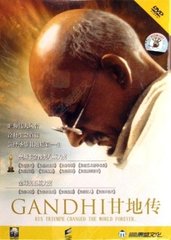强右卫门前脚刚一走,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的联军就从冈崎出发了。十八日中午,队伍经过牛久保,抵达设乐原,立刻安营扎寨。信长驻扎在极乐寺山,家康安营于茶磨山。然后,两军决定进行一次最后的议事。
夕阳西下,家康带领神原小平太康政和鸟居彦右卫门元忠出了营帐,朝极乐寺山信长的大营赶去。此处距离长筱城约八里。
三人催马赶到弹正山的时候,看到脚下的连子川和对面郁郁葱葱的森林,家康似乎听到长筱城那些饥渴难耐之声又从远处传来。他手搭凉棚向东望了望。
“主公,要迟了。信长大人恐已等不及了。”鸟居元忠催促家康道。而家康却一动不动,他似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通向长筱,便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
“主公,平时懒得挪地方的信长公,居然也会来到这种地方。”
“知道了。”
“既然知道了,再让人等着,恐怕不好。赶紧去吧。”
“元忠,你知道信长为什么不愿挪地方吗?”
家康的视线从群山转向密林,“织田大人这次是从心底里想帮我一把,因此,他才按兵不动。”
元忠听了,眉头紧锁,思量着,多么会替人打圆场啊。正是考虑到是他人的战争,才按兵不动,这就是信长。这一点就连德川氏的小卒都十分清楚。
“信长公心里正怕着呢——他怕武田胜赖得知咱们赶到,一下子从长筱撤走,溜回甲斐,避免和咱们决战。”
“他不会那么傻!”元忠反驳道,“果真那样,真是意外的好运。您还记得他在冈崎住了好几晚的事吗?”
家康终于回头看了元忠一眼,此子居然想到这一步?
“一定不会有错。因此,他才急急忙忙地赶来,无论如何也要开一次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决战。”
家康的脸上浮起微笑,没有对元忠再说下去,催马扬鞭,直奔极乐寺而去。
已故的信玄有一种叫“隐游术”的游击战术。那就是冷静计算敌我双方兵力的差距,一旦发现没有胜算,就撤回兵马,让对方空等一场。信长正是清楚这一点,才故意拖拖拉拉。虽然家康这样判断,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主公,今天对待信长公的态度一定要强硬一些。”后面的元忠又强调了一句。
正如元忠所料,信长的大帐里,众将早已坐好,正等着家康的到来。以织田的两个儿子信忠、信雄为首,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泷川一 益,还有前田利家等众将凑到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商讨战术。在刚刚支上帐篷的草地上,只有信长一人坐在床几上。看到家康过来,身后却看不见信康的影子,信长 奇怪地问道:“三郎呢?”
“正在松尾山安营扎寨,回头把决定告诉他就行了。”
“德川大人,请坐。”信长指了指身旁的座位。
“信长公,我看甲州那边必定前来决战。”家康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鸟居元忠和神原康政,微笑道。
“那么,我军必胜无疑。”
“的确如此。”信长高兴地点点头:“为防万一,我还有话要对德川大人讲。”
“愿闻其详。”
“也没有别的。只是胜赖是德川的宿敌,你一定想一战决胜负,然后在此站稳脚跟。如果真想如此,恐怕考虑不周。无论是你还是三郎,深入敌军时,万一有个闪失,就是胜了也不合算。一旦变成那种局势,对于我信长来讲,从岐阜发兵助你一臂之力,恐也就失去意义了。”
家康默默地点点头。信长的一番话也使鸟居元忠非常吃惊。信长好像已经看出了家康心中的不安。他用“发兵助你一臂之力”这几个微妙的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 的立场。“不管发生什么,这一仗你只管稳坐钓鱼台,所有事都交给我信长好了。对方若果然挑起决战,并取胜了,你也全当是游山玩水,只管看热闹。这次,武田 的人马就好比一群任我处置的麻雀。”
家康脸上现出不快的神色,信长嘴里说是助一臂之力,可心里却想单凭自己的力量取胜,以此向天下炫耀实力。
“您不是说是‘一臂之力’吗……”一会儿,家康又恢复了先前的微笑。
“你求我帮忙,我们如果只是游山玩水也对不起你,所以想奋勇往前,没想到你却误会了我的美意……”说完,信长把目光移到展开的地图上。这是在冈崎时议 好的兵力部置图,上面用红笔画满了圈圈点点。沿着连子川河岸围满长长的栅栏,然后把敌人引诱过来,就可以像捕麻雀一样任意处置他们。
家康盯着地图,又仔细想了想:“仅仅这样,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织田和德川的人马总共两万八千,其中包括信长从势力范围内调集到的三千五百火枪手。从岐阜出发的时候,信长特意让每个人扛了一捆木材来,他用带来的这 几万根木材做栅栏,从连子桥一直到弹正山的左翼,光栅栏就结结实实地做了三层,即是为擅长骑马作战的武田军预先设下的绊马桩。
要想一举捣毁家康和信长的营盘,武田的人马必定试图突破栅栏,而大量人马会在此处受阻,届时,所有火枪对准拥挤在栅栏处的敌人猛烈开火,这就是信长考 虑了很久的密策,是必胜战法。正因如此,他才胸有成竹地对家康说什么游山玩水啦,什么只管观赏风景啦之类的话,而家康还是觉得不放心。
“噢,这样你还不放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信长感到有些意外,盯着家康问道,“哪里不妥,只管讲来听听。”
家康不答,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方道:“您肯定武田会来突破栅栏吗?”
“哈哈哈……这个我可以打包票,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但是,即使是敌人中了我们的圈套,也……”家康说到一半,又打住了,“我的家臣中,有个叫酒井左卫门尉忠次的……”他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说起莫名其妙的话来。
“你在说什么?”突然,信长也警惕起来。他那老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想透视家康的想法,“忠次这人,由于出使过多次,见多识广,即使不用别人提醒,也知道怎么办。你是想问问他有什么计策?”
“要说忠次,确实能征善战,现在可以把他叫出来,向他讨个主意试试看。”
这次,神情严峻、思虑重重的换成了信长。“好吧,赶快把他叫来。”
“小平太,传忠次过来。”家康说完,将手中扇子指向栅栏阵的起点连子桥外侧,“在那里,可以让我的家臣大久保兄弟为诱饵。如果再劳您大驾,家康实在于 心不忍。”信长哑然失笑。家康的按部就班也并非无可取之处,但是,信长不是这类人。家康精如猴子,诡计多端。这样也不错。两员大将斗智斗勇,充分发挥各自 的长处,联军就会越来越强大。
“你所说的大久保兄弟,是不是七郎右卫门忠世和治右卫门忠佐?”
“正是。我想让他们兄弟俩为我军打头阵,大人意下如何?”
“好。要是让大久保兄弟去,我没有意见。”信长又道:“如果栅栏外的大久保兄弟陷入苦战,我会命令柴田、丹羽和羽柴三员大将从北面杀出。”
说话之间,酒井忠次来了。营内众将和侍从,目光刷的一下都集中到了他身上。因为对信长的战略不大满意,家康觉得心里不安,所以,他把忠次叫来问一问,也并非毫无道理。
“噢,是忠次啊。”还没等家康招手,信长先打了个招呼,“这次战役,你有什么策略,说来听听,不要拘束。”
“是。”忠次深深地鞠了一躬,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郑重其事地走到信长面前,单腿跪地,研究起地上展开的地图来,“在这里,武田军追击我方作诱饵的部队,向有海原出动,如此一来,敌人后方就空了出来。”
“会空出来?”
“是的。那时,我军则悄悄潜入敌人背后,乘机夺取敌人在鸢巢山的防御工事,两位大人意下如何?”
“夺取敌人后方的鸢巢山……”家康沉吟。
“是的。如果大人照我所说安排,可在前一天晚上潜入敌人背后,黎明时分就会拿下鸢巢山,到时候,大人就会看到这样做的效果了。”
忠次得意扬扬地讲着,家康则在一旁似听非听。信长以敏锐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突然大笑起来:“忠次啊!”
“在。”
“我信长活了四十二岁,才开始明白那句谚语:螃蟹挖洞学田螺——就这么点本事。哈哈哈哈……混账,还说什么清楚这次战役。这不是和强盗山贼的战斗,这是大战,你讲的那些,在三河、远江等地只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小战场可以管点用。行了,你的聪明才智我领教了,滚!”
一旦嘲笑起别人,就破口大骂,无休无止,这正是信长的性格。忠次羞得面红耳赤,一旁的众将大气也不敢喘,一个个低着头。只有家康依然保持着沉默。
“那么,请恕在下告退。”
忠次退下去后,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其后的商议,转来转去总围绕着把敌人引诱到木栅栏之后,如何如何这一点上,当然,如果敌人不上钩,必须重新考虑。夜幕降临的时候,会议才基本结束,众将各自回到新的营帐。
“家康,不忙回去。”当只剩家康主仆几人的时候,信长笑着说道。
“到底还是被他看透了。那么,请忠次再来一趟吧。”家康也心有灵犀。他两眼看着信长,一边点头,一边用力一字一句地说:“如此一来,我军就胜利了。终于可以安心了。”
当忠次再次被叫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地上燃起一堆堆篝火,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忠次脸色苍白,一副戒备和愤怒的神色。
“忠次,过来。”家康缓缓地向忠次招了招手,“织田大人说再跟你谈谈。”
“是。”忠次来到二人面前,单腿跪倒在地。信长挥挥手,把两名贴身侍卫也打发下去了:“忠次,再往前来一点。”
“是。”
“不愧是家康的左膀右臂,你刚才讲的策略,我心里实际上佩服得五体投地。”
“……”
“虽然是在营中,但也不可麻痹大意。由于刚刚发现一个州甘利新五郎的奸细,我干脆将计就计。因此,敌人必定前来有海原决战。只是,先出击的敌人遭到我 军迎头痛击后,发现不对劲,定会撤回去,这样一来,我们的猎物就少了。因此,我正在考虑有没有更好的计谋。决战之日的早晨,夺取鸢巢山的敌人工事,实是高 见,真是说到信长的心坎上了。只不过由于是夜袭,一旦让敌人知道了,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故意在众将面前嘲笑你。我想明天一天打桩钉栅栏,你明晚悄悄行 动,趁敌人到有海原的时候,趁机拿下鸢巢山的堡垒,我给你五百火枪手,你意下如何?”
“这……是真的?”由于太意外了,忠次看看家康,又看看信长。家康依然双眼微闭,似在侧耳倾听。
“哈哈哈,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妙计,如果让人给听了去,岂不可惜,所以,我是故意斥责你的,还请你不要见怪。说句实话,你讲的夜袭,我恨不能亲自去呢。家康,立大功的机会让忠次抢走了,真可惜。”
家康依然轻轻点点头,然后对忠次说道:“率领五百火枪手,好好干。”
“是,二位大人放心。”
“注意,莫要被人发现。”
“遵命。”
“那么,我也告辞,回去还有好多事得赶紧给众将安排。”家康深施一礼,站了起来,信长则不客气地拍拍他的肩膀,“你听远处打桩的声音,咣当咣当,多么悦耳啊,德川大人。”
就这样,德川、织田的军情议事结束了。
药王寺山的武田胜赖也连夜把众将叫到一起商议军情。营帐里点了许多大蜡烛,奇热无比,走进去就跟进了蒸汽浴房似的。众人脸上油光闪闪。
“这么说,主公无论如何都要决一死战?”正对着胜赖、说话犹疑不定的正是马场美浓守信房。
也不知是否听到信房说话,胜赖把主战派的迹部大炊助胜资叫了过来。
“听说在敌入内部卧底的甘利新五郎来报,什么内容,赶紧讲一讲。”
迹部大炊故意夸张地点点头,然后看了一眼马场、山县、内藤和小山田,那眼神仿佛把四人都看成反对决战的头头。“是这么回事,织田的大将佐久间信盛通过甘利给我写了一封亲笔密函说佐久间要归顺武田氏,得立一件大功,他想以此作为礼物献给主公。”
“嗯?佐久间信盛想为武田效力?”内藤修理急切地问道。
“确实如此。”迹部大炊重重地点点头,“函上说,信长的缺点是性子急,一旦发起火来,不骂到满座人都低头不语,决不罢休,一张利嘴曾把佐久间盛骂了个狗血喷头,这话早就听甘利说了。”
“果真如此?织田可是马虎不得的谋略家。”
“说的正是。”大炊用军扇拍拍胸脯,接着道,“对方想立个大功献给主公,我看主公既没必要拒绝,也没必要警惕。我想把佐久间亲笔密函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宣读一下。”接着,大炊拿出一封书信来,让大家看了看。
“密函是这样写的:今主织田信长,内中极惧武田大军,所谓主动进攻云云,万不可能,且,身边若无丹羽长秀、泷川一益二猛将,必不敢轻举妄动。故,若武 田军队前去攻打,信盛必寻机从里接应,一举破信长大营。信长大营一旦击破,家康败走无疑,以此为礼,献胜赖公,斯时还望笑纳。”
满座听完,鸦雀无声。
“佐久间想投诚?把密函拿来我看看。”胜赖老练地说着,扫了一眼书信,然后卷了起来,夹在腋下,“不管怎么样,决不能指望佐久间叛变,万一他真来投诚,届时再考虑不迟。那么,明天就照原计行动,左翼由山县三郎兵卫昌景率领。”
“遵命。”
“小幡上总介信贞在一旁辅佐。山县之右为左马助信丰,再右即逍遥轩与内藤修理。”
内藤修理悄悄地看了一眼旁边的马场信房,沉默无语。
“右翼是马场信房和真田源太左卫门二位……”
大帐里只有一个干杂活的僧人在转来转去,给烛台添灯油。一连串的命令下去了,却半天没有人回答,胜赖急了,声音和眼神都严厉得像刀子一样,“你们难道想违抗军令?”
武田一方的军情议事一直持续到十九日晚,主战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微妙气氛,使会议难以作出决议。有的说要看对方怎么出击而定,有的则坚持认为等敌人来了之后再出兵痛击,才是上策。
他们还在争论不休,德川、织田两军的军报却接连不断地传来,对方的军事部署己初露端倪。
听说德川的主力正前往弹正山,并且在山前筑起三重高高的围栏。主战派又众口一词,情绪高涨起来。“佐久间所说果然不假,信长没有前来进攻的勇气。若非如此,他为何进了家康驻扎的茶磨山,还筑起三重栅栏,有筑那么多的吗!”
“如此一来,我方可主动出击,将其一举击溃,即便敌人不出来,我们顶多另想办法而已。”
胜赖从一开始就是主战派,所以,这句话可说是最终说服了反对派。终于,在十九日晚亥时左右,武田一方拿出了最后决议:二十日行动,先在敌人前面布阵, 二十一日拂晓发起总攻。第一支人马为山县的赤备军二千骑。第二支为武田逍遥轩和内藤修理。第三支为小幡上总介信贞。第四支为武田左马助信丰。第五支为马场 信房和真田兄弟。
想打头阵的胜赖最终还是留在了药王寺山,这多多少少也给了反对派们一丝安慰。军事会议结束,众将从胜赖的营帐出来时,时间已经很晚。马场美浓守信房仰望着天上的月亮,等候着后面的山县三郎兵卫。
“山县,你我交情多年,想不到就要分别了。”
“唉!时势如此,还有何方!”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先到你的营帐再说吧。”
“要不去我营帐途中的大通寺山,有一个山谷,那里有一处山泉甚好,再细言吧。”
二人说着,从侍卫手中接过缰绳,这时,内藤修理亮、小山田兵卫和原隼人看见二人,也催马赶了过来。
“就这样分手,真有些舍不得。”内藤修理打了一声招呼,三郎兵卫和信房也相视一笑。这次战役,大家都似已作好战死沙场的准备。
信房想起此事,就不住地捶胸顿足:“要守住武田氏这份家业,就得避免如此冒失,我们都劝过主公,都尽力了,可是,既然决议已定,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如果再说三道四,后人会笑话我们主公愚蠢,做不了领袖。”
信房见大家愤愤不平,又悲痛道:“唉!牢骚怨气,就不必说了。拿出甲州武士的气概来。只可惜,就这样分别,真是令人不舍。”
小出田兵卫也沉痛不已。不知不觉,五人骑着马并排走到了一起。马场信房心情沉重,一句话也不想说。三郎兵卫终于提议道:“咱们到大通寺山的山谷,以水代酒干一杯,然后再分别吧。”
信房紧贴着三郎兵卫,把马靠了过来。他谨慎地望望四周,加重语气:“山县大人,你得活下去。”
“为什么又提这扫兴之事。”
“万一大败,就请你断后,把主公安全送回甲州。”
山县三郎兵卫轻轻地摇了摇头:“鄙人愚钝,恐不能胜任。”
“你若不承担此任,那就麻烦了。一旦主公看见局势不妙,他也会拼命地杀入敌阵的。”
“马场大人,我看这个活儿你来干吧。既已经决定了,我就得服从军令,身先士卒,不然士气怎么起来?到时胜仗也会变成败仗。不要再说了。”
“无论如何……”
“不行,我不能答应你。否则,我掉脑袋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马场信房下了马,唉声叹气,望着时隐时现的月亮,沉默不语。让第一队人马山县三郎兵卫活下来,的确有点勉为其难。如果这样,被任命为第五队首领的自己 就必须为了殿后留下。但是,一旦往甲斐撤退,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都未可知。难道一名武将一辈子所心仪的主人,就只有一位吗?如真是这样,信玄公逝 时,自己是否也应随之而去?同样追慕信玄的人肯定不少,这样一来,是否对现在的胜赖不义呢?
穿过树丛,绕过岩角,来到大通寺山谷底的时候,已近亥时四刻。月光洒下来,溪面泛起银白色。大家找到一处水洼,跳下马来。
“刚开始一万五对五百,现在变成了一万五对四万。”说话的是原隼人。
“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撤退,居然还要决战,不自量力!来,干杯。”内藤修理从马背上取下勺子,舀了一勺水,“那么,先由山县开始吧。”
“哦,真是难得。你们看,月亮的影子映到勺子里了。”三郎兵卫笑着喝了一口,然后把勺子递给旁边的马场信房。
信房毕恭毕敬地端着勺子,口中念念有词:“八幡大菩萨,您就看着吧,诸位,我先去了。”
说完喁了一口,递给内藤修理。
内藤什么也没有说,又递给原隼人。
“哦,多么甜的泉水啊,甜得让人无法形容。”原隼人咕咚喝了一口,又递给小山田兵卫。
“哈哈哈……”小山田兵卫却笑了,“就这样死去,大家说的话怎么听起来就像撒谎一样。哈哈……”
不知从哪里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仔细一听,溪流声中还似和着河鹿的低声叹息。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从黎明时分起,东南风就猛烈地刮着,发白的天空风起云涌。武田军第一队的山县人马,已经前进到左翼最边上的连子桥附近。预料到战 斗可能会在早晨打响,他们早就作好了准备。天刚蒙蒙亮,前面构筑的防马栅栏看上去还不是很清楚。山县的赤备骑兵队的任务就是冲破栅栏,杀进敌人大营。
“该吹进攻的号角了。”三郎兵卫望着前方自言自语。短小精悍的他飞身上马,显得格外威武。
“喂,有敌人到栅栏外面来了,给我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人!”
三郎兵卫有些纳闷。黑洞洞的栅栏露出一丝亮光,有一些黑影在那里晃动,定睛一看,原来是些步兵。
家康的手下有两员猛将,一为大久保忠世,另一为大久保忠佐,这兄弟二人,乃是家康的左膀右臂,打仗的时候,总是这二人中一人开始,另一人收尾。今天在此把守的正是这兄弟二人。由于山县乃武田大军赫赫有名的猛将,所以,兄弟二人丝毫不敢马虎,还没等到天亮,就开始行动。
山县派出的探子还没有回来,只听见对面大久保的人马摩拳擦掌,喊杀声震耳欲聋。“不要轻举妄动。”
三郎兵卫命令道。他独自骑马登上一座小山丘,察看敌情。视野模糊,看不清到底有多少敌人。但是敌人一旦出来,就是天大的好事。若是敌人缩了回去,他无论如何也要踏平栅栏,发现敌人要出来,便可趁机冲上去,杀他个七零八落。
“报!栅栏外的敌人乃是大久保的人马。”
正在这时,突然从后方的鸢巢山方向传来闷雷似的声音,嗵嗵嗵,嗵嗵嗵……像雪崩一样,枪声大作。
“嗬!他妈的!”三郎兵卫勒住战马,骂了一声。这枪声听起来不像是只有五六十支的样子。如果大敌已经摸到了背后,那么后路便被掐断了。
毋庸置疑,这枪声正是酒井左卫门尉忠次率领的火枪奇袭队打响的。忠次率领信长特意配给他的五百火枪手,昨天晚上就已摸到了鸢巢山上。突如其来的震天枪声,使左邻的武田左马助和后面待机的小幡上总介的阵营像炸了锅一样,乱作一团。
山县三郎兵卫勒住马缰,像塑像一样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良久,他大喊一声:“各位注意!”接着像风一样催马跑到阵前。
大战开始。不,不如说是二千名骑兵武士为了踏平大久保的步兵,卷起了一阵狂风。
天渐渐地亮了,战鼓咚咚,号角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