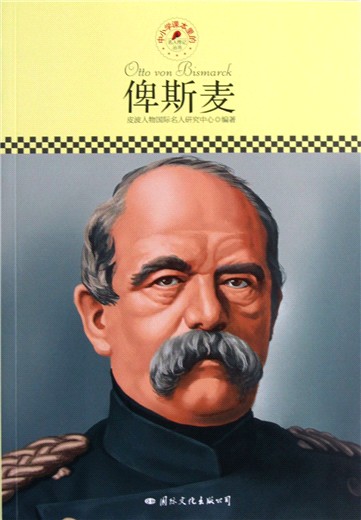1941—1951年
1941年,曼德拉——一个引人注目,有着自然威严风度、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成了成千上万拥向约翰内斯堡人群中的一员。两年前,南非在史末资将军领导下加入英国及其盟国一方,对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进行战争。战时工业对劳工有大量需求。
坐乡间公共汽车,然后又坐火车(在一节标有“非欧洲人”的车厢里),曼德拉一路北上,经过纳塔尔进入德兰士瓦的高地疏林草原,直到堆有黄砂的矿区渣坑所标志的金城埃戈利郊区。他突然被推进一个高楼林立的新世界,车辆往来快得令人目眩,各种肤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奔走繁忙。城区和白人居住的宽阔市郊,到处是繁荣的景象。可是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许多“郊区土著人乡镇”和城市的贫民区内。这些贫民区居民拥挤,卫生条件极差,没有电、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电话,可不断地受到警察的抄查,搜寻那些违反通行证法和违反禁酒法的人。骚乱纷起,家庭瓦解,罪案频增。对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非洲人来说,这些就是种族歧视下的严酷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开始了。
他从童年起所受的训练是过体面、有地位和受保护的生活,而现在他被投进城市生存的熔炉。第一件事是找一个工作,而最好的希望在矿上。许多年后他很有趣地回忆这段往事:他被录用在皇冠矿当一名警察,答应不久将提升他当办事员。他带着圆头棍和口哨,守在通往黑人矿工住区的大门旁。可没几天大酋长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于是他再次逃跑。
他在亚历山大找了一间房。亚历山大是约翰内斯堡东北边缘一个杂乱的市镇。有个熟人建议他去见“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可以给他出好主意。西苏鲁比他年长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非常了解被列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在矿上他曾经拿着尖锄、铁锨在地面下1英里处干活;他在一个白人家里当过“厨工”;他在一系列的工厂里工作过,同不公道的老板发生冲突。与此同时,通过函授他读完了初级证书课程。他和母亲住一起,她为白人家庭干洗衣活。曼德拉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城里开一家地产介绍所,经营尚能为黑人使用的享有自由保有权的土地。他立刻给这位年轻的新来者一个工作,每月2镑外加佣金。
曼德拉诉说他早年想学法律的志向,于是西苏鲁提供经济援助,使他能够通过函授课程取得文学士学位。西苏鲁还借给他一笔钱买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后又把他介绍给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于是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一面继续当学徒。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同“欧洲人”打交道——当时人们都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地方长官、商人和教师;现在曼德拉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在一起。他一到办公室,那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向他说明:“你看,纳尔逊,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佣人送茶时,你就从盘上取你自己的茶。我们已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它,告诉高尔一下。注意点,他影响不好。”
高尔·拉代贝也是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小个子,比较高傲,政治上激进。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的回答说:“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来,拉代贝避开新杯子,故意挑一个旧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争吵,也不想和打字员争吵,装着不想喝茶。
另一个打字员在没事做的时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当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这个女孩子显然很窘。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品店买点香波。”
他带着幽默感讲述着这类小事。当白人的偏见和愚昧指向他本人时,他的反应总带着这种幽默感;当指向不能自卫的人民时他就极为愤怒。
在当学生的时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结婚。她是一位漂亮说话温柔的护士,在市立深矿医院工作。他们在奥兰多安家。奥兰多是正在扩展的市镇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挤满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约翰内斯堡的西南大约10英里(这一带后来名叫索韦托,那是“西南部市镇”这几个字字头的缩写)。西苏鲁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护士。奥利弗·坦博这时也已来到约翰内斯堡,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物理课。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业余课程很艰巨;而且他缺乏适当的学习设备,还有长途火车旅行和夜里11点钟的宵禁。他跟着当学徒的这家事务所里的一位波兰犹太人,对他很好,使他永远感激。那位同事给他种种鼓励,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师,从而“赢得各界居民的尊敬”,还要他躲开政治。
但曼德拉无法这样束缚自己。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滕布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吸引。沃尔特·西苏鲁已是一名成员,他还鼓励坦博和曼德拉投身于黑人政治团体中这个历史最久和坚定不移的组织。可在194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时衰落失去许多会员,他们分裂出去组织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样称呼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职责应是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来推进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从那以后,他们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国民大会活跃起来,并证明了他们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非洲人国民大会(原来叫作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国民党的前两年。四名青年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塞梅本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来。他们的目标是团结自己的民族。塞梅认为,部族倾轧是歪门邪道,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他坚持,“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大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酋长们和他们的部下、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牧师、教师、记者和律师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们从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亚纳、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教育家约翰·杜贝被选为全国主席,塞梅当了司库,自学成才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普拉吉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个组织以美国国会为原型,也含有英国议会的结构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议长和一个由酋长组成上议院。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在议会、教育、工业和行政方面废除种族歧视。一位代表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当时梦想着有一天出现变革,非洲人坐在议会里并且能够自由购买土地。”
他们的确是非洲人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是反白人。也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将他们引向谋求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分一杯羹,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不许用黑人种族主义以牙还牙。在以后几十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背离它对种族主义的否定。
那场第一次庄严的集会还念了祈祷文,唱了一首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美诗《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采用为国歌)。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一面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此后是漫长的抗议岁月,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为。抗议表现为示威游行和集会,表现为派代表团和请愿。这种非暴力抗议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加紧镇压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此时有一位来自东开普省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牧师詹姆斯·卡拉塔,不顾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开始顽强地复活这个组织。此前,他已被任命为总书记。a·b·克苏马博士充实进来担任新的全国主席,保证了那场复活运动。游历广泛、经验丰富的克苏马在约翰内斯堡开业行医,生意兴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往来,其中有z·k·马修斯,他是黑尔堡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和“土著法与政府”的讲师,在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声名。1936年,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尔佐格的种族隔离法案所震惊,此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开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这些能干的青年人一样。后者在黑尔堡卷入了学生运动,此时也正在崭露头角。
这是一个人心骚动的时刻:工业发展带来了外国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外国投资靠着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给黑人的工资通常低于最低生活水平,各种非洲人工会正在变得更富有战斗性。可是,当工人们向这种制度挑战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施加压力:1942年发生的一系列罢工遭到史末资的“战时措施第145号”的反击,这个法令宣布非洲人举行的一切罢工都是非法的。尽管如此,罢工继续进行。在亚历山大,人们罢乘以反对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他们太穷了,付不起昂贵的车费。在高地疏林草原地带,在凛烈的寒冬里,数以千计的男女上工来回步行10英里。10天后,公共汽车公司投降了。1年后的1944年,车票再次涨价,抵制重新开始。这次人们步行7个星期直到赢得胜利。
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促进了自由和自决的思想。阿非里卡极端主义者也许亲纳粹,但南非的非洲人领袖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和非洲遭受殖民统治的各民族,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在克苏马和马修斯领导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一项《非洲人的要求》文件,要求“在所有国家里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和积极推动“殖民地人民享受自治”。除废除通行证法和对产业工人的种族歧视,以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要求之外,他们还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当然包括选举权。
所有这些事件和影响,以及政府并未实现改革的诺言,激起了曼德拉和其他青年民族主义者心中新的对抗情绪。奥利弗·坦博在谈到那些日子时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不跳舞,也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也如此。”(可是曼德拉注意锻炼身体,他成了很好的拳击手。)他们在彼此的家里或办公室里集会,畅谈自己的政治哲学。
博学的、富有吸引力的安东·穆齐瓦克海·伦贝迪,极其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是祖鲁族农场工人的儿子。这些工人穷得披着麻袋当衣服,可是他们决心要使这个孩子上学,设法凑够上小学的费用。然后他靠着自己努力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一名律师。伦贝迪和a·p·姆达(也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了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青年联盟”。他们着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振作”起来。他们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洲人意愿的象征和化身,要有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是在组织上它一直很软弱,“把自己看作是双手光洁的绅士们的团体”。“青年联盟”向那些非难者保证“他们父辈的斗争和牺牲”并非徒劳;它必会成为“非洲民族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必然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外国人领导”和“大规模输入外国思想”,都被坚决地拒斥;尽管这些思想如果有用可以借鉴。
伦贝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同克苏马博士洽谈,后者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他的谨慎是对的;他们的“振作行动”将根本改造这个组织。
1944年4月,伦贝迪被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被选为书记。曼德拉也参加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说他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从不注意让国民大会组织群众运动。他们的宗旨是,通过“青年联盟”促进一场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为达到这个目的,“青年联盟”将为废除种族歧视法律和非洲人能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斗争,以便非洲人“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将按人数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之外还要加上大众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他们要求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与此同时,克苏马博士和共产党以及南非印度人大会组成联合阵线,开展反对通行证法运动(共产党创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于1894年由圣雄甘地创立)。政府拒绝议会要求撤消通行证法的一项法案,并下令大批逮捕违反通行证法的人,于是反对通行证法的运动急剧发展起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宣称通行证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里的希特勒式的作法”。但是游行、请愿和派代表团——一切能做到的合乎宪法的抗议方法——都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因为经过纳粹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非洲人和有色人发挥了作用),变革肯定不可避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胜利游行。游行规模之大,在约翰内斯堡前所未见。20万非洲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人跟在铜管乐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三色旗帜之后,口号是“让我们消灭这种勾当!”但是,由于战争使这个国家向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外国投资开放,它使白人增添了财富、也加强了权力。
1946年发生的事件,清楚地提醒人们不仅仅是非洲人受压迫:印度人走到斗争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位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起了领导作用。这时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集团住区法”,这个法案打算将印度人永远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实际的抵抗活动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
曼德拉时常和米尔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场大街胡勒瓦德大厦里米尔的单元房,家具寥寥无几,是一个人们聚会场所。在这里朋友们、学生们和积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和辩论直至深夜。其中有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鲁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士,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后者是一个年仅18岁英气焕发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移民那样,属于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活动家之列。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