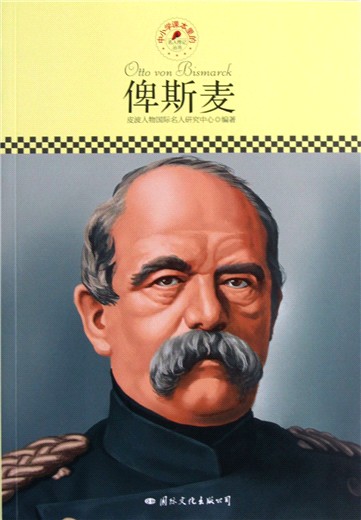他叙述了自己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和他所接受的训练课程。法庭上有他对这些事情所做的几本笔记,这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宗旨一贯是非洲民族主义。它的概念不是叫喊“把白人赶下海去”那种非洲民族主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自由和自我完善。
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自由宪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蓝图。它号召重新分配财富,并不是土地国有化;它规定矿山、银行和垄断企业国有化,因为目前大垄断资本只让一个种族占有。假若对它们不实行国有化,就算政治权力扩大到白人之外,种族统治将会延续下去。在所有的金矿让欧洲人的公司占有的情况下,废除“黄金法”对非洲人的禁律只不过是作个姿态而已。在这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和国民党过去的政策是一样的。许多年里,国民党把金矿国有化作为它纲领的一部分,因为那时金矿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根据自由宪章,国有化是在私人企业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的。实现自由宪章会给非洲人的各个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繁荣开辟新的天地。以我所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鼓吹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没有谴责过资本主义制度。
以共产党而言,若我对它的政策理解正确的话,它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建立国家。虽然它也准备为实现自由宪章而努力,以此作为对白人统治所造成问题的短期解决办法。它把自由宪章看作实现纲领的起点,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不同,它只吸收非洲人参加。它的基本目标过去是、现在仍是实现非洲人的团结并赢得完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工人阶级的统治。共产党试图强调阶级差别,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试着协调它们。这是二者的主要差异。
的确,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不断进行紧切合作。但是,合作只能证明它们有某些同样的目标——是指消灭白人统治,而并不说明它们的利益完全共同。
世界历史充满这类实例。英国、美国与苏联一起反击希特勒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除希特勒之外,没有人能说这种合作使丘吉尔和罗斯福成为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力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
这种合作的另一个例证完全可以从民族之矛之中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有成员告诉我,共产党会支持民族之矛,后来的确这样。
他还举例说明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未成为共产党国家。他还说过去共产党人能够而且确实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他回忆说,年轻时,他在青年联盟成员中曾经主张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这个提议遭到失败。反对者包括保守主义者。其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开始就应将自己建成一个涵盖各种政治主张的非洲人民的议会,而不是仅包括一个派别的政党。他最后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成见,南非白人很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政治家会欣然将共产党人作为朋友。但是对我们,理由很明显。在为反压迫而斗争的人们之中,在当前阶段,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想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同进餐,一同交谈,一同生活和一同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和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现在很多非洲人趋向于将自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的这种信念,因为立法机构把一切拥护民主政策和非洲人自由的人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而被进一步确认;在“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之下,把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被宣布为非法者。虽然我一直就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我在蔑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本人也在这个恶劣的条例的名义下挂了名。我还因此被软禁,遭关押。
不仅仅我们在国内政治中将共产党人看成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直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也在支持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其实比西方国家更同情我们的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要比绝大部分白色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厉害。在这样的形势下,象1949年的我那样傲慢的年轻政治家,才会宣称共产党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曼德拉谈到自己的立场问题。“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洲爱国主义者”。接着他介绍了他在特兰斯凯的滕布兰地区代理大酋长监护下的成长过程。现在他被无产阶级的理想所吸引,这部分是因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部分也来自他对早期非洲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赞赏。那时南非的土地属于部落所有,也不存在剥削。
确实,象我已经说明的,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以为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让我们的人民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所遗留下来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我本身,我认为,对共产党在当前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中是否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还可以讨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按照自由宪章获取民主权利。只要那个党推进这项工作,我就欢迎它的帮助。我认为这是各种族的人参予我们的斗争的一种方式。
从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从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人认为西方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但是,与此相反,我却赞赏这个制度。
《大宪章》、《民权法典》,是全世界民主主义者所心仪的文件。他补充说,他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西东方两方面的影响,他希望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时完全客观。
曼德拉接着又转到共产主义问题。他对展出的三份他的手稿作了说明:他的一位老朋友,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也是共产党员,这个朋友曾劝他加入共产党。他却予以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立场不鲜明并且充满难懂的术语。他的朋友让他把想法重新写一份材料。曼德拉告诉法庭,“我同意了,但是我没能做完这件事……直到这次审判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我没有再见到它。”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政府曾提到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受共产党的启示,共产党则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推动非洲人民参加军队,这表面上是为非洲人的自由而战,实际上却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
曼德拉声明:
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十分荒谬。民族之矛是非洲人建立的,是为了在他们自己土地上取得自由而战斗。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支持这个运动,我们唯一的期望是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非假想的苦难,或者象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明显特征——贫困和没有人之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确认,是我们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南非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这里的差别极大。白人可能享有的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非洲人则生活于贫困和痛苦中。40% 的非洲人生活在拥挤不堪的“保留地”,有些地区干旱严重。那里的土壤侵蚀和过度耕作,使非洲人不可能只以土地为生。30%的非洲人是劳工、佃农或在白人农场里作雇工,过着类似于中世纪奴隶的生活。其他30% 的人住在城镇,在那里他们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习惯,使他们在很多方面离白人更近。但是绝大多数非洲人,甚至这一部分人,仍因收入微薄和物价极高而陷于赤贫中。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列举了1960——1961年白人和黑人教育经费开支的数字,说一个白人孩子的教育费用等于黑人孩子的12倍,而同时班图教育制度对非洲人的限制使他们的教育更为低劣。由于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好工作都给白人留着,黑人工会不被承认,黑人的罢工不被准许。
曼德拉继续说: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
从他自身的经历,从他作为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中所见到的一切,曼德拉明确指出了非洲人民在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
“通行证法”,是非洲人最为痛恨的立法之一。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都随时受警察的监查。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贫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和黑人城镇所独有的种种暴力事件。监禁和死刑也没有能医治这种脓疮。
非洲人想得到足以糊口的工资。非洲人希望从事他们能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政府认为他们应做的工作。非洲人期望他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居住,而非被强迫离开不是我们出生的地区。非洲人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能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永远也不会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非洲人希望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限制在他们所居住的黑人区。非洲男人希望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在男人单身宿舍过着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生活。非洲妇女希望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而不是长期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希望在晚上11点钟以后可以出门,而不是象孩子那样被禁闭在家里。非洲人要求能在自己的国内旅行,在他们愿意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所指定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整个南非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要求在社会中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我们永远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这些话在白人听起来很革命。因为选民的大多数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但是,不能允许这种恐惧阻止这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它能保证种族和睦和所有人的自由。不能认为给所有的人选举权就导致种族统治。以肤色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它消失了,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的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种族主义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它成功后不会改变这个政策。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进行着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真正民族性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因他们自己的苦难、自己的遭遇所激起的斗争。这也是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曼德拉讲到这儿停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起头看着法官,当他重新说话时,声音低沉:
我在一生中,已经把自己奉献给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斗争,也反对黑人专制。我珍爱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献身。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曼德拉说了4个多小时。现在是第二被告沃尔特·西苏鲁。作为辩护的主要证人,他要反击原告长时间的进攻。然而一旦掂量出尤塔的分量,西苏鲁就忘记了自己是处在被告席上。他有11年没在公共场合露面了,现在他却要控制这个讲坛。他和戈文·姆贝基的任务是讲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四天,既不试图作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没有警察的行动,南非今天就会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该给予警察很大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