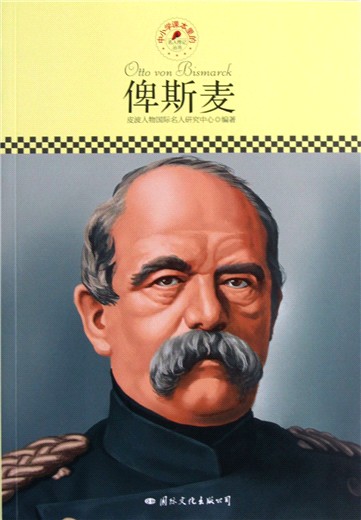1971—1978年
在罗本岛,被《泰晤士报》称为“南非民族主义巨人”者,是466/64号囚犯,他每天在海滩上采集海藻制作肥料。那是极累人的劳动,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冲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远处,船舶驶进驶出开普敦港。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使我们放弃战斗,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我们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被当作犯人,而是也被当作黑人对待,这样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
到70年代初,他们顽强地表达的不满再加之国际上的压力,赢得了虽不大却有意义的改进:牢房里有了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冬季有“权”在读书时用条毯子围在身上;有热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个排球场,它后来改成一个网球场。他们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绝,因为这意味着走出隔离区。在室内,他们有乒乓球和国际象棋,每月有一场电影,每天晚上放录音音乐。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惩罚的。更重要的是,接触新闻的要求一再被严辞拒绝,从事木工和编篮子之类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由于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许可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来后狱规进行了更改,及时得到最新书籍以完成课程变成不可能了。接着,当局又禁止政治犯修习研究生课程,这严重剥夺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并且因不许学法文和德文,就改学高年级的阿非利堪语。
他突然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曼德拉被剥夺一切学习权利4年。监狱的官员称发现有“回忆录”藏在牢房里,而政治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纸张受到严格限制,仅够用于学习和写被允许的每月一封500字的家信。他要求“拿出回忆录给我看看”,他们却从来没有出示过。
经过在石灰矿坑多年劳动,他不是唯一视力减弱的人。由于他患高血压而且腰部不好,狱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他一张床,板凳换成椅子,并给予无盐伙食。象利沃尼亚案其他人员那样,他从d类升到c类,然后又升到b类,他被允许有更多的探视,但还是限于每次半小时。
每到探视时,温妮都必须办理同样的手续:首先通过地方长官从司法部和警察那里取得书面许可,然后在出发和返回时都向警察报告。不再允许她坐火车或小汽车,而必须乘飞机去开普敦,这样就要承担更多的旅费。国内外朋友们慷慨地捐助。很难记得住对谈话的种种限制。当问到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引起看守们掐断她同她丈夫的对话时,温妮说:“当他问到鲁斯·弗斯特或鲁斯·马索奥阿内(他过去的秘书)或奥利弗·坦博的情况时;当他谈论特兰斯凯的情况包括他的家庭——马坦齐马兄弟们时;以及说到正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时谈话就被打断。”
曼德拉常常说服看守们让探视继续进行。“他和他们说话好象他们是小孩子:‘你们肯定听得出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有相当长时间没见到我的家属了;不管怎样我想继续下去,你们继续听吧,那是你们分内的事。’”
他的探视者当中有马克加图、马卡基韦和他的姐姐梅布尔·诺坦库·恩提马克韦。他的母亲也曾远途跋涉渡海来到罗本岛。相聚之后,当看着她离开时,他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他接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已经去世。温妮和孩子们在特兰斯凯参加了葬礼。
一位从特兰斯凯来的亲戚在葬礼之后到罗本岛探视,他说到曼德拉对于那些操办葬礼的人是如何的感谢:“他一直问,某某人来了吗?某某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灵通。他让我对所有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表示问候和感谢。”
1973年12月,监狱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视察,这反映了政府急于兜售它班图斯坦“独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难友麦克·马哈拉吉率领的代表团指出,如果他们承认特兰斯凯,愿意住在那里,他们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复是“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绝不会妥协。”(尽管如此,政府后来仍几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还是“不”。)有讽刺意义的是,小酋长凯泽·马坦齐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领导特兰斯凯走向“独立”,按滕布人风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总理沃斯特也向温妮·曼德拉提出过,给她自由的条件让她承认特兰斯凯是她的“家园”。她的回答是:“厚颜无耻!要是有人应该离开南非的话,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她再次被控违反对她的禁令,1974年期间在克龙斯塔德监狱被监禁6个月。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感到在那里更加解放,肉体上觉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它更能令人满足。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监禁引起了不安。津姬听到这个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你永远不要哭,你哭他们就高兴。”泽妮回忆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们的监护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带着探视她们的母亲:透过玻璃隔板她们和她谈话半个小时,谈关于学校,关于零用钱以及她们是跟谁在一起。温妮看上去总是很好。但是孩子们开始发觉朋友们害怕到家里看望她们,因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们带走审问。
很久以后,曼德拉回忆起他当时的情感,他给妻子写信说:“虽然我总是努力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我实在不能适应你也被关到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象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苦难似乎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绝不会忘记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德度过的6个月期间,我们所遭受的令人极为痛苦的经历。”1
温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诉、缓刑和监禁,关于这些方面的详情难以掌握。在她而言,长时间的反抗是对成千上万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战中她无所畏惧,对他们的粗暴侵扰,她大胆地予以还击。可是一系列的阴险袭击,使她身体受到攻击,她的住宅被扔进汽油弹,她毫无办法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曾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攻击行为出于政治动机。”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津姬也发现父亲的幽默和热情。她告诉一个记者,“事前我很愤怒并有点忧虑。但是我发现他很有办法,也很迷人。他设法使我的思想摆脱那里的环境,使我想起比较快乐的情况。他说,‘你知道,我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坐在我腿上和全家一起吃星期天烤肉。’”虽然她没有看见父亲走来——她们被领进小屋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她设法瞧着他在会见后走开,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健康强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敏捷。
当女孩子们下一次探视时,她们单独前往。开车送她们到开普敦码头的那个朋友,看着她们和一队穿着橄榄绿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认为这是令人伤心的场面,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唱着他们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间里,温妮和她的丈夫达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从对方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彼此的斗争环境后,曼德拉以谨慎的方式,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虽然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更为接近,但这些年轻的领袖们首先受到被流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的赞许,称赞他们“以勇敢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把斗争推向前进;并以其行动表明保证革命的主要动力——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非洲人国民大会机关刊物“塞查巴”说,用“黑人”称呼所有被政府列为“非白种人”者,是一个新事物。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是60年代从泛非主义者大会那里继承来的,渊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国地图上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给东非一个奴隶国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一书中,把想象中的非洲国家叫做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这个名称。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
延续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了,这对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独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主席欢迎奥利弗·坦博,称他为同志和战友。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也得到很大推动,因为莫桑比克能为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提供基地。
但在南非,欢欣鼓舞的黑人很快被镇压,当局根据“恐怖主义法”拘留了77人。这些人包括“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正筹划举行庆祝会来表达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团结;还包括那些被怀疑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募集会员的男人和妇女们。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