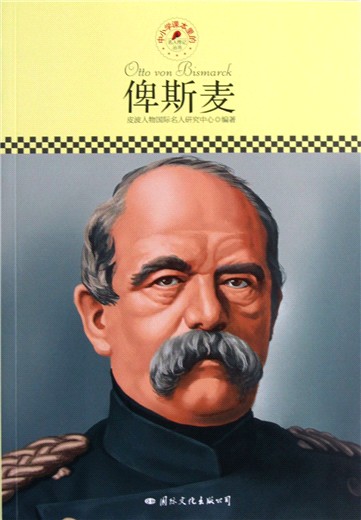他们甚至没有成为这个贫民窟居民的“荣幸”,他们原是被那些肥胖的农场主赶出来的零散劳工。对一些幸运的黑人母亲而言,最高工资每月也只有5兰特。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夜间搜捕和葬礼。
流放听起来很可怕,然而也能给人清静。每时每刻都令人想到,只有黑人才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受害者;这又使人心神紧张。毫不怀疑,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事业多么神圣,但我们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不管我们的贡献如何微小,没有比投身这一事业更伟大的了。
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她开始逐渐被她的邻居们接受,生活发生了变化,以致她可以这样说,“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爱护。我到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唤醒了他们,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非洲人国民大会会高兴的,我没有必要演说或高喊。”孩子们振臂呼喊“权力!”欢迎她。当看到温妮·曼德拉在邮局当着白人的面使用他们的公用电话时,广大黑人也跟着这样做。1981年,面包工人和清洁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罢工。在布兰德福特,这些都是巨大的政治突破。
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几年来,她在干旱的住地为营建绿洲付出了艰苦努力,效果很为显著。她的花园满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生机盎然。她的邻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会提供菜种,也跟着她学种起蔬菜、花草来。
她住的房子一直没有洗澡间,但安装了一个喷头,朋友们送来一台冰箱和电池电视机,还有许多书、精制的非洲壶和邻居送给的几片漂亮的绣花彩布。现在来访的人可以进屋,并坐在诊所边的柳树下喝茶。
在1981年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温妮,获悉了她对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看法。她说,美国政府继续充当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庇护者,甚至是支持者,美国总统也摆出一副“不需要黑人朋友”的姿态。温妮指出,南非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黑人的不满情绪,以致于暴力革命现在已“不可避免”。她严厉批评西方投资商,斥责他们在南非参与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与奴役。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20年来,温妮·曼德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格成长为一名领袖。她变得很漂亮。当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女儿泽妮说:“我想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们的确使她快乐而且不得空闲,当他们玩耍时,你会发现她眼睛闪光。”她有四个孙子女:泽妮夫妇的两个女儿(扎基韦生于1977年、扎马斯瓦吉生于1978年)和一个儿子(津赫莱生于1980年);津姬的小女儿佐莱卡,生于1980年,她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奥帕·塞卡马拉。温妮生活在布兰德福特的艰难时期奥帕给了她极大帮助,甚至在与津姬的关系破裂后,他仍象兄弟一样对待津姬和泽妮。津姬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宗德瓦。
与此同时,温妮坚持学习社会学,偶尔还获准参观南非大学,该学校位于比勒陀利亚城外,温妮的丈夫和其他政治犯曾经也在此地学习过。
有人问泽妮:“你母亲从没有情绪沮丧过?”她回答说:“如果她有过沮丧的时候,她也藏而不露。”奥利弗·坦博一次谈起曼德拉时也说过,他从没有发现纳尔逊·曼德拉沮丧过。当身体不舒服时,曼德拉仅在信中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比如他在1979年9月给温妮的信中就这样写过:“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医生,他给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脚跟进行检查。”
接着他描述了去开普敦看外科医生的旅程:
海水汹涌,尽管我站在甲板上的隐蔽处,仍看到象下雨一般。船不停地颠簸,船头劈开一个又一个浪头。在从罗本岛到开普敦的途中,象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当船在颠簸摇晃时,那情景看起来如同无数铁块在崩落。在几步开外我看到一条救生带。在我距救生带之间有五名警官,其中两名年轻得象孩子。我心中想:如果出事,船要沉没,我将在这世间犯下最后一宗罪行,到地狱后再低头谢罪。我要跑过去冲开他们,第一个系上救生带。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险。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7199票的支持鼓舞了孩子们和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对你来说,那更加振奋人心,它会变蹩脚的小棚屋为楼房,使窄小的房间变成象温莎别墅厅堂一样宽敝的大室。我要让我们的所有支持者都知道,我没有期望得到过100张选票,更不要说7199票,竞争对手是一位英国公主和令人尊敬的英国改革家杰克·琼斯先生。
他希望温妮能在1980年8月代表他去德里——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但南非政府拒绝给她签发护照。曼德拉计划提交印度方面的声明遭监狱当局拒绝,但后来还是被私带出岛,由奥利弗·坦博宣读了这个声明。
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根据经验,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我们得出了新的看法。当眼界放宽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些青年人观点的不妥之处。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声明接着说:
对共同遭遇的理解,虽然这种遭遇的程度令人生畏,但它唤醒了我们人类的整体意识,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世界责任。它有助于我们增强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他援引尼赫鲁的话:“在一个充满冲突、敌意和暴力的世界中,更有必要在一切时候对人类命运保持信心。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则现在的苦难便无关紧要,我们会无愧于为之奋斗的未来。”)
基于这种认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坚定不移地奋勇向前。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雄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