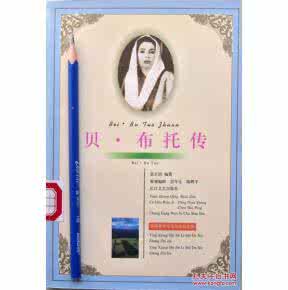云南的沉重军费负担,已引起朝廷的忧虑。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他指出:“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他认为,应把驻云南的满洲兵移驻湖南,以减轻国家对云南的军费负担。【《清世祖实录》,卷136,4~5页。】
自清军入关以来,无日没有战争,生产遭到破坏,加之清入关前明朝的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清接手这个烂摊子,财政相当困难。继季振宜此奏之后,户部于顺治十七年五月又一针见血地说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特别提到云南兵多,已使国家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户部报告说:目前“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云南所需粮饷尤多,“以致各省挽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非)小。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今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应敕兵部酌议,务部永远可行”【《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
无论朝廷重臣,还是地方大吏,都强烈呼吁,只有撤军、裁军才能使国家的财政负担有所减轻。
截至顺治十七年五月,吴三桂的兵到底有多少?幸好清官方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准确的数字。在上面引述的户部奏疏中透露:“云南平西王下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包括归降的南明兵与农民军)共六万名。”两项合计,共七万人。【《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三桂在进军云贵过程中,收编了数以千计以至万计的降卒降将,都隶属他的统率之下。这些人特别能战斗,堪称雄兵猛将。再加上他从辽东带来的将卒,也是一支能战斗的部队,成了军中的骨干部分,“素称精锐”。他的军队既多,又能打仗,是一支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除此,在云南还驻扎了不属于他统领的满洲八旗兵,如信郡王多尼平南将军卓罗等部、洪承畴部,与三桂兵合计,总数可达十二三万。这对于云南省来说,是无法养活这么多军队的。户部提出的报告,引起世祖的重视,以为此事为“国家要务,关系重大”,要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速奏”。
以军事起家的吴三桂,自然不愿意裁减他的军队。为此,他向朝廷申辩:“边疆未宁,兵力难减,宜如旧时。”说“边疆未宁”,也是实情。李定国、白文选还隐蔽在中缅边境伺机出击;永历作为明朝的象征,政治的偶像还存在,有卷土重来之忧。但他们的力量已消耗殆尽,对付他们,是不需要数万大军的。三桂提出的理由,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不让朝廷动他的一兵一卒!三桂明白,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与威望,就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庞大军队。
三桂的心腹将领、副都统杨珅出了个主意:以先除永历,“绝人望”,使裁撤军队之议不能实施。【《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这正是洪承畴所密授的“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之计,此刻即以剿灭永历为名,动用军事力量,就能保证军队之数不致裁减。
吴三桂觉得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吴三桂奏疏日期,《逆臣传》、《清史稿》等书只载顺治十七年,不具月日。《清世祖实录》,卷134载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丙午(二十二日)条下,《庭闻录》则记为二月二十日,前后相差近两个月。三桂请兵进缅前后两疏,此记似将第一疏日期二月二十日误为第二疏四月二十二日之期。】,向朝廷提出进兵缅甸、殄灭永历的奏疏。清朝官书《清世祖实录》、《逆臣传》,以及《清史稿》等都载有这篇奏疏,但都是摘记,且有改动,惟《庭闻录》记录最详,系原疏照抄。为了解该奏疏全貌,也便于分析三桂此时的基本思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臣三桂请进(兵)缅(甸),奉旨: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无强行”;再则曰:“斟酌而行”。臣窃以为,逆渠李定国挟永历逃命出边,是滇土虽收而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军费浩繁,睿虑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忽(忍)以此贻忧君父!顾臣向请暂停进缅者,益谓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粮食不充,事多牵系,在当日内重而外轻也。乃拜疏之后,果有元江之事(指上文提到的沅江土司那嵩之叛)。土司遍地动摇,仗我皇上威灵,一举扫荡。由此蓄谋观望之辈,始知逆天之法难逃,人心稍觉贴然。然逆渠在边,终为隐祸,在今日内缓而外急也。
臣恭承上谕,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务必筹划,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疎,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窃以为边孽不殄,实有三患二难,臣请毕陈其说。
夫永历在缅,而伪王李定国、白文选、伪公侯贺九仪、祁三升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藉永历以惑众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以尽根株,万一此辈立定脚跟,整败亡之众,窥我边防,奋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时,彼已退藏,兵撤复至,迭扰无休,此其患在门户也。
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有(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庆以号召内外诸蛮,饵以高爵重禄,万一如前日沅江之事,一被煽动,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
投诚官兵,虽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
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磬,市中米价巨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凡召买粮草,民间须搬运交纳。如此,年年纳,岁岁输,将民力尽用(于)官粮,耕作半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也。
臣彻底打算,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舒,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谓臣言可采,敕行臣等尊奉行事。
臣拟今岁八月间,同固山额真卓罗统兵到边养马,待霜降瘴息,大举出边,直进缅国,明年二月,百草萌茅,即须旋师还境。但自省城边上,一路粮草,应于云南设法支给,又在边上养马,必得四、五十日,尽力喂养圆膘,须供得两月路程,方可行动。出边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粮。臣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猓猡兵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余万口。以在边养马,出边捐粮,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约该米七万余石。此内如投诚官兵与随带人口,先于安插之日已给月米,节次题明。又经户部拨给官兵(顺治)十六年饷银在案,今应一例随军支给粮饷,其余绿旗、苦特勒原不支粮,今出兵远征官兵,必带苦特勒随往边外,无粮何以养活?应于出边之日为始,将苦特勒照例给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有土司猓猡目兵,原未食粮饷,应于调到之日,照例给米,并酌给盐茶、银两与所带苦特勒一例给米,以励其行,回日方行停支。
此两项虽算在十万口之内,但原非食粮之数,米系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粮,又在到边七万石之外。此盖就出边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马匹仍须牧放,积下一月口粮,在边接济,大约前后共得十万石。此项粮米,不敢外请,发银专待户部。原议拨给云南十六年买米银两,并十七年俸饷、豆草银两,催解到滇,臣分发到边上召买,以备支给,另行开销外,至于满汉约共有马六万余匹,作喂养五十日算,以米、豆、大麦三色兼搭,每马日得仓升八升,共该二十四万石,若以今市价论,需银无数。如谷熟收之日,市价稍平。臣大约酌量米、豆、大麦各价不等,多少牽筭,每斗约作八、九分,该银二十余万两,又马日支草二束,共该六百万束。若以今日市价论,每束该七、八分一钱不等,需银甚多,俟秋成后,臣鼓励士民召买,每束量给草价、脚银二、三分,约该银十七、八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庭闻录》,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