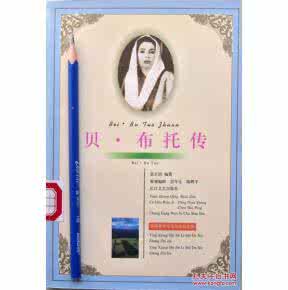其一,恪守清太宗以来,世祖、多尔衮和圣祖继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如“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也”。三藩“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王其巩固封疆,殚抒筹策……功名永重山河。”【《八旗通志·耿继茂传》(初集),卷175,4283页。】要三藩镇守南疆,“屏藩王室”。这就是说,永不撤藩,子子孙孙世袭王爵,与清朝相始终。这些诺言和盟誓,都写入赐封的金册之中。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依人们的愿望为转移,当诺言与实际利益相冲突时,信誓旦旦的诺言,写进金册里的盟约,都会被撕得粉碎!
其二,将吴、耿、尚三王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把兵权收回。此法颇类“杯酒释兵权”。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前代(唐)藩镇之祸,采取释其兵权之法,于宴会上将握重兵的将帅之兵权收归己有,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逐除前代之祸,君臣相安无事。此即“杯酒释兵权”,成为千古美谈。诚然,历史不能照搬,但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足以作为借鉴;
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逐个解决,如兵法上说的,各个击破;
其四,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
其五,不急于撤藩,即使尚可喜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例如,等待尚可喜、吴三桂及其属下老一辈去世,留至第二代掌权时,可趁他们年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可行性。圣祖采取了第四方案,即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而多数阁臣主张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比较而言,实行这一方案较为得策。因为尚可喜主动提出撤藩,确是出于诚意,吴、耿要求撤藩实非己愿。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冷静、慎重地制定一项稳妥的政策。圣祖急于撤藩,欲毕其功于一役,根本没考虑到吴、耿在被迫的情况下撤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大多数廷臣对撤吴藩已表示出顾虑重重。他们为什么坚持不同意撤吴藩?正如他们已向圣祖所表示的见解,他们考虑到云南虽然平定,但那里的情况复杂,潜伏着一定危险,如吴藩一撤,局势不稳,担心会出现反复。要说三桂图谋不轨,还没有抓到谋反的证据,朝廷无法说出口,以他对清朝的特殊功绩,贸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三桂早已交通朝中诸臣,关系密切,他们是同情他的。在他们心中还有一层隐忧:“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权重”【《庭闻录》,卷4,12页。】,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三桂之下,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骚动。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剪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圣祖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昭梿:《啸亭杂录》,“论三逆”,卷1,3页;参见《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
他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例如,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未叛,矢志忠于朝廷,这对圣祖的不实之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圣祖同阁臣们的秘密谈话,表明一个有见识的满族统治者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畏惧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三藩“必反论”来吓唬反对撤藩的廷臣,并为自己的撤藩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终于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吴三桂估计朝廷一定会挽留他,同尚、耿两藩有所区别。这个估计没有大错,因为事实上正如三桂所预料的那样,多数廷臣是不同意撤吴藩的,他们的意见能够左右圣祖,不致做出违背他的愿望的事。但是,他却低估了年轻的圣祖判断问题的能力、不受任何人摆布的自行其是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圣祖真撤,结果弄假成真,木已成舟,已经无法挽回!
四、撤藩逼反
圣祖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他热切期待朝廷命他世守云南的希望,转瞬之间,已化为泡影!他只觉得当头一棒,昏昏然;又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精神沮丧,真是一落千丈!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后悔何及!君命是无法抗违的,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同家属和官兵全部撤离云南,重新回到他锦绣前程和人生的起点——山海关外的锦州,到了那里,他将失去一切权利,除了保留平西王爵位,不再参与国家政务,无所事事,只能掌管自己的庄田,安闲度日,从此,他将由一个权势显赫的王爷,威震一方的大将军,变成一个无权无威的“富家翁”。他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好像置身于荒漠无际、人迹难至的空旷之区,孤独、寂寞将伴随着他了此残生。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
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该怎么办?抗拒吗?要落得个叛逆的罪名,他不愿意轻易自毁数十年血战挣得的荣誉;服从吗?他将失去已得的一切,他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想得很多很多,可是,他又感到自己无力去改变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海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做出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
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很乐意引退,如果他在名利场上已感厌倦,情愿“息肩”,退居水边林下,纵情于大自然的乐趣之中,那么,他就会接受和执行圣祖的撤藩决定,这一切问题自然都不会产生,烦恼也无从而来,历史就会朝着和谐、“善”的方面发展。然而,强烈的权势欲驱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最使他思想受到震动的是,他感到清朝欺骗了他,撕毁了所有的承诺,把已给他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收了回去,这怎能使他心甘情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他抗拒朝廷背信弃义的撤藩决定。可是,他怎样才能自卫,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在撤与不撤之间,他徘徊不定,犹豫不决;在他与朝廷之间的这杆历史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激烈地摇摆起来,他力图控制住自己,却不时地出现失控。他无可奈何……
且不说撤藩引起吴三桂如何震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就说他的属下,当撤藩令一下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庭闻录》,卷4,14页。】他们在为三桂鸣不平,同时,也为他们个人将失去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益痛心疾首。他们跟随三桂多年,早把自己的命运同三桂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荣皆荣,一损皆损。这批人,都与三桂有着血缘的或虽非血缘、彼此却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构成了以吴三桂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吴三枚,三桂的从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探凡胠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吴应期,三桂的侄儿,骁勇善战,官至都统,是三桂的得力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