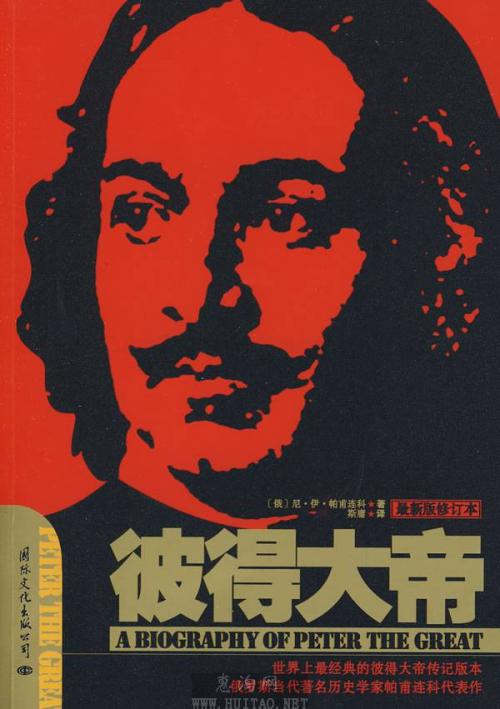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李吃坏了东西晚上起来拉肚子,一共拉了二十几回。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跟我和爸爸抱怨,说他把外面的水泥地都给搞脏了,爸爸听了赶紧送他到医院,不久他就过世了。他过世后我伤心得如丧考妣,我写了一篇作文悼念他,文字中披露出对母亲的无情的强烈不满。同一年爸爸到彭伯伯家里打麻将,打到一半时他去上厕所,三十多分钟都没出来,那位戴着千度近视眼镜的杨委员不耐烦了,要我进去看一看。我走进浴室发现爸爸倒在地上,身旁有一大摊血,眼镜掉落在地面,镜片全都碎了。我惊恐地跑出来告诉那些三缺一的委员们:“爸爸吐血了!爸爸吐血了!”大伙儿赶忙叫救护车,抬了担架准备送父亲去医院,正在慌乱的时候,杨委员的眯眯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瞄了我一下,十分不耐烦地说:“赶紧把他弄走吧!我们还要打牌呢!”我当时听了不禁在心底暗自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脱离这个圈子,而且永远不碰麻将这个鬼东西。老李过世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再也没人为我做饭了,只好到母亲打牌的高家,坐在牌桌底下等饭吃。晚上我一个人不敢待在家里,总要等到十一二点母亲打完牌后再一道回家睡觉。
小学毕业后参加初中联考,因为数理成绩太差一个学校也没考上。爸爸只好带我到台北,动用了所有关系,希望能帮我挤进一所私立中学。没想到卫理女中招考时的数学题目我竟然都能解答,其他科目也都答得不错,故而顺利进入了这所以生活教育著称的基督教住宿女校。
干爹陈公亮先生与干妈郑真女士。
在卫理这所环境整洁幽僻、充满宗教气息的女校里, 一住就是六年。
以崇拜的眼神看着发福的爸爸。
十五岁在台北荣星花园留影。
十五岁时与台湾中影基本演员林玑合影。
念大一时与学长陈立恒合唱民谣,那时学校里唱西洋民谣的风气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