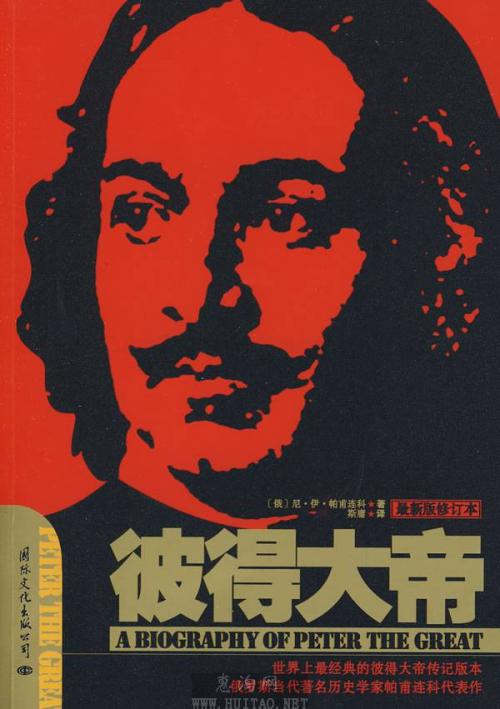其实没进卫理之前基督教对我而言已经不陌生了。小时候存信巷口就有间基督教的聚会所,我为了得到耶稣抱着小绵羊的卡片,被里面职事的牧师相中,邀我加入教会的唱诗班。卡片上的耶稣虽然只是西方宗教组织想象中的至人,但那张俊秀悲悯的脸孔,却成了我日后意识中最重要的原型之一。西方宗教的各种仪式也都能令我产生“大事即将降临,正该做些准备”的神圣感。
圣诞晚会和沿门报佳音是卫理学生最爱的庆祝活动。圣诞节前后,一楼的行政大楼、宿舍的大厅和礼堂,到处都是彩饰的圣诞树,有时还会搭起一座马槽,里面有圣母、圣婴以及西方三圣的塑像。平日里每逢周五,学校都会邀请牧师、学者与专家为学生们阐述神的道理与人的道理。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中,教官和训导主任不时地站起来一排排地巡逻,看看“点头族”有没有动静。所谓的“点头族”就是每逢听道、听训便自动进入酣睡状态的学生。平日里很难沉睡的我,只要一听见教条式的训诫,就困得连眼皮都睁不开了,下巴也松了,有时支撑脑袋的手臂因失去知觉而突然滑落,“点头族”差点没成了“磕头族”。台上的讲者如果欠缺自知之明,说不定还以为台下起了最强烈的共鸣呢。
二十七岁之后我开始“疯狂寻道”,时常参加各种法会,我发现坐在身边的母亲和念中学时的我反应完全相同,她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坐在法师或仁波切的身边有一种天下太平的感觉,于是平日里需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的她,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进入了无意识状态。对我而言道德训诫和数学公式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它只能令我昏睡,无法使我觉醒。女校里的学生很少有人会去思索神学问题,大伙儿被一一团一 祥和的宗教气息笼罩着,自然而然地落入各种宗教信念的制约里。我从信仰进入自我探索历经了漫长的转化过程,日后因某些人生的危机才有了真正深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