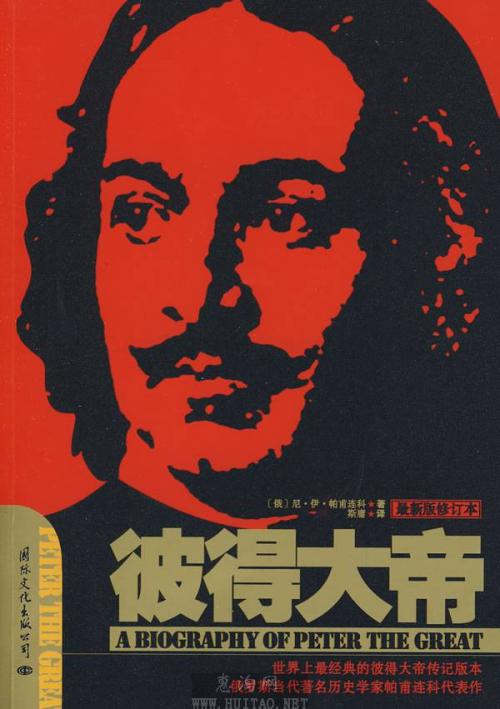父亲搬出去和他真正相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每个月的薪水悉数一交一 给母亲作为家用,我从此算是真的和母亲相依为命了。就在这段时间,我向数学家教欧陽狮老师透露我想自一杀的念头。老师大为惊讶,不解为何一名念初中的少女竟然有轻生的念头。他开导了我半天,我只说人生太苦,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
从那时起我每到日落黄昏都有一股活不下去的感觉,那不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还包含了生理上的感觉。我的大家庭人际失和,现在连小家庭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当时我的心态突然起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书读得再好都没有人与人的联结来得重要,于是开始热衷于课外活动,充当起班上合唱一团一 的指挥,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为班上的同学说书。
同学似乎很喜欢听我说话,于是我就“下回分晓、下回分晓”地一路讲个没停。一个学期下来我的人缘已经完全改观,但功课却一落千丈。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什么“十项全能”,根本是母亲口里的“十不全”——照顾到这边,一定忘了那边,注意到内在,一定忽略外在。所幸我不是一个求全之人,日子也就这么偏颇地过了,后来接触到灵修和宗教,才明白原来只有解脱的智者方能无漏。
这段时间我开始出现一些意识上的特异现象。某个周末我和几位同学结伴到西门町看电一影 ,大家走了几条街,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正在等红绿灯时,我突然进入一种“大忘”的状态,我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要往哪里去,也忘了为什么站在十字路口。我傻傻地跟在同学的身后走了好几条街,才想起自己是谁。
那次的经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想也许是累了或闪神了。后来上大一时,有一回坐在男同学的摩托车后,也突然兴起“我是谁”的大疑问。平日瞥见镜子里的自己,感觉竟然很陌生,有一种“我不是我”的疑惑,像这一类的现象,都是促使我寻道和找寻自己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一回和母亲到西门町看电一影 ,两个人在簇拥的人潮中往前推进时,我注意到前方有一名工人正准备钉广告看板,这时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看板可能会掉下来。当我们经过时看板真的掉了下来,铁皮的尖角戳到母亲的上唇,刺了一个九十度的小口子,肉立刻翻了起来,而且鲜血直流。这时我发现自己竟然气得浑身发抖,把那名不小心的工人臭骂了一顿,母亲反倒心软了,直说没关系,一点小伤罢了。我自然流露出的那份骨肉之情令她有点受一宠一 若惊,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是好,表情显得有些尴尬。那次的经验令我意识到我们母女在日积月累的障碍之下,仍然深深渴望着彼此的关爱。
打从父亲走后,母亲收拾起怨恨自怜的心情,把平日里挽成髻的长发剪掉,烫了一头时髦的短发,每周仍然和她的牌搭子聚在一起玩麻将。我对这玩意儿始终没什么好感,学也学不来,不过年长了些,倒希望母亲每天能有点事做,也好多给我一点空间与时间。
我们和干爹全家仍然时常往来,干爹还是那么疼我,一见面就塞给我一件小古玩、小器物,干妈也总想着把一些好看的围巾和饰品留下来送我穿戴。干爹时常邀我们母女到戏园子看京剧,旁观上一代的人对京剧的反应也是一场文化震撼,从其中你可以清楚地嗅到中国人对安全感的渴望。一出出重复再三的戏码演了不知多少回了,观众仍然感动得落泪、叫好;电视里的连续剧也一样,十年前的戏和十年后的戏不但剧情雷同,连服装都还是那几套。未知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一直不大,能预料、能掌握的才可以放心地被感动。只见台下的人对台上的人所要唱出或道出的下一句台词皆已耳熟能详,他们随着一胡一 琴的节奏跟着哼哼,那股志得意满的模样令我差点又禁不住要笑场。
其实台下的戏比台上的戏一精一彩多了。从这个外省人最重要的社一交一 活动中,你可以窥见许多陈腐而有趣的人性,至于台上的演出,在我的眼底根本是一出出的荒谬剧,什么王宝钏苦守寒窑,什么忠孝节义的,再鸡猫子喊叫的情节,总脱不了在锣鼓喧天之下以一句草率的“也就是了”圆满收场。我喜欢嘲笑母亲最爱的余兴节目,她则反讽我们下一代的人没文化,不像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