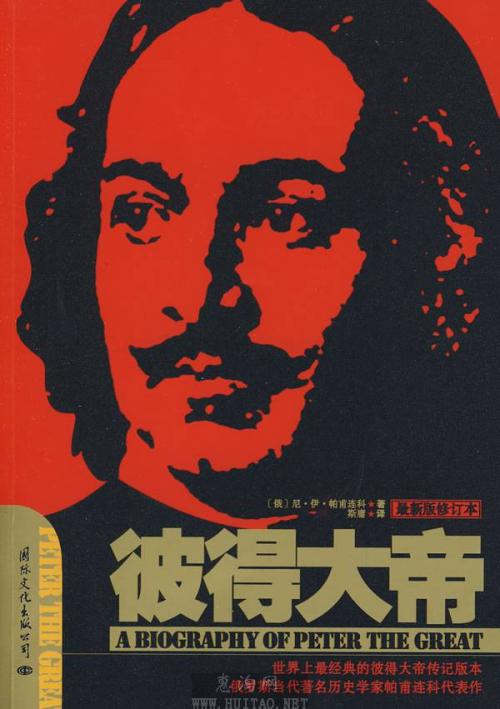升高中后班上有好几位老师颇受同学的欢迎,譬如教生物的许翠英老师,教理化的史老太,教数学的王右钧老师,以及从香港来的一位教国文的女老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的绰号是板鸭),另外还有一对教英文的美国年轻夫妇mr. -and-mrs.anderson 。
许翠英老师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她对各种生物的兴趣和喜爱可以从她的言语中清楚地得知,同学们受到了感染,上课都很专心,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心专注得连外面的噪音都听不见了。她有时带我们出校门去外双溪附近勘察自然,我们怀着“出埃及记”的心情跟在她身后,其实我们真正的兴趣还是校外的小杂货铺。大家火速地钻进去买话梅、橄榄,吃不完的就放在太空衣的帽子里私运回宿舍继续享用。我们对许老师的通融都十分感激。
教理化的史老太是道地的北平人,一口京片子在假牙的开合中夹杂着怪异的嘶声,她的幽默神似《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同学们喜欢逗她,寻她开心。如果理化不及格,到她的房里和她磨蹭一阵子,六十分通常有望。有一回上课时她旗袍里的老式底裤松了,突然脱落在脚背,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从香港来的那位国文老师特别喜欢我的作文,她当时受“左”派思潮的影响,言论里经常流露出社会主义和宗教的人道关怀。我因为家中有母曾嫁过共产一党一 员,在她的启蒙之下开始阅读起托尔斯泰和鲁迅,或许是这个缘故,我的作文总能博得老师“冰雪聪明”或“兰心蕙质”之类的评语。在个人信心的建立上这位老师带给我不小的帮助,后来有人从她的床 底搜出了《毛-语录》之类的书籍,因而被冠上“匪谍”的帽子,自此幽囚受辱。解严之前国民一党一 对人权和人心的钳制从这位老师的遭遇可见一斑。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厚厚的镜片和嘴唇、瘦长平板的身材、齐耳的老革命头和陰丹士林的长旗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mr.-and-mrs.anderson 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年轻夫妇,他和她的教学方式都颇为开明。安德森先生喜欢在视听教室里播放披头士(the beatles )的歌曲给我们听,有时也以自一由 联想的形式和我们探索神学。我记得某一天他要我们在纸上随意绘出自己潜意识里的神性。我当时画的是两座山,中间有道桥,他要我站起来说明其中的含意,我告诉大家我愿意做一道桥联结人的国度与神的国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其实那么早我的潜意识已经知道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了,但这份愿望的彻底实现却历经了漫长的二十几载。
王右钧先生是我从小到大最有缘的数学老师,他的教学灵活,令数学智障都得到了启蒙,只可惜我虽然与他有缘,却始终与数学无缘,最后要不是他放水,我高三可能毕不了业,还有好几位同学也都是同样的情况。
从高三开始我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的世界里,我花许多课外时间阅读国外的报章杂志及翻译作品,譬如time 、life 、newsweek 、national geographic 、vogue ,以及泰戈尔的诗集、屠格涅夫的小说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那时乌托邦的思想在我的心中逐渐萌芽,每节下课的休息时间,我和最要好的同学王建梅(目前是博达版权公司的负责人)一同搭档演出lennon-and- mccartney 。老王长得真像列侬(john lennon), 后来又加入了低几届的李敏,而她长得也十分酷似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 ),三个人背了数十首披头士的畅销金曲,每节下课凑在一起高歌,旁边总是有一群同学围观。
那时有一个全球性的集体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它是绿色的、和平的、反物质文明的、超验的、个人主义的、存在主义的、寻求解脱与兄弟爱的。它横贯东西,纵贯古今,它从宇宙的神经系统出发传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也传至我的神经中枢,我整个人突然从有一搭没一搭的状态醒了过来。
我看着woodstock 演唱会的画面,看着那密密麻麻、赤身裸一体、满身是泥泞的人潮: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头戴鲜花,满坑满谷坐了一地。我知道他们正在反叛——反叛传统的束缚,反叛文化的制约;我知道他们想要打破——打破昏睡的状态,打破孤立的幻觉。我这名生长在东方某个岛屿的十六岁少女对于他们所进行的同谋,就这么理所当然地懂了。我仿佛不再孤单,我透过媒体和这个全球性的运动接上轨了。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时的嬉皮士运动仅仅是一种方兴未艾的蠢动,后来它又逐渐演变成了更深刻的集体意识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