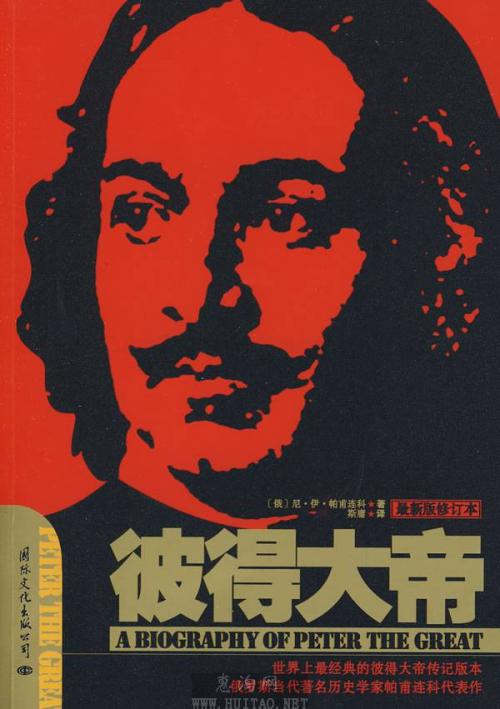从纽约回到台湾,我发现《云深不知处》带给观众和媒体的印象仍然留有余一温一 ,一年前结识的某些新闻界友人又重新回头来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纽约的种种经历。我当时早已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中国娃娃头,额前的刘海儿垂挂在看起来相当自然的双眼皮上,新闻界的老大哥宇业荧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还是比较喜欢单眼皮的我,另外有些艺文界的友人也怀念我以前的东方古典美。我发现凡是对我说真话的朋友多半能维持比较长久的情谊。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似乎助长了当年台湾服装界的中国热,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深化,我愈来愈清楚中国风就是最适合我的风格,不需要再追随已经技穷的西方设计师们一季一季地跟着一团一 一团一 转,把宝贵的能量消耗在物化而低自尊的向外驰求。 此外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上的除旧布新罢了,心态如果老旧陈腐,穿得再时髦也毫无新意。
中影公司从群众的反应嗅到了我的潜力,决定和我签订基本演员合约。说实话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的演员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导演、编剧都是半摸索半凭直觉地运转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凡事讲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湾的电一影 从业员可以算是天才了,因为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占整个东南亚市场。就创意而言编剧是所有电一影 从业员中真正的创意人,演员和导演严格讲起来都是诠释者。然而当时的编剧人才十分匮乏,除了张永祥之外就属琼瑶的作品最有销路了,其后果是每部片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剧中人的对白与独白听起来总是似曾相识,连幕后的配音员都是相同的那两三个人。
导演群中除了老一辈的李翰祥、一胡一 金铨、白景瑞、李行、宋存寿之外,应该数刘家昌的产量最丰,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刘疯子”。刘疯子走路快、动作快、思考快,国骂出笼的速度也快;像一场台风似的,他把全组的工作人员吹得七零八落。他要求自己要做个省时、省钱、省人力的导演,因此而创下了三天拍完一部电一影 的惊人纪录。他片中的演员从这部戏的客厅跑进了另一部戏的饭厅,接着又都挤进了咖啡厅。片尾他通常用蒙太奇手法让男女主角漫步于白浪滚滚的沙滩,配上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终结了一部又一部的“三厅电一影 ”。
刘疯子到今天都是我的好友,他真是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类。别人口出秽言总给人负面的感觉,然而他的“六言绝句”即使吐了一百回,你还是觉得童言无忌。他的性格愤世嫉俗,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无论怎样折腾,总能维持住吓人的排场。他看似不忠不孝,可每逢紧要关头,却出落得“忠一党一 爱国”。他的情绪永远写在脸上,他的计划永远挂在嘴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幼稚,因为连最精明的商人也臣服于他的魅力之下。当然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简单结论,人性的复杂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演员群中有许多高能量的、不吝于展现自我的人,真正吸引我注意的通常还是内敛型的人,其中以郎雄最能引起我谈话的兴趣。虽然合作的机会不多,但我总觉得心灵有些方向是相似的。演艺人员虽然不是个个胸中有墨,却很少有愚钝之人。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也许智识上的收获并不多,但情感和情绪的一交一 流往往是通畅无阻的,视觉上的享受也很充足。当时有许多明星都是“摄影机偏爱的演员”——他们的骨骼构造、脸上的肌肉、身材的比例、肤色与肤质、情绪的展露和身体语言,都能带给观众一份美感和吸引力。国外也有许多这类个人魅力型的演员,他们多半能成为超级巨星,虽然他们在每部戏中展现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剧中人。
客观地比较之下,我早已认清自己是“摄影机不爱的演员”——我的脸不是“巴掌大的小脸”(这是非常关键的上镜条件),体重则必须维持在四十五公斤左右,脸部在镜头上才能呈现出美感。此外我的气质带着几分冷艳,身材却不够女人,然而我对自己不满意的程度还不到需要丰臀隆乳的地步,所以演出的尽是一些非玉女非艳一星 的尴尬角色,譬如《梅花》中跳海自一杀的女老师、《笕桥英烈传》中高志航跳河自一杀的贤妻、《花非花》中特立独行的舞女、《跟我说爱我》中的叛逆女画家、《酒色财气》里偷汉子的老兵之妻、《借一尸一还魂》中的女鬼、《六朝怪谈》中与白马做一愛的少女等等。
我在准备这些角色的时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当天才拿到剧本,甚至没剧本就开拍的情况也有。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刻画只有简单的交代,导演运镜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联短镜头,因此演员在演出时情绪动不动就被切断。通常是走几步路到达定点,回过头来转成最上镜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独白的内心戏。每当演员需要和伙伴演出对手戏时,往往由副导演伸出拳头来顶替,因为他或她上厕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论是哭、是笑、是说,还是默然无语,面对的经常是一只拳头。
当时流行的爱国战争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经常会运用到特技,演员在土法炼钢的爆破技术和高来高去的吊钢丝中饱经忧患。我曾经把《七月幽灵》这部片子里的惊险爆破过程写成杂文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中。当时负责的技一师是一名退伍下来的军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闻这位仁兄在《八百壮士》的拍摄过程里炸死了几名充当临时演员的士兵,所以在每个跟火药有关的镜头开拍前,都会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咛一番。
只见导演一声令下,我和石峰就开始拼了命地连跑带跳,在我们飞跃过土堆的那一刻,炸药果然被引爆,威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大。智者常说:你恐惧什么,就必定会发生什么,但中镖的不是我而是企图保护我的石峰。只见他的西装裤上布满了小小的孔洞,当他把裤子掀起时发现腿上起码有十几处伤口,都是被炸药轰得四处乱窜的小石子击中的。当时的演员碰到这类问题通常很难获得赔偿,李涛的前妻张海伦在泰国拍戏时整只手都被炸掉,后来自一杀身亡了。像这类的不幸事件在这个工作领域里是层出不穷的。
另外有一回在澎湖的望安岛拍摄《六朝怪谈》的外景,这部片子的导演王菊金说服了几位艺文界的友人客串演出。片子的构想不差,工作人员和演员的组合也不俗,唯独经费有限,必须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拍摄。剧情取材自魏晋南北朝的传奇,总共分成三个部分,调子采用日本怪谈的模式,我负责演出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女主角小茵和她的宠物白马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竟然到达以身相许的地步。原来白马不是禽一兽 而是有灵之物,深夜里它化身为一名书生和小茵完成了男女大事。家里的长辈觉得人一兽 之间似乎有异,便自作主张宰掉了白马。白马的皮被剥了下来铺在院子里晒干,这时待嫁的小茵前来看它最后一眼,没想到马皮竟然飞扬起来将小茵重重裹住,悬在树梢结了一个茧。这个故事叙述的就是茧的由来。
如同其他影片的拍摄过程,《六朝怪谈》也需要克服各种人事问题、技术问题与沟通问题,工作人员和导演相处得并不愉快。我记得为了拍摄马皮飞起来裹住小茵的画面,导演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由女主角裹着马皮自行转圈子,再以摄影机的高速镜头呈现快速旋转的效果。我全身裹在马皮里,两只手臂完全不能动弹,两脚既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旋转,又要维持住身体的稳定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转了没多久就出事了。我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笔直地倒在地面,头部刚好撞到一块石头,当场晕了过去。我晕过去的时候竟然进入了濒死经验——脑子里快速地浮现一连串的人生倒带镜头,每个镜头似乎都在与人争吵,我想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咽了气,神识一定会奔往内在次元的修罗道。结果那一个“为艺术牺牲”的镜头在银幕上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借一尸一还魂》叙述的是台湾民间的一则鬼事再添加一些编导的想象,我饰演的是被鬼魂占据肉身的女主角。我记得这部戏拍摄的时间是十一月左右,当时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但是为了赶工,仍旧得熬夜到清晨。这部戏里有许多画面都需要杀生。导演为了制造血腥的场面,在剧本原有的架构之外又添加了许多杀鸡、杀鸭、杀鹅与杀蛇的镜头,甚至还准备杀猪。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着半透明的白色纱质长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举着菜刀,跟在一群白鹅的身后,做出杀红了眼的表情。我那时和李敖刚刚离婚,正在打官司的阶段,心里已经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无意义、如此令人作呕的戏,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几天之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导演说虽然我不必亲手杀生,但拍电一影 有许多取巧的技术,并不需要草菅任何生灵,如果还要继续拍这类镜头我就宣布罢工。
当时的合约大都是一面倒向资方的,我喊罢工其实要赔上一大笔钱,然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一部大烂戏在电一影 院顶多上映几天就下片了,值得这样杀杀砍砍吗?后来导演权衡轻重之后决定不再添加杀生的镜头,于是保住了几头猪的命,虽然那几头猪最终还是会变成一人 类五脏庙里的祭品。此戏上演时树诚兄去看了,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在这部影片里我把那名充满怨气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诉他当时我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怨气冲天。
几年后在香港和一群宝贝蛋演出《大笨贼》这部戏,男主角是许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场戏里许冠文幻想自己是骑着一匹白马的王子,我则是坐在他身后的公主。我们两人骑着马正有说有笑时,马儿突然受惊而扬起了前蹄。许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顺着马屁一股四脚朝天地摔在地面,许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躯体配上重力加速度整个摔在我身上,当场我就动弹不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忙请来一位跌打名医,这位广东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药贴在我尾椎部位,一个钟头之后我才能站起来走动,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台湾,第三天又赶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轻的跌打师父替我推拿了一个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从此之后右半边身体经常隐隐作痛,直到三十多岁遇见一位气功高人——唐师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积物,疼痛才痊愈的。结果那个再度“为艺术牺牲”的镜头连一秒钟都没出现,原来整段都被导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从影历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我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跟受制于拥有及物化观的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也较有能力处理现代女性的省思与成长。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去酝酿我所饰演的钢琴家角色,同时还为我请了两位恶补演奏技法的老师,一位是尚未出道时的黄韵玲,另一位则是“胖子”范宗沛(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电一影 配乐师了)。他们协助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复再三地模拟肖邦练一习一 曲《冬风》中的一段。对于几乎完全不会弹钢琴的我而言,这真是一项艰涩的挑战,然而两位小老师的功力很高,后来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颇具说服力。此外这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一影 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发音一向称得上标准,拍摄时又有老师指导,最后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德文对白也颇有说服力。整体来说,这部电一影 终于让我尝到了专业和自重的滋味。
当时台湾的电一影 工业在几位新锐导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我记得我们在中影看毛一片时孝贤正在剪接《风柜来的人》,老杨看到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画面,禁不住兴奋地大喊:“你敢这样搞啊!那我也要这样搞!”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因大胆忠于自己所流露的快意,心里生起了一股悸动,湿霉的空气中似乎飘拂起了宜人的熏风。那一刻我才开始深自反省,其实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暗自嘲笑对白的荒唐和肤浅;那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应。我在这个领域里占了十年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到底贡献了什么?我能为我的演艺伙伴们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正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