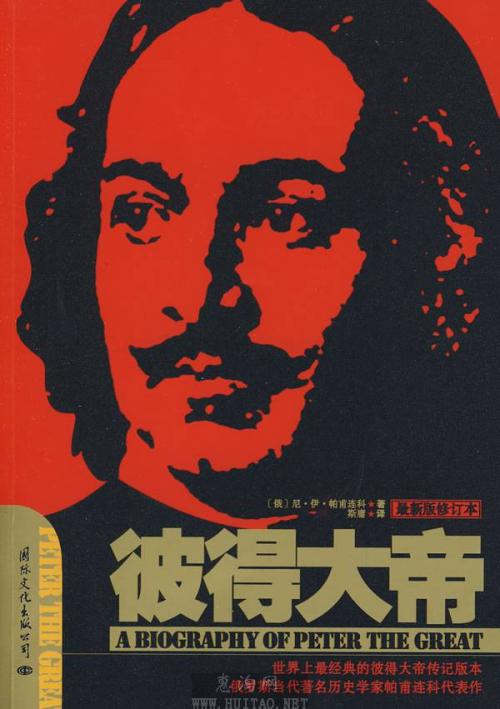在这段期间我开始思索演员的深度定义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演员在社会形象上和人类内心里都承载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种种投射。他既是人人羡慕的名利典范和过度被注目的焦点,又是轻易被藐视和嘲弄的对象,即便是最杰出的演员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赤裸地站在媒体白纸黑字的布阵中,时而被槍林弹雨轰得遍体鳞伤,时而受一宠一 若惊地登上了天;他似乎是拥有最多群众力量的人,又似乎是毫无权力或重要性的局外人。他总是在政客与财阀主办的晚会里饰演募款的甘草角色,即使在大银幕或小荧光幕上他也只是一个媒介,一个传达他人的人生观的工具,那么,演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人类学者和心理学家回答得最深入。
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是以萨满或巫的形式展现的,那时他的功能乃是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是最早期的歌者、智者、舞者、文化传递者、占卜者、医者和人生顾问。他透过宗教仪式来治疗和转移人们心中的恐惧及困惑,甚至直接成为无形能量的管道,展现出神力;譬如日本能剧、印尼及西藏的仪式舞蹈,都存在着这样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曾经拥有过神权以及崇高的地位,东西方皆是如此。但自从西方正统基督教会兴起后,巫的传统就被逐渐贬为异端,人神中介的角色开始由牧师取而代之,演员的崇高地位从此沦为娱乐他人的艺匠。在东方世界里,演员也逐渐沦为戏子、俳优,以及卖一婬一、无情和伪善的象征。
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似乎达到了心智与情感之间的整合及平衡,因此能展现出高等形态的理解力与流畅无阻的情绪表达。当我仔细反观自己时,我发现十五年来的演艺工作,我的焦点竟然不是情绪与情感上的表达,而是智力活动。我在拍戏时手上几乎永远有一本书相伴,内容不外是哲学、心理学、玄学或宗教。戏剧中的演出似乎并不是我心中的重点,知性活动反而是我所热衷的。乌塔·哈根曾经说过:“一个知性的演员可能将真实的演出冲动过分理性化。”很显然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演员。我发现自己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或荧光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而且我关心理论和形上思维远远超过戏剧上的表现。当我开始清楚自己的特质和潜力时,心中最深的召唤就变得清晰可闻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投入于智慧的探索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于是我告诉老母从此之后我不再为金钱工作,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