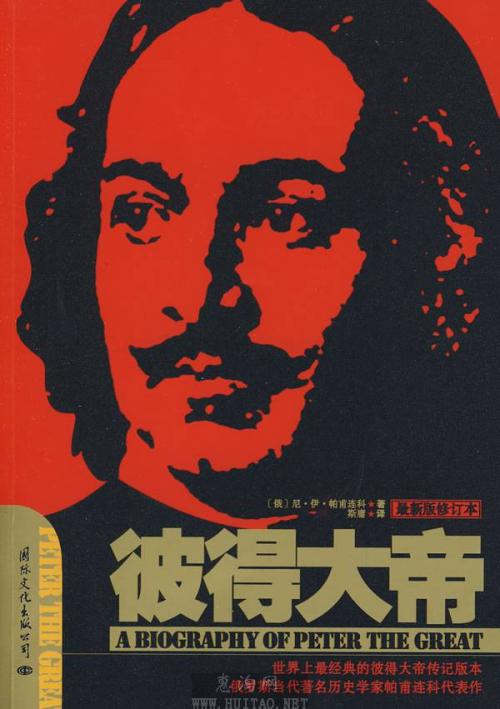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b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又心疼起这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突然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二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该拿出二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门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厅里,由《中国时报》主编高信疆和作家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礼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至于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录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必须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还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了。婚礼结束后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午饭,饭后回到金兰大厦,没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喝,嘴里还得意扬扬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精神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这“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赔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只能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一胡一 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后来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跟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当时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讲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连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见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萧先生回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请了出去,向老母告知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都被搬空了,天母静庐也换到了一胡一 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一交一 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一交一 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的。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他。剑芬接着说道,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英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了谱。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动机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太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智慧罪犯”。于是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给送李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一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兰去住了。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斌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一交一 ,他的妻子孙春华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脱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一交一 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续。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一交一 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这时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地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砸过去的时候,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闪了腰。两个人就这样闹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猛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宵夜(已经成了早餐),这时李敖突然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生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起来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一交一 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明,立刻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如果我不能马上回李敖一份书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内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分钟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明。那张纸我没有保留下来,只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从此不再遇见“试探”。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离婚协议书。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传达出来的讯息还是有情感的,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与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回到金兰不久便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他说他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一边,好好地安静一阵子再做决定。我一边落泪,一边满心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恐怕很难再密合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立刻对我说:“静庐的所有权状在我手里,你在法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罪,律师有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一切一交一 由律师处理,不久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必要的,人一怠忽危机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