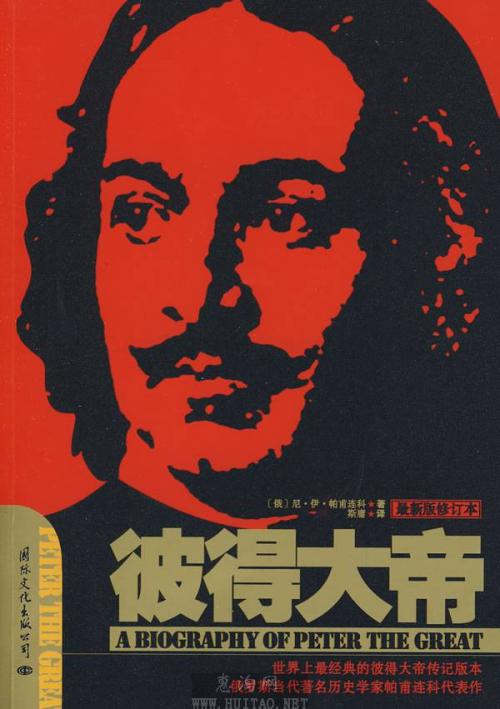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与他此生最有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么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内心并没有难以承担的挂碍;母亲对这位第三者始终无法释怀,她不愿意我经常探望父亲,如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她也有微词。我对这位第三者抱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华阿姨是位经营餐馆业多年的一江一 南女性,独立豪迈之中带有双鱼族牺牲奉献的倾向。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实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的是母性的滋养、呵护与一宠一 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那份深切的渴望若是没获得满足,他是很难在这个世界正常运作的。华阿姨扮演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与再生母亲。每次我看到他们互动的模式,都会暗自生起对人类心理创伤的感叹。父亲和华阿姨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便瘫痪在床 上不愿意动弹。我用“不愿意”这几个字,是因为你不难洞悉他想重拾襁褓阶段被命运剥夺的母爱。他拒绝下床 走动,他不肯好好地吃饭、上厕所、洗澡,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华阿姨一手包办。华阿姨是一贯道的信徒,她喂父亲素食,规定父亲念《金刚经》和《地藏经》回向给冤死的祖母。父亲一不高兴就像恃一宠一 而骄的逆子,用他的断掌打华阿姨或是拧她的大腿。华阿姨全盘承受了,因为她了解他的需求,也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对这样的一位第三者,我还能有意见吗? 一九八八年底我从纽约回台湾后,父亲的健康数度危急。我去医院看他,华阿姨在一旁落泪,她告诉我父亲在危急时嘴里总是念着我的名字。虚弱无语的他,直觉仍然相当敏锐,我的心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满头的银发和光滑的皮肤,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九八九年陰历三月初十是父亲虚岁八十五岁的生日,三月初八则是我的生日。春仲,在我们的生日还未来临之前,某一天夜里我接到华阿姨打来的电话,她要我赶紧到她们家,她说父亲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赶到她的住所,进入卧室,坐在父亲的床 边,握着他余一温一 犹存的双手,在泪眼模糊中安静地端详着他的宝相。感觉上他的神识还没离开那个空间,大概是在等待我的出现吧!我心里暗自思忖:他早就准备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世;沉重的情债终于还完了。
我的释怀多于哀恸,回到家里我把父亲的死讯告知老母,老母用高度的意志力压下了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半夜里从她的房间传来了断断续续类似梦呓的咒骂,我从床 上爬起来有点不安地走进她的卧房。她矮小的身躯在超大的床 上缩成了胎儿形状,整个人不能控制地颤抖着,僵硬干涩的嘴里不停地咒骂:“你这个老鬼……你总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长……我赢了……”我没有干预她的宣泄,默默地把门带上,心里怀着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独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举行告别式的那一天,与父亲有一交一 情的老委员及友人络绎地进入第二殡仪馆的景行厅吊祭父亲的遗容。母亲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念祭文的专人以职业化的哭调唱诵着父亲的生平事迹。他在呜呼哀哉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一连串的歌功颂德——父亲三十多年没有开口质询被他粉饰成谠论留徽,母亲三十多年的麻将生涯被他改写成相夫教子。母亲耐着性子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一派一胡一 言!”我看着这场与事实大异其趣的荒谬剧,儿时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浑身颤抖地暗笑不已,母亲竟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长跪于地,悲剧演着演着又成了喜剧。还好我们动作不大,只有干哥哥小龙发现了我们反常的举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龙强掩着脸上的笑意走到我们母女身边,歪着嘴低声对我们说:“稳着点,太不像话了。”接下来老委员们在父亲的棺木上覆盖一党一 旗,以隆重的葬礼替父亲盖棺论定。据说是否应该覆盖一党一 旗,委员们曾经有番争论。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亲只恨不得快点回到灵界喘口气,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浓妆的皮囊上是否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男性总是借着一党一 国来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连自知之明都谈不上,还能谈宏观的国家民族吗?事实是,自知之明远比立国平天下难得多。大题目总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却是一种把面子掀掉的举动。我心里正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突然颈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颈子?这件事太离奇了,于是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一胡一 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人生无数场的悲喜剧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上演。说老实话,我赞同希腊左巴对死亡的乐观态度,葬礼应该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反省一下,换一副身体再来。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试着揣摩父亲的意思,决定把这笔钱一交一 给华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出乎我意料之外母亲竟然答应了,但是她主张先把钱汇进我们的银行,一周后再转入华阿姨的账户。一周之后我询问母亲是否已经转账,她的脸色突然一变,表情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家庭的女人?”我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一股巨大无边的怒火攻上我的心头,我把老母压在沙发的一角,开始一泻千里地对她大声训斥。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接着我开始指出她人生观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说:“你的气焰凭什么那么高?你一生都在麻将桌上,毫无建树地混了一辈子,却总是骑在别人头上。如果你真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不出去找份工作,像华阿姨和潘阿姨那样?你以为自己的才分比这些女人高,我却觉得她们比你强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处处设限,让人家无法自在,无法快乐。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根本大错特错了,钱是解决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没有因为钱多就解决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我像训女儿一样足足骂了她一个小时,母亲一语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当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左边的颜面神经有点麻痹,照镜子一看才发现左半边脸已经眼歪嘴斜。洗脸时眼睛无法完全阖紧,水会流进眼里;刷牙时牙膏从嘴角流了出来;喝水时只能靠半边嘴唇小心翼翼地吸进去。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后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过,那不是太恶心了吗?老母趁火打劫地说:“你瞧,这就是不孝的现世报。”这句话唤醒了我正义之师的大梦,我发现如果以正义合理化内心的暴力,这股负面力量还是会依循因果定律反扑到自己身上。真实的正义之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怨恨;虚假的正义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亲不知自省的借口罢了。这样的双向观察使我免于再度落入愤怒的陷阱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找医生治疗这个怪病。
见了好几位西医,都说周边神经麻痹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复原了。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台中的中医,这位医师告诉我说这个病叫做“神经感冒”,针灸可以帮助它快点痊愈,即使完全不医治,一个月后也能不药而愈。我等了一个月,情况果然好转,不过完全恢复却是三年之后的事了。这件事让我体悟到克氏所说的,情绪能量必须在每个当下透过不谴责、不压抑的观察,将它完全燃烧、释放,如果一味地压抑和累积,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对人对己的重大伤害。我发现自己在处理情绪能量上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