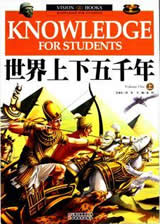他们慢慢地穿过奶牛场,走下土丘,到了珀金斯 老宅。宅子外面停了四五辆汽车。他的父亲敲动了门环。杰斯 能听到特里恩王子叫着从房子的紧里面冲向大门。
“嘘,特里恩王子,”杰斯 听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声音说,“趴下。”门打开了。开门的人正在弯腰去摸小狗的背。特里恩王子看到杰斯 就抓住机会,挣脱了束缚,高兴地跳到男孩的身上。杰斯 抱起了他,像特里恩王子还 是只小狗的时候他经常做的那样,抚摩着他的脖颈。
陌生男人脸上半露出奇怪的笑容,说:“我看他认识你,进来吧,好吗。”他后退一步站着,让这三个人进去。
他们走进那金色的房间。房间还 和以前一样,只是因为阳光从南面的窗户射了进来,显得更美了。杰斯 从未见过的四五个人坐在一边,低声说些什么,但大多数时间,根本不说话。没有坐的地方,那个陌生人从餐厅里搬来了几张椅子。这三个人不自然地坐下,等着,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一个年老妇女从长沙发上慢慢站起来,走向杰斯 的母亲。她的头发全白了,眼睛是红的。“我是莱斯 利的姥姥,”她说着,伸出了手。
他的母亲局促不安地握着她的手低声说:“阿伦斯 夫人,就在土丘上面。”
莱斯 利的姥姥握了他母亲的手,然后是他父亲的手。说:“谢谢你们来。”接着转向杰斯 ,说:“你一定是杰斯 。”杰斯 点点头。“莱斯 利——”她的眼睛里已满含泪水。“莱斯 利跟我说起过你。”
有一会,杰斯 感到她还 要说些什么。他不愿意朝着她看,所以让自己抚摩着特里恩王子,王子正横跨着趴在他的大腿上。“我很难过——”她控制不住了。“我受不了。”开门的那个男人走过来,抱住了她。在他把她带出这个房间的时候,杰斯 听到她在哭。
她走了,他感到高兴。像她那样的女人还 哭,有点奇怪。那好像是电视里谈到波利登特的那个女士突然哭了起来一样。这不相称。他看到房间里周围所有的成年人都哭红了眼。他想对他们说,看我,我就不哭。他身体的一部分退一步检查这个想法。他是他这样年龄的人中,惟一的一个知道自己最好的朋友死了的人。这使他变得很重要。学校里的孩子们,在星期一或许会在他周围低声说话,对他很尊重——就像去年,比利·乔·威姆斯 的父亲在汽车撞车中死了之后,他们对待比利那样。在他不愿意说话的时候,可以不必跟任何人说话,所有的老师都会对他特别好。甚至妈妈也会使他的姐妹对他好。
他突然想去看莱斯 利入殓的情况。他想知道她是在后面的书房里,还 是在米尔斯 堡的一个殡仪馆里。他们会让她穿着蓝牛仔裤下葬吗?或者,让她穿复活节那天穿的女学生裙和有花的短外衣。穿这套衣服好。穿蓝牛仔裤,别人会讥笑的。他不愿意让任何人在莱斯 利死后还 嗤笑她。
比尔到房间里来了。特里恩王子从杰斯 的大腿上溜下来,向他跑去。那个男人弯腰,抚摩着小狗的背。杰斯 站起来。
“杰斯 。”比尔走过来,抱着杰斯 ,好像他是莱斯 利,而不是他自己。比尔紧紧地抱住了他,羊毛衫上的一个纽扣压在他的额头上,使他感到很疼。但是,虽然他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他没有动。他能感觉到比尔的身体在哆嗦,他怕抬头,如果抬了头,他就会看到比尔也在哭。他不愿意看到比尔在哭。他想离开这所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使他透不过气来。为什么莱斯 利没有在这里帮助他离开呢?为什么她不跑来使每个人都又笑起来呢?你想,死亡是多么伟大呀,它能使每个人痛哭,不断地痛哭。嗳,也不。
“你知道,她爱你。”他从比尔的声音知道他在哭。“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如果你不……”他的哭声完全爆发出来了。过一会,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成为她的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比尔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他自己,而像一部老伤感电影里的一个人。是莱斯 利和杰斯 会取笑的人,以后还 会模仿的人。呜——呼——,你是她那么好的朋友。他禁不住往后退了一点,退了一点点,让他的额头离开那讨厌的纽扣一点点。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比尔让他后退了。他听到他的父亲在他的头顶低声地问“葬礼”的事。
比尔用他接近正常的声音低声地回答,他们已决定把尸体火化,明天把骨灰送到宾夕法尼亚老家。
火化。有个东西在杰斯 的脑子里喀嚓响了一下。这就是说莱斯 利走了。变成灰了。他再也见不到她了。甚至死了的莱斯 利也见不到了。永远见不到了。他们怎么敢这样?莱斯 利属于他。和世界上任何人相比,莱斯 利都更加属于他。但甚至没有任何人问过他。甚至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而现在他将再也见不到她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只是哭。不是为了莱斯 利。他们不是为莱斯 利哭。是为自己哭。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他们能够有一点点关心莱斯 利,就决不会把她送到这个非常讨厌的地方。他必须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手,因为他怕自己可能会用拳头狠狠地打比尔的脸。
他杰斯 是真正关心莱斯 利的惟一的一个人。但莱斯 利却使他失望。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走了,死了。她走了,离开了他。她走了,正在那根绳索上晃悠,向他证明她不是胆小鬼。所以,她在那里,杰斯 ·阿伦斯 。或许,她现在正在某个地方取笑他,拿他开玩笑,好像他是迈尔斯 太太似的。她曾经使他吃惊,使他脱离了他以前的自己,进入她的世界;然后,在他真正熟悉她那个世界之前,而回到他原来的世界又已经太晚了的时候,她离开了他,使他在那里无依无靠——像在月球上到处流浪的宇航员,一个人,孤零零的。
后来,他怎么也弄不清是什么时候离开珀金斯 老宅的,只记得他是脸上淌着愤怒的眼泪,朝自己家奔上土丘的。他嘭的一声,踢开了门。梅·贝尔站在那里,褐色的眼睛睁得溜圆。“你看到她了吗?”她激动地问。“你看到她躺在棺材里了吗?”
他打了她,打了她的脸。使的劲比他一生中打任何东西的都大。她轻轻叫了一声,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他走进卧室,在床垫底下摸莱斯 利在圣诞节送给他的纸和颜料,直到全部把它们抽了出来。
埃利站在卧室门口抱怨他。他推开她,走了出去。布伦达坐在长沙发上也在埋怨,但真正进入他耳朵的只有梅·贝尔抽泣的声音。
他跑出厨房,穿过奶牛场,头也不回,一直跑到溪边。溪水比他上一次看到的时候稍微低了一点。上面,绳子磨散的一头,还 在沙果树上悠悠地晃动。我现在是五年级跑得最快的孩子。
他尖声叫着什么,但叫声里没有话语,又把纸和颜料用力扔到褐色的脏水里。颜料漂在水面,像船一样随着水流漂游;而纸张在四处打转,吸着浑浊的水,被往下吞没,兜着圈子,往下。他看着它们全都消失。逐渐地,他刚才疯狂奔跑后急促的呼吸和心跳慢慢地平静下来了。由于下雨,地面上仍然是泥泞的,但他还 是坐了下去。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永远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他把头低到膝盖上。
他的父亲在泥地上坐下,坐在他的旁边,说:“那是在做傻事。”
“我不管。我不管。”现在,他哭了,哭得很凶,几乎透不过气来。
他的父亲把杰斯 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似乎他只有乔伊斯 ·安那么大。他轻轻拍着他的头说:“好啦,好啦。别做声,别做声。”
杰斯 一面啜泣,一面说:“我恨她。我恨她。我希望在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见过她。”
他的父亲抚摩着他的头发,不说话。杰斯 慢慢安静下来。他们两人都看着水。
最后,他的父亲说:“真糟,是吧?”这是杰斯 所听到的他父亲给别的男人说的那种话。他奇怪地发现这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使他有了勇气。
“你相信人会到地狱里去吗,我是说,真正地下地狱?”
“你不是在担心莱斯 利·伯克吧?”
这听起来有点不舒服,,但还 是——“喔,梅·贝尔说……”
“梅·贝尔?梅·贝尔又不是上帝。”
“呃,但你怎么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呢?”
“天哪。孩子,别傻了。上帝不会把任何一个小女孩送进地狱的。”
在他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把莱斯 利·伯克当小女孩,但肯定上帝还 是把她当小女孩。到十一月,她才十一岁。他们站起身,开始向土丘上走去。他说:“我说恨她,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他的父亲点点头,表示理解。
每个人,甚至布伦达对他都很和蔼。每个人中,只有梅·贝尔是例外,她犹犹豫豫地退在后面,似乎怕和他有任何关系。他想给她说声抱歉,但做不到。他太累了,简直说不出话来。他只得让这件事听凭她处理了。他太累,累得没有力气想该怎么说了。
那天下午,比尔上他们家。说,他们就要离开这里,到宾夕法尼亚去,他想知道杰斯 能不能在他们回来之前照顾那只狗。
“没有问题。”比尔要他帮助,他很高兴。他担心今天上午自己跑了出来,伤了比尔的感情。他也想知道比尔是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怪罪他的。但这一类问题,他说不出来。
他抱住了特里恩王子。在满是尘土的小意大利轿车转上主路的时候,他向他们招手。他想,他看到了他们也向他招手,但因为太远,不能肯定。
他的母亲从来不许他养狗,但没有反对特里恩王子到他们家。特里恩王子跳到他的床上,蜷缩在他的胸口,他抱着他睡了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