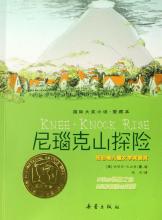天暗下来,树叶子在窗外哗哗地响着。我坐在妈的怀里伤心。妈帮我轻轻挠着后背,那块地方是我最喜欢别人摸的。
妈突然拍拍我,说:“好吧,我带你飞一次,怎么样?”
那当然也不错。
妈让我换上她的一套灰色的衣服,这样在黄昏时候不容易让人看出来。我们不能让人看到在天上飞。准备好了以后,妈把我背在她的背上,从三楼窗上往下一跳,我吓得大叫一声,妈那时已经隐了身,一点也看不到,只是可以觉得她的温暖,所以,我就好像在梦里跳了楼一样。我一定会摔死的啊!
妈说:“淼,你别卡我脖子啊。我上不来气。你放心,妈不能摔死你。我是你妈妈。”
我们飞起来了,在梧桐树的树梢上掠过。我看见树梢上有绿色的毛毛虫在爬,其中一条还拉下一条白色的大便。
我真的飞过南京西路口上的那个黑脸警察的头顶,他没看见我,他铁青着脸在骂一个想抢红灯的司帆,那个司机是个秃头,头顶上亮晃晃的,对警察满面堆笑。
路上挤满了下班的人们,可是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看天,所以没人看到我,没人发现一个孩子在他们头上飞。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都打开来了,红红绿绿,闪闪烁烁,照亮了街上人们的脸。每个人的脸上都很累的样子。大家急急忙忙地从街上走过,工作了整整一星期了,大多数大人的脸上不那么高兴,他们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公文包。
街上在塞车,出租车里那个算钱的机器上,红色的数字吧嗒吧嗒地往上跳,开摩托车的人在车缝缝里窜来窜去,有一个女人坐在后座上,风吹起了她的裙子,露出她雪白的大腿,她多么缺少教养!
有许多女人挤在熟食店里买东西,她们肯定是不高兴回家再做菜了。她们中有一个人抬头算钱的时侯看见了我,可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又把头低下去,和收银小姐核对钱数去了。她的身边,隔着个大玻璃,正好挂着一只通红油亮的烤鹅。那女人小小心心地数着手里找下来的一大把零钱,她大概根本就不相信她看到一个孩子在树梢上飞,以为是她自己看花眼了。她可真是个蠢女人啊。
路过波特曼前面,有一大段空旷的路,没有树。这时,在“硬石”西餐馆门口,一个小孩抬头看见我了,他马上张大了嘴巴,指着我说不出话来。我张大两只手,做出小鸟在飞的样子,我希望那孩子以为是我独自在飞。可我刚张开手,妈就叫:“你要死啊,会滑下去的。”
妈叫得也太响了,那孩子都听到了,他马上四下里看,找是谁在叫。
我们飞过去了。
我们到了有希尔顿酒店的那条路上,黄昏时候那里沿着街,有许多人在摆小摊,卖袜子、纽扣、头发夹子,大张的画,还有卖白兰花和毛笔的。黑黑瘦瘦的外地人蹲着卖旧碗旧花瓶,妈说他们卖的全是假古董。
这时候-我看到了爸爸。他从49路车站那里走过来,胳膊里夹着个大黑包,后脑勺有一撮头发翘着,和马路上遍地走着的下班爸爸没什么两样。
爸爸走到一个卖毛笔和宇帖的男人面前,那个男人笑着招呼爸爸,他叫爸“刘老师”。爸哪里是什么老师啊,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爸爸别是在诈骗吧。
爸爸从那人手里拿过一大堆毛笔和字帖,给了那男人一百块钱。
妈说,那个男人是天王的爸爸。他为了付老师加倍的学费,下班以后就到这里来摆小摊子。是妈找到了他,就用这法子把我们听的那亠部分学费还给他家。
妈说: “你爸爸说,我们虽然是偷的,,可也不能让这么穷的人吃亏了。” 爸爸和那男人说,他班上还有一些同学,也要他代买毛笔和字帖。现在孩子的毛笔字都不好,得多多练习。那男人高高兴兴地说好。爸爸也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和妈妈飞过他的头顶,他也像所有心事重重的下班爸爸一样,什么也没看见。他一手拿着大黑包,一手拿着一大包毛笔。我想,今年暑假我一定会过得很惨,全得我来把它们用完。
得了一件好事,你也总得为它付出些什么。爸爸觉得这样才是公平的。
妈妈说:“当一个人的老婆的意思,就是他怎么想,我也怎么想。我们是连体人,想的东西都一样,而且你还会为他的想法骄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那天晚上睡觉时,妈走到我的房间里,摸摸我的脸说:“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