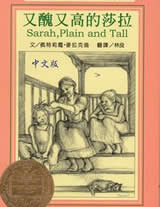如果你闭上双眼,碰上你运气好,你有时会看见黑暗中悬浮着一汪池水,没有一定的形状,颜色淡白,十分可一爱一。然后,你把眼睛眯一眯,水池就现出了形状,颜色变得更加鲜明;再眯得紧些,那颜色就变得像着了火似的。但就在它着火燃一烧以前,你就瞥见了那礁湖。这便是你在大一陆上所能看到的礁湖的最一逼一近的景象,仅仅是美妙的一瞬间,要是能有两瞬间,你也许还 能看见拍岸的一浪一花,听见人鱼的歌唱。
孩子们时常在礁湖上消磨长长的夏日,多半在水里游泳,或在水上漂浮,玩着人鱼的游戏,等等。你不要因此以为,人鱼们和他们友好相处;恰恰相反,一温一迪在岛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她们对她说过一句客气的话,她感到这永远是她的一个遗憾。当她偷偷地走近湖边时,她就看到成群的人鱼;特别是在流囚岩上、她们喜欢在那儿晒太一陽一,梳理她们的长发,那神态撩得她心里怪痒痒的。她可以像是踮着脚走路似的,轻轻游到离她们一码远的地方;可这时她们发现了她,就纷纷纵身潜入水中,或许还 故意用尾巴撩水溅她一身。
人鱼们对待男孩子们也是这样,当然彼得是例外,彼得和她们坐在流囚岩上长时间地谈天,在她们嬉皮笑脸的时候,骑上她们的尾巴。他把她们的一把梳子给了一温一迪。
看人鱼最魅人的时间,是在月亮初升时;那时,她们会发出奇异的哭号声。不过,那时候礁湖对于人类是危险的,在我们要谈到的那个夜晚之前,一温一迪从来没见过月光下的礁湖。她倒不是害怕,因为,彼得当然会陪伴她的;而是因为,她有严格的规定,一到七点钟,人人都必须上一床一睡觉。她时常在雨过天晴的日子来到湖畔,那时,人鱼大批地到水面上来,玩着水泡。彩虹般的水做成的五颜六色的水泡,她们当作球,用尾巴欢快地拍来拍去,试着把他们拍进彩虹,直到破碎为止。球门就在彩虹的两端,只有守门员才许可用手接球。有时,礁湖里有几百个人鱼同时在玩水泡,真是一大奇观。
但是,孩子们刚想参加她们的游戏,人鱼们就立刻钻进水里不见了,孩子们只得自己玩了。不过,我们有证据知道她们在暗中窥视着这帮不速之客,并且也很乐意从孩子们那儿学到点什么。因为约翰引进了一种打水泡的新方法,用头而不是用手,于是人鱼守门员就采用了这方法。这是约翰留在永无乡的一个遗迹。
孩子们在午饭后,躺在岩石上休息半小时,这景象也是挺好看的。一温一迪一定要他们这样做,即使午饭是假装的,午休也必须是真的。所以他们全都在一陽一光下躺着,他们的身一体给太一陽一晒得油光锃亮的,一温一迪坐在他们旁边,显得很神气。
就在这样的一天,他们全都躺在流囚岩上。岩石并不比他们的一床一大多少,不过,他们当然都懂得,不要多占地方。他们打着盹;或者,至少是闭着眼睛,趁一温一迪不注意时,不时互相挤一捏一下。一温一迪正忙着做针钱活。
正缝着缝着,礁湖上起了变化。水面掠过一阵微颤,太一陽一隐去不见了,一陰一影笼罩着湖面,湖水变冷了。一温一迪穿针都看不见了。她抬头一看,一向是喜笑颜开的瞧湖,这时变得狰狞可怕、不怀好意的了。
她知道,不是黑夜来到了,而是某种像夜一样黑暗的东西来到了。不,比夜还 要黑暗。那东西没有到来,可是,它先从海上送来一阵颤一抖,预示它就要到来。那是什么呢?
她一下子想起了所有那些她听到过的、关于流囚岩的故事。之所以叫流囚岩,是因为恶船长把水手丢在岩石上,让他们淹死在那儿。当海潮涨起时,岩石被淹没了,水手们就淹死了。
当然,她应该立刻叫醒孩子们;因为,不仅莫名的危险就要临头,而且睡在一块变冷的岩石上,也不利于健康。可是,她是一个年幼的母亲,不懂得这个道理;她以为,必须严格遵守午饭后休息半小时的规矩。所以,虽然她害怕极了,渴望听见男一性一的声音,可她不想叫醒他们。甚至在她听到了闷声闷气的划桨声,心都跳到嘴里的时候,她还 是没叫醒他们。她站在他们身边,让他们睡足。一温一迪难道还 不勇敢吗?
幸好男孩子当中有一个即使睡着了,也能用鼻子嗅出危险。彼得一纵身蹦了起来,像狗一样,立刻清醒了,他发出一声警告的呼喊,唤醒了别的孩子。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手放在耳朵上。
“海盗!”他喊道。别的孩子都围拢到他身边。一丝奇特的笑意,浮现在他的脸上,一温一迪看到,不禁打了个寒颤。他脸上露出这种微笑的时候,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们只能站着静候他的命令。命令下得又快又锐利。
“潜到水下!”
只见许多双大一腿一闪,礁湖顿时就像荒无人迹了。流囚岩孤零零地兀立在恶一浪一汹涌的海水中,仿佛它自己是被流放到那儿似的。
船驶近了,那是海盗的一只小艇,船上有三个人,斯密,斯塔奇,第三个是个俘虏,不是别人,正是虎莲。她的手脚都被捆绑着,她知道等待着她的命运是什么。她将被扔在岩石上等死。这种结局,在她那个部落的人看来,是比用火烧死或酷刑折磨还 要可怕的。因为,部落里的经书里,不是明明写着,经过水是没有路可以达到那幸福的猎场的吗?但是她的脸色从容镇静,她是酋长的女儿,死,也得死得像个酋长的女儿,这就够了。
正当虎莲口里衔着一把刀登上海盗船的时候,海盗们把她捉住了。船上没有设人看守,一胡一克总是夸口说,凭他的名气就能在一英里方圆之内护卫着他的船。现在,虎莲的命运也能够维持他的船。又一声哀号,在那个狂风怒号的夜里,会传得远远的。
在他们自己带来的黑暗中,两个海盗没有看见岩石,直到船撞上去才知道。
“顶风行驶,你这笨蛋。”一个一爱一尔兰口音喊道,那是斯密的声音,“这就是那块岩石。现在,我们只消把这印第安人拾起来扔到岩石上,让她淹死在那儿,就完一事了。”
把这样一位美丽的女郎丢在岩石上,确实是件残酷的事。可是,虎莲很高傲,不肯作无谓的挣扎。
离岩石不远,但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有两个脑袋在水里一起一落,那是彼得和一温一迪的脑袋。一温一迪在哭,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惨剧。彼得见过许多惨剧,不过他全忘了。他不像一温一迪那样,为虎莲感到伤心。他气愤的是,两个人对付一个,因此,他决意要救她。最容易的方法是,等海盗离开后再去救她,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做事从来不用容易的办法。
没有他办不到的事,于是,他现在就模仿一胡一克的声音说话。
“啊呵咿,你们这些笨蛋。”彼得喊道,模仿得像极了。
“是船长。”两个海盗说,惊愕得面面相觑。
“他准是游泳过来的。”斯塔奇说,他们想看,又看不见他。
“我们正要把印第安人放在岩石上。”斯密冲着他喊。
“放了她。”回答是令人吃惊的。
“放了?”
“是的,割断绑绳,放她走。”
“可是,船长——”
“马上放,听见没有。”彼得喊道。
“这真是怪事。”斯密喘着气说。
“还 是照船长的命令做吧。”斯塔奇战战兢兢地说。
“是,是。”斯密说,判断了虎莲的绳子。一眨眼,虎莲像泥鳅一样,从斯塔奇的两一腿之间,滑一进了水里。
一温一迪看到彼得这样机灵,当然很高兴;可是她知道,彼得自己也一定很高兴,很可能要叫喊几声,暴露了他自己。所以,她立刻用手捂住他的嘴。正要这样做时,她的手停住了,“小艇,啊呵咿!”湖面上传来一胡一克的声音,这次,发话的却不是彼得。
彼得大概正准备要叫喊,可是他没有叫喊,却撅一起嘴,吹出一声惊异的口哨。
“小艇,啊呵咿!”又来了一声。
一温一迪明白了,真正的一胡一克也已来到了湖上。
一胡一克朝着小艇游过去,他的部下举起灯笼给他引路,他很快就游到了小艇边。在灯笼的亮光下,一温一迪看到他的铁钩钩住了船边;正当他水一淋一淋地爬上小艇时,一温一迪看见了他那张凶恶的黑脸,她发一抖了,恨不得马上游开;可是彼得不肯挪动,他兴奋得跃跃欲试,又自大得忘乎所以。“我不是个奇人吗,啊,我是个奇人!”彼得小声对一温一迪说;虽然一温一迪也认为他是个奇人,可是为了他的名誉着想,她还 是很庆幸,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听到他的话。
彼得向一温一迪做了一个手势,要她仔细听。
两个海盗很想知道船长为什么到这儿来,可是,一胡一克坐在那儿,他用铁钩托着头,显得非常忧郁的样子。
“船长,一切都好吧?”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可是,一胡一克的回答只是一声低沉的呻一吟。
“他叹气了。”斯密说。
“他又叹气了。”斯塔奇说。
“他第三次叹气了。”斯密说。
“怎么回事,船长?”
末了,一胡一克愤愤地开口说话了。
“计谋失败了,”他喊道,“那些男孩找到了一个母亲。”
一温一迪虽然害怕,却充满了自豪感。
“啊,他们真坏。”斯塔奇喊道。
“母亲是什么?”糊涂的斯密问道。
一温一迪大为诧异,她失声叫了出来:“他居然不知道!”从此以后,她总是觉得,如果要养个小海盗玩,斯密就是一个。
彼得一把将一温一迪拉到水下,因为一胡一克惊叫了一声:“那是什么?”
“我什么也没听见。”斯塔奇说,他举起灯笼向水上照。海盗们张望时,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那就是我告诉过你们的那只鸟巢,浮在海面上,那只永无鸟正伏一在巢上。
“瞧,”一胡一克回答斯密的问题,“那就是个母亲。这是多好的一课啊!鸟巢一定是落到了水里,可是,母鸟肯舍弃她的一卵一吗?不会的。”
他的话声忽然断了,仿佛一时想起了他那天真无邪的日子——可是他一挥铁钩,拨一开了这个软弱的念头。
斯密很受感动,他凝望着那只鸟,看着那鸟巢渐渐漂走;可是,更多疑的斯塔奇却说:“如果她是个母亲,她在附近漂来漂去,也许是为了掩护彼得。”
一胡一克抖缩了一下。“对了,”他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斯密的热切的声音,把一胡一克从沮丧中唤一起。
“船长,”斯密说,“我们不能把孩子们的母亲掳来做我们的母亲吗?”
“这计策太棒了。”一胡一克喊道,他那大脑瓜里立刻就想出了具体的方案,“我们把那些孩子捉到船上来,让他们走跳板淹死,一温一迪就成了我们的母亲了。”
一温一迪又禁不住失声叫了起来。
“绝不!”她喊道,头在水面上冒了一下。
“这是什么?”
什么也看不见,海盗们想,那一定是风吹的一片树叶响。“你们同意吗,伙计们?”一胡一克问。
“我举手赞成。”他们两个说。
“我举钩宣誓。”
他们都宣誓了。这时,他们都来到了岩石上,一胡一克忽然想起了虎莲。
“那个印第安婆一娘一在哪儿?”他突然问。
他有时喜欢开个玩笑逗趣儿,他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没问题,船长。”斯密美滋滋地回答,“我们把她放了。”
“把她放了!”一胡一克大叫。
“那是你下的命令呀。”水手头结结巴巴地说。
“你在水里下的命令,叫我们把她放了。”斯塔奇说。
“该死,”一胡一克暴跳如雷地喊,“搞什么鬼?”他的脸气得发黑;可是,他看到他们说的是实话,不禁惊讶起来。
“伙计们,”他有点颤一抖地说,“我没发过这样的命令。”
“这可怪了。”斯密说。他们全都心慌意乱起来。一胡一克提高了声音,可他的声音带着颤一抖。
“今夜在湖上游荡的一精一灵鬼怪呀,”他喊道,“你们听到了吗?”
彼得当然应该不出声,可是,他当然非出声不可。他马上学着一胡一克的声音回答。
“见你的鬼,我听到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胡一克连脸都没有发白,可是斯密和斯塔奇吓得抱作一一团一。
“喂,你是谁?你说。”一胡一克问。
“我是詹姆斯·一胡一克,”那个声音回答,“快乐的罗杰号船长。”
“你不是,你不是。”一胡一克哑着嗓子喊。
“该死,,”那声音反唇相讥,“你再说一句,我就在你身上抛锚。”
一胡一克换了一副讨好的态度。“如果你是一胡一克,”他几乎是低三下四地说,“那么,告诉我,我又是谁?”
“一条鳘鱼,”那个声音回答,“只不过是一条鳘鱼。”
“一条鳘鱼!”一胡一克茫然地重复了一句;他那一直鼓得足足的傲气,这时突然泄一了气,他看到他的部下从他身边走开了。
“难道我们一直拥戴一条鳘鱼作船长吗?”他们嚷嚷着说,“这可是降低我们的身份了。”
他们原是一胡一克的狗,反倒咬了他一口;一胡一克虽然落到这一步,可是他并不太注意他们。要反驳这样一个可怕的一胡一说,他需要的,不是他们对他的信任,而是他的自信。他觉得,他的自我从他身上滑走了。“别丢下我,伙计们。”他哑着嗓子低声说。
他那凶悍的天一性一里,带有一点女一性一的特色,所有大海盗都一样,有时也会因此得到一些直感。忽然他想试一试猜谜游戏。
“一胡一克,”他问,“你还 有别的声音吗?”
要知道,遇到游戏,彼得总是禁不住要玩的。于是他用自己的声音快活的回答:“有啊。”
“你还 有一个名字吗?”
“有的,有的。”
“蔬菜?”一胡一克问。
“不是。
”矿物?
“不是。
”动物?
“是的。
”男人!
“不是!”彼得嘹亮地回答,声音里带着轻蔑。
“男孩?”
“对了。”
“普通的男孩?
”不是!“
”奇异的男孩?“
一温一迪苦恼地听着,这次的回答是”是“。
”你住在英国吗?
“不是。”
“你住在此地吗?”
“是。”
一胡一克完全闹糊涂了。“你们两个给他提出几个问题。”他对另两个人说,擦擦他汗湿的前额。
斯密想了想。“我想不出什么问题。”他抱歉地说。
“猜不出啦,猜不出啦,”彼得喊,“你们认输了吗?”
他太骄傲了,把这个游戏玩过了头,强盗们看到机会到了。
“是的。是的。”他们急切地回答。
“那好吧,我告诉你们,”他喊道,“我是彼得·潘!”
潘!
霎时间,一胡一克又恢复了常态,斯密和斯塔奇又成了他的忠实部下。
“好啦,现在我们可以把他弄到手啦。”一胡一克高声喊道,“下水,斯密。斯塔奇,看好船。不管是死是活,把他抓来。”
说着,他跳下水去;同时,彼得那快活的声音喊了出来。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好啦,好啦。”湖的四面八方都响应。
“那么,向海盗进攻。”
战争很短,但很激烈。头一个使敌人流血的是约翰,他英勇地爬上小艇,扑向了斯塔奇。经过一场剧烈搏斗,海盗手中的弯刀落掉了。斯塔奇挣扎着跳到水里,约翰也跟着跳下去,小艇漂走了。
水面上不时冒出一个脑袋,钢铁的寒光一闪,跟着是一声吼叫,或一声呐喊。在混战中,有的人打了自家人。斯密的开瓶钻一捅一着了图图的第四根肋骨,他自己又被卷一毛一刺伤了。远离岩石的地方,斯塔奇正在紧迫斯莱特利和孪生子。
这一阵子彼得又在哪儿呢?他在寻找更大的猎物。
其他的孩子都很勇敢,他们躲开海盗船长是无可责怪的。一胡一克的铁钩把周围的水变成了死亡地带,孩子们像受惊的鱼一样,逃开这块地方。
可是有一个人不怕一胡一克,有一个人打算走进这个地带。
说也奇怪,他们并没有在水里相遇。一胡一克爬到岩石上喘一息,同时,彼得也从对面爬上来。岩石滑得像一只球,他们没法攀缘,只能匍匐着爬上来。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对方也正在爬上来。两个人都在摸索着想抓住一块能着力的地方,不料竟碰到了对方的手。他们惊讶得抬起头来,他们的脸几乎挨到了,他们就这样相遇了。
有些大英雄都承认,他们临一交一手前,心都不免有些往下沉。假如彼得那时也是这样,我也不必替他隐瞒。不管怎么说,一胡一克是海上库克唯一害伯的人。可是彼得的心没有往下沉,他只有一种感觉:高兴。他喜欢地咬紧了他那口好看的小牙。像转念一样快,他拔一出一胡一克皮带上的刀,正好深深地插一进去,这时,他看到自己在岩石上的位置比敌人高,这是不公平的战斗。于是,他伸手去拉那海盗一把。
就在这时,一胡一克咬了他一口。
彼得惊呆了,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不公平。他变得不知所措,只是楞楞地望着,吓傻了。每个孩子第一次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都会这样发呆。当他和你真诚相见的时候,他一心想到的是,他有权利受到公平待遇。如果你有一次对他不公平,他还 是一爱一你的,不过他从此就会变样了。谁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受到的不公平,除了彼得以外。他经常受到不公平,可他总是忘记。我想这就是他和别人真正不同的地方吧。
所以,彼得现在遇到不公平,就像初次遇到一样,他只能楞楞地望着,不知所措。一胡一克的铁钩抓了他两次。
几分钟以后,别的孩子看见一胡一克在水里发狂似的拼命向小艇游去。这时,他那瘟神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得意的神色,只有惨白的恐惧,因为那只鳄鱼正在他后面紧追不舍。在平时,孩子们就会一边在旁游泳,一边欢呼;可是,这次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见了彼得和一温一迪,在湖里到处喊着他们的名字,寻找他们。他们找到那只小艇,钻了进去,一边划着,一边高喊:“彼得,一温一迪。”可是没有回答,只听到人鱼嘲弄的笑声。“他们准是游回去了,要不就是飞回去了。”孩子们断定。他们并不很着急,因为他们很相信彼得。他们像男孩子一样的格格地笑,因为,今晚可以迟睡了,这全是一温一迪一妈一妈一的错。
当他们的笑语声消失以后,湖面上一片冷清的寂静,随后忽听得一声微弱的呼叫。
“救命啊,救命啊!”
两个小小的人一体正朝着岩石游来,女孩已经昏过去,躺在男孩子的臂上。彼得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把一温一迪拽上岩石;然后,在她身边躺倒了。虽然他自己也昏迷了,他却知道湖水正在上涨。他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淹死,可是他实在无能为力了。
他们并排躺在岩石上时,一条人鱼抓住一温一迪的脚,轻轻地把她往水里拽。彼得发觉她正在往下滑,突然惊醒了,恰好来得及把她拉回来;不过,他不能不把实恬告诉一温一迪。
“我们是在岩石上,一温一迪,”他说,“可是这岩石越来越小了,不多时,水就要把它淹没。”
可是一温一迪现在还 听不懂。
“我们得走。”她相当开朗地说。
“是的。”彼得无一精一打采地回答说。
“彼得,我们是游泳还 是飞?”
彼得不得不告诉她:
“一温一迪,你以为没有我的帮助,你能游泳或是飞那么远,到岛上去吗?”
一温一迪不得不承认,她是太累了。
彼得呻一吟了一声。
“你怎么啦?”一温一迪问,立刻为彼得着急了。
“我没法帮助你,一温一迪。一胡一克把我打伤了,我既不能飞,也不能游泳。”
“你是说,我们两个都要淹死吗?”
“你瞧,水涨得多快。”
他们用手捂住眼睛,不敢去看,他们心想很快就要完了。他们这样坐着的时候,一样东西在彼得身上轻轻一触了一下,轻得像一个吻,随后就停在那儿不动了,仿佛在怯生生地说:“我能帮点忙吗?”
那是一只风筝的尾,这风筝是迈克尔几天前做的。它挣脱了迈克尔的手,漂走了。
“迈克尔的风筝。”彼得不感兴趣地说,可是紧接着,他突然抓住风筝的尾,把它拉到身边。
“这风筝能把迈克尔从地上拉起来,”他喊道,“为什么不能把你带走呢?”
“把我们两个都带走!”
“它带不动两个,迈克尔和卷一毛一试过。”
“我们一抽一签吧。”一温一迪勇敢地说。
“你是一位妇女,不行。”彼得已经把风筝尾系在她身上。一温一迪抱住他不放,没有他一道,她不肯去。可是,彼得说了一声“再见,一温一迪”,就把她推下了岩石;不多会儿,她就飘走看不见了。彼得独自留在了湖上。
岩石变得很小了,很快就会完全掩没。惨白的光偷偷地袭上海面,过一会儿,就能听到世上最美妙动听、最凄凉悲切的声音:人鱼唱月。
彼得和别的孩子不同,可是,他到底也害怕了。他浑身一阵颤栗.就像海面掠过一股波涛;不过,海上的波涛是一一浪一逐一一浪一,以致形成了千层波涛;可是,彼得只感觉到一阵颤栗。转眼间,他又挺一立在岩石上,脸上带着微笑,心头的小鼓突突地敲。像是在说:“去死是一次最大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