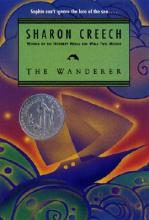04 美洲笑鼻狐
1935年1月6日,星期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很开心地看到爸爸坐在桌前看报。
我感觉得到他见到我很高兴,这可不是装出来的。“嗨!”他说。
妈妈正在给娜塔莉打行李。我不敢相信她今天就要去寄宿学校了,我以为至少还 有一个星期。
小娜把厨房的椅子拉进客厅,硬挤在三个条板箱中间。“嗨,娜塔莉,今天早上太阳起床了吧?”我就像每天早上一样问她。
她从来不回答。以前这让我很生气,我可不愿当石头的弟弟。去年有一天,我生气了,从她身旁走过,没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有!
那天,我出门上学后,妈妈说娜塔莉坐在我房间外面整整哭了两个小时。娜塔莉不是个爱哭鬼,而是个爱叫鬼,我从没见过她为了算旧账而哭的。妈妈不清楚为什么娜塔莉要哭,她不知道我冷落了娜塔莉。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问娜塔莉太阳的事情,她不回答,我也只会感到一点小小的不爽。
“那么,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里,你早餐想吃什么呀?”妈妈问她。
“柠檬蛋糕。”娜塔莉说,她每天都这样说,而每天妈妈都会说:
“傻宝贝,你不可以把柠檬蛋糕当早餐吃。”
“不过也没什么不好!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吃柠檬蛋糕是个不错的点子。你觉得怎么样呢,穆思?”妈妈问我。
“当然好啊。”我说话的声调像女孩一样高。我不知道以后我的声音听起来会不会像米老鼠,或是像魔豆藤上面的巨人。
娜塔莉将身子转向我,直视着我的双眼,那样子好像她消失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又突然出现一样。
“别看着我,这又不是我出的主意。如果由我决定的话,我们此刻已经在圣·摩尼卡1玩了。”我小声地说。
(圣·摩尼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滨城市,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爸爸读报纸头条新闻给娜塔莉听,还 把每一条都加上数字:“金门大桥持续施工。一百零三人返回工作岗位,两人辞职,七人犹豫不决,五人跷脚休息,二人晚餐吃香肠,三人没有……”
“吃早餐了!”妈妈叫道。
娜塔莉的脸离盘子只有五六厘米远。她吃得飞快,害得我肚子痛。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不跟她一起吃饭。
“娜塔莉·佛莱纳根全家。”我坐下来时,小娜说。
我很纳闷:她到底知不知道她要去住校了?我们把马利诺夫学校说得好像连英国女王的小孩也会被送到那里一样。不过不知怎的,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都绕过最主要的事情不提。
你放学后并不是回到家里来哦;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你可是在学校里哦。
爸爸用餐巾擦了擦他的大嘴巴,说:“娜塔莉,跟年纪相近的孩子在一起,你会有多开心啊!”
我在想,所谓的年纪相近是多大年纪?不过我知道他的意思。或许娜塔莉会遇到其他跟她一样的小孩;或许他们会彼此相认,然后用他们自己特别的方式沟通。
妈妈把小娜打扮好以后,爸爸提起她的行李,把纽扣盒交给她,然后打开门。
“穆思。”妈妈好像这会儿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觉得你不需要跟来。”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想去。”我的眼睛没看妈妈,也没看爸爸和小娜。
“海伦!”爸爸的声音带着哀求。
“肯姆,我只是觉得他不想去罢了。”妈妈说。
“穆思当然想跟来。”爸爸把小娜的行李箱交给我,又拍拍我的背,“没有他,我们办不了这件事!”
这让我想起六岁时妈妈把我送到外婆家住的事。她把我的每一件内裤都仔细打包,弄得好像去外婆家是多么大的优待一样。到了外婆家,外婆脸上带着怒火。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用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瞪着我妈。等妈妈离开后,我听到外婆对外公说:“有个糟糕的精神科医师认为娜塔莉所得到的关注不够,所以海伦就把他送出门了!我们的马修啊!有他在这里,我就像是在泥浆里打滚的猪一样快乐。可是这件事实在太蠢了,哪个小孩没有兄弟姐妹?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有七八个兄弟姐妹呢!家里有个弟弟才不是娜塔莉变成这样的原因,把他们姐弟俩摆在一起瞧瞧,那个了不起的精神科医师就会知道了。他才该去检查脑袋呢。把穆思带开,只会让小娜病得更严重。”
隔天一早是爸爸叫醒我的:“穆思,带着你的枕头。”他说着,一边把我行李箱上的扣子啪啪地扣上。“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走向码头。娜塔莉走得特别慢。我担心我们会错过船班,不过或许这正是她的计划。
我喜欢把这几年也想成是她的计划之一。然后有一天小娜会说,这一切都是她假造出来的疯狂游戏,想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她。
爸爸在前面紧走。昨天船夫告诉我们:“我们不等任何人,即使是上帝也得准时。”不过不知为什么,那艘旧军用汽船还 在等着。
妈妈走过那个“探密箱”——一个金属探测器,专门用来确保没有人带枪上岛。
当我正观察着船老大松开跟我的手臂一样粗的缆绳时,妈妈对小娜说:“这所学校是你的机会,娜塔莉。你真幸运,拥有这样的机会。”
小娜没说什么。她两眼盯着一只从木头长椅上啄起洋芋片的海鸥。我抬头看着蓝天,一只鸟在高空中飞翔,另一只正低空掠过蓝绿色的海面。
爸爸带了一本书在身上,书名是《麦奎格动物图鉴》,里面有不错的索引。没有什么事比爸爸朗读图书索引给娜塔莉听更让她开心的了。
“美洲叶鼻蝠,48页。”爸爸念着,“美洲鹌鹑,232页;美洲棘鼠,188页……”
一群海鸥飞过我们船的上方。娜塔莉和我看着它们,身体比平常摇晃得更厉害。不过在这儿不太看得出来,因为船也在不停地摇晃着。
“我数过了,共有229只鸟。”我指着海鸥说。
“坏穆思。”娜塔莉说,“9只鸟,9只。”
我对着她微笑:“我数了数,有47个人在甲板上。”
“坏穆思,11个人,11。”娜塔莉很爱挑我的错。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娜塔莉开始带着书来找我——都是大部头像字典或百科全书之类的旧书。她会翻到最后一页,再把书重重地放在我的膝上。我搞不懂她想做什么。有一天,为了要让她走开,我便开始念她打开的那一页。那是一本历史书,索引里满满地都是人名与地名。我念到“马丘比丘”这一座古印加帝国的遗址时,念成“麻丘皮丘”。“坏穆思。”她说,“马丘比丘。”直到妈妈告诉我马丘比丘才是正确的读法以前,我都以为是娜塔莉在发神经。妈妈立刻到图书馆替娜塔莉借了一大摞历史书。没多久我们就知道娜塔莉并不是对历史有兴趣,她爱的是索引,什么主题都好。但我们仍然不清楚她是怎么学到马丘比丘的正确读法的。
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旧金山的码头了。爸爸说,囚犯们都说,你花十二分钟去恶魔岛,却要花二十年才回得来。
我们稍坐了一会儿,看着要上教堂的一家人走下船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转过身倒退着走,手抓着栏杆,小心翼翼地移动他短胖的腿。他的爸爸朝我妈妈眨眨眼:“他长大以后会从事保险业。”
“好了,马上下船,把货搬出来吧。”爸爸说。可是妈妈好像黏在座位上,她直盯着那个娃娃瞧,娃娃正紧握住他妈妈的手穿过码头。妈妈用手帕擤了擤鼻子,很快地眨眨眼睛,努力想忍住泪。
娜塔莉看见这一幕,便在椅子上蜷缩成小球不肯动了。妈妈试着恢复镇定,再度用开朗的声调说话。
“娜塔莉,亲爱的,我有一点点感冒,没什么,亲爱的宝贝。现在,来吧!甜心。这是一个好日子啊!”
她的话听起来假惺惺的,娜塔莉也知道。娜塔莉把膝盖抱得更紧了。爸爸小声地说,希望他不用背她。
爸爸蹲下来,单膝跪地,跟小娜讲了很久的话。船夫用手势催促我们下船。妈妈焦虑地摆弄着手套,她拉低帽檐,穿过甲板去跟船夫说话。
我把重心从一只脚换成另一只脚,接着又换回来。最后,爸爸站起来,看着我说:“穆思,你能不能让她起来?”
“该下船的每一个人都得下船!”船夫大声嚷嚷。要回阿卡拉岛的人也开始登船了。
我四处张望着想主意。我把那本书抓起来翻到最后,说:“美洲笑鼻狐,3000页。”
娜塔莉还 是紧紧蜷曲着,不过她的头稍稍往上抬了抬。
“澳洲鹌鹑,200页。”我说。
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个声音,然后脱口说出:“不对,穆思!美洲叶鼻蝠,48页。美洲鹌鹑,232页!”她说。
我往船梯板走了一步,边说:“美洲棘畜,18页。”
“坏穆思。坏、坏、坏。美洲棘鼠,188页。”她摇摇头,不过现在她站起来了,跟在我后面。
一步接一步、一页又一页,娜塔莉跟着我下船了。爸爸提着棕色行李箱,妈妈微笑着,娜塔莉跟在我旁边。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很紧,很痛。
从我出生到现在,娜塔莉可能只拉过一次我的手,现在是第二次。为什么她要挑现在?
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不过是妈妈的另一个疯狂点子罢了。
我觉得肚子不舒服,我想把娜塔莉拉着的我的手甩开,可是我没有。我继续走。好穆思。乖穆思。我总是做我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