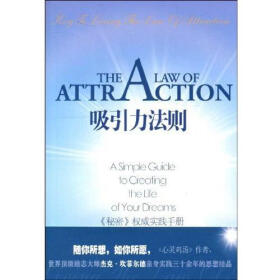做出承诺,是真正的爱的基石之一。具体而深刻的承诺,即便不能保证情感关系一帆风顺,也会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人将精神贯注于某种事物之初,其感情投入可能非常有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她)就应该投入更多的感情,不然,情感关系迟早会走向瓦解,或始终处于肤浅、脆弱的状态。还是以我为例,我在结婚典礼之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表现一直很镇定。渐渐地,我感觉紧张乃至有些发抖,甚至不记得婚礼的过程,以及随后发生的任何事。经过一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了这一人生变化,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家庭上,终于走出坠入情网的状态,找到了真爱的原动力。通常说来,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只要投入更多的情感,便可从生物学上传宗接代的本能阶段,成长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父母。
对于以爱为基础的情感关系,全身心地付出,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只有持久的情感关系,才能使心智不断成熟。假如我们生来就缺乏安全感,不仅时刻担心遭到遗弃,而且感觉前途渺茫,心智永远都不可能成熟。夫妻面对依赖和独立、操纵和顺从、自由和忠贞等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方案,甚至将问题扩大化,整天生活在猜疑、恐惧的阴影中,就无法平心静气地找到出路,最终会使情感关系归于毁灭。
做出承诺,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安全感。但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难以做出承诺。让病人做出承诺,通常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不知道如何实现“精神贯注”,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调。消极性人格失调者不愿承诺,甚至丧失了承诺的能力,他们并不是害怕承诺的风险,而是可能完全不知道如何做出承诺。他们可能在童年时,就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承诺,所以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也从未有过承诺的体验。
神经官能失调患者能够了解承诺的意义,但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失去了做出承诺的动力。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父母大多具有爱心,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承诺带来的安全感,不过后来因为出现死亡、被遗弃或其他原因,这种安全感宣告终止,使其承诺无法得到回应,并成为痛苦的记忆,他们由此害怕做出新的承诺。患者一旦经受过心灵的创伤,除非建立起理想的情感关系,不然伤口就难以愈合。有时候,作为心理医生,我每想到要接待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心中就忐忑不安。毕竟,想使治疗顺利进行,心理医生就必须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像富有爱心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全心全意地去关心病人,而且不可半途而废,这样才能打开病人的心扉,对症下药。
27岁的雷切尔小姐患有严重的性冷淡,而且性格内向,言行过于拘谨。她有过短暂的婚姻,离婚后就来找我治疗。她告诉我,由于无法接受她的性冷淡,丈夫马克和她分道扬镳。雷切尔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和马克结婚是件好事。我希望他温暖我的心灵,让我有所改变,但我想错了。这也不是马克的问题。和哪个男人在一起,都无法让我体验到性的乐趣,我也不想从性爱方面找到乐趣。
尽管我有时也认为应该做出改变,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很不幸,我习惯了当前的状态。尽管马克时常提醒我,让我尽量放松下来,可是,即便我能够做到,也不想改变当前的状态。"
治疗进行到第三个月时,我就提醒雷切尔:她每次前来就诊,还没坐到座位上,就起码要说上两次“谢谢”———第一次“谢谢”,是我们在候诊室刚见面时;第二次“谢谢”,是在她刚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雷切尔问:“这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这样多礼没有必要。从你的表现看,就像是个缺乏自信、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客人。”
“可我本来就是客人,这里毕竟是你的诊所。”
“说得对,”我说,“可是别忘了,你已经为治疗付了钱。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属于你,你有自己的权利,你不是客人。办公室、候诊室,还有我们共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你付费买下了它们,它们就是属于你的,为什么要为属于你的东西向我道谢呢?”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这么想。”雷切尔惊讶地说。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还认为,我随时都会把你赶走,对吗?”我说,“你认为我有一天可能这样对你说:‘雷切尔,为你治病实在是无聊,我不想再给你治疗了。你赶快走吧,祝你好运。’”
“你说得没错,”雷切尔说,“这正是我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赶我走吗?”
“哦,那种可能也未必没有,任何心理医生都可能那么做。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永远都不会。那么做有悖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听我说,雷切尔,”我说,“我接待了像你这样的长期患者,就是向你和你的病情做了承诺。我要尽力帮助你治疗,只要需要,我会一直同你合作,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直到把问题解决,或到你决定终止治疗为止。总而言之,决定权在你手中。除非我不在人世,不然,只要你需要我的服务,我是绝不会拒绝的。”
雷切尔的病因不难了解。治疗伊始,马克就告诉我:“我想,对于雷切尔的状况,她母亲要承担很大责任。她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却不是个好母亲。”原来,雷切尔的母亲对子女要求过分严格,雷切尔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在家中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待她,就像对待普通雇员一样。除非雷切尔照她的话,达到她希望的一切标准,否则她在家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她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和我这样的陌生人相处,又怎么可能感觉安全呢?
父母没有给雷切尔足够的爱,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仅依靠简单的口头安慰,伤口永远不可能愈合。治疗进行了一年,我和雷切尔讨论起她当着我的面,从来都不流泪的情形,这是她不能释放自己的证据。有一天,她不停地唠叨,说她应该提高警惕,防备别人给她带来伤害。这时我感觉到,只要给她一点点鼓励,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我伸出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柔声地说:“雷切尔,你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但是很遗憾,这种一反常规的治疗模式并未成功,雷切尔依旧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连她自己也感到灰心:“我办不到!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释放自己!”下一次治疗时,雷切尔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得说实话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告诉我,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迷惑不解:“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你要把我的问题做个总结。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再为我治疗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下轮到雷切尔迷惑了,“上一次,你不是要让我哭出来吗?”她说,“你一直想让我哭出来,上次还尽可能帮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我想,你一定不想给我治疗了,因为我不能按你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对吗?”
“你真以为我会放弃治疗吗,雷切尔?”
“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不,雷切尔,你说错了,不是任何人。你母亲或许有可能那样做,可我不是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你不是我的雇员,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去做我要你做的事,而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这段时间属于你。为了治疗,我会给予你某种启示或敦促,可是我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非要做到什么程度。
还有,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治疗多长时间都可以。"
如果童年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我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抛弃”对方,即采取“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
这种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雷切尔小姐的性冷淡,就是其中之一,她无疑是向丈夫以及以前的男友宣告:“我不会把自己彻底交给你。我知道,你早晚会把我抛弃。”对于雷切尔而言,在性爱以及其他方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意味着情感的投入,而过去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给她带来回报,所以她绝不愿“重蹈覆辙”。
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在起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五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古老而富裕的家族,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和其他病人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才不会抛弃她,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
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雷切尔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彼此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配合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爱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代表着承诺和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爱,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其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爱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爱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爱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唿唤。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
假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充分的,病人迟早也会做出承诺———对心理医生和治疗本身的承诺,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病人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做出承诺,而有的病人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走到这一步。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使病人做出承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彼时彼刻,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病人做出承诺,意味着敢于承担承诺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心理医生对治疗做出承诺,其风险不仅在于承诺本身,也在于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挑战,甚至要对以往的认识做大幅度修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包括移情的心理现象),通常面临诸多困难。要实现自我完善,享受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进而使真正的爱成为人生的重心,就必须无所畏惧,敢于做出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当然,任何有别于以往的调整,都可能要经受极大的风险。譬如说,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他第一次同一个女子约会时,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还有,对任何人都缺乏信任的患者,第一次躺在心理医生诊室的病榻上,也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于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对丈夫宣称,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她都想步入社会生活,获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在55岁之前,一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终于有一天,他严肃而坚决地告诉母亲,从现在开始,她绝不可以再叫自己的乳名,因为那既幼稚又可笑;一个不苟言笑、貌似硬汉的男子,某一天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流下了充满真情的热泪;还包括雷切尔———她有一天终于放松下来,在我的诊室里号啕大哭……此类改变,使当事人承担的风险之大,甚至不亚于战场上深陷险情的士兵。如果士兵被敌人的枪口顶住后背,就没有逃生的可能。同样,一个追求心智成熟的人,思想和情感随时都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恢复到以前熟悉而又狭隘的方式。
心理医生也要拥有同病人一样的勇气和智慧,而且要承担自我改变的风险。我本人就是如此。在多年治疗中,我经常根据不同情况,打破常规治疗模式。遵循过去的治疗原则,可能承担的风险更小,但为了病人顺利康复,我需要冒险实践,有时宁可违背传统和常规的做法,拒绝因循守旧,更不会敷衍了事。回顾过去,每一次成功的治疗,都有冒险尝试的痕迹,而且每每让我经历了更多的痛苦。治疗者只有承担必要的痛苦,才更可能取得意外的成效。有时候,让病人了解医生艰难的选择,对于他们也是深刻的震动、强大的激励,促使他们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治疗者和被治疗者心灵相通、彼此鼓励,才更可能使治疗立竿见影。
家长的角色和心理医生相似。聆听子女的心声,满足他们的需要,有助于家长实现自身完善,而不是盲目坚守权威,颐指气使。恰如其分地做出改变,使人格和心灵不断完善,才能担负起做父母的职责。
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和自我完善过程中,也会跟着一并走向成熟,对于双方都是大有益处。不少父母在子女处于青春期以前,尚算得上尽职尽责,渐渐地,其思维却变得落后和迟钝起来,无法适应子女的成长与改变。他们不思进取,放弃了自我完善的进程。有的人认为,父母为子女经受痛苦与牺牲,是一种殉难行为,甚至是自我毁灭,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父母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子女。父母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子女的变化,就不会与时代脱节,对其晚年人生也大有益处。遗憾的是,很多人漠视这一点,白白错过了自我成熟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