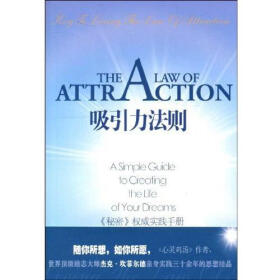微光
“疾风骤雨,衣履尽湿的时候,有人借伞替你遮一遮,这悄悄的一线光,是你我之间最值得珍重的缘分。”
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仍在大学附近租房子住,房租便宜,连带着饭钱也不贵。
住的小区有几家一层的临街小饭馆,客人都挺多,刚搬过来那天,一家一家地转,转了好几个来回还没有定下来选哪一家。
我妈看见我这种样子肯定会碎碎念:死孩子,那你就一家吃一顿,最后看看哪一家好吃,然后一直吃下去不就行了吗?
从天光微暗到天色全黑,我颇有兴致地一圈一圈转着。
粗看起来,几家小饭馆的摆设都差不多。一台电视机挂在餐厅里,谁想看谁就遥控。灯光大都是白色的,只有一家选择了黄色的灯光,略显昏暗,并不亮堂。我后来问老蔡为什么,他说:“有一天,有个学生说,在黄色灯下吃饭,感觉像回了家,于是我就换了。”
老蔡是其中一家饭馆的老板。当初选择他家做长期食堂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的女儿。
老蔡的女儿五岁左右,经常坐在饭馆的门口洗碗,所有的碗都一模一样,她看着桶里的碗,又看着手上的碗,再看看桶里的碗,再看看手上的碗,整个人突然就静止下来,坐在那儿开始发呆。
她眉头紧锁,一定遇见了特别为难的事。
只见她冲进屋里,找来一个新的桶,把手上的四个碗按顺序一一放好,又迅速把四个碗按次序一个一个洗干净,擦干,摆好。再跑到妈妈收钱的柜台下面拿出一小瓶油漆和一只小毛笔,开始在每一个碗的底下写字。
哦,那时我才看明白,估计她是在给这些碗做标注。我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她,笑了起来。我走过去问她:“小妹妹,你为什么要在碗上写字啊?”
她头没有抬,一边写一边说:“这样就可以知道是谁的碗了。”
“那么多碗,为什么你只写这几个?”
“是今天几个姐姐的碗。”小蔡写完歪歪扭扭的字抬起头看着我。
我问:“如果哥哥也在你们家交一个月的伙食费,你能不能给哥哥的碗也写一下名字啊?”
“好啊,现在就给你写。”小蔡风一样地跑进去,又风一样地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碗。
因为小蔡,我成了他家的订餐顾客。
包月每餐一个炒荤菜,三块;如果一荤一素,五块。
如果不是包月的顾客,一荤一素两个菜要七块。
因为每餐可以节约两块,所以学生带学生,老蔡的小饭馆生意一直挺热闹。
老蔡热情憨厚,小蔡聪明伶俐,相比之下小蔡妈妈略微吝啬刻薄。
说刻薄也是当时的感受,现在想起来,如果那个小饭馆不是因为有了小蔡妈妈,也许倒闭得会更快。
老蔡每次炒菜的时候,都会有学生站在旁边等自己的菜出锅,所以老蔡每次放荤菜的时候,学生伢子们就会在旁边喊:“老板,多放一点儿喽,不要那么小气嘛。”每次有人这么一说,老蔡就尴尬地笑一笑,顺手多抓一把肉放进去。
这时小蔡妈妈就会很生气地冲过来,对老蔡说:“你疯了啊,一个菜才三块钱,又要肉又要油又是免费米饭又要交房租,你这么搞我们还要不要做生意了?!”
小蔡妈妈发飙的时候,学生们就赶紧一吐舌头做个鬼脸纷纷溜走,留下老蔡一个人很无助地被小蔡妈妈劈头盖脸骂一顿。我也听见过老蔡的辩解:“好啦,以后我们的女儿如果在外地上学,要炒个菜的话,有老板这么对她,我们也放心对不对。”
“对对对!!但我们就一个女儿,现在我们有五十多个包月的顾客,每个月都这样跟你说,我们怎么吃得消!要么就取消包月,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做生意。”小蔡妈妈脑子转得好快。
“小蔡,妈妈平时是不是很凶啊?”我偷偷逗小蔡。
“不是啊,妈妈凶是有原因的。”小蔡急着辩解,我看小蔡妈妈走过来了,赶紧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吃饭。
常有同学不能按时交包月的餐费,他们总会偷偷地跟老蔡求情,递上一支烟,什么都好解决。但自从被小蔡妈妈发现两次之后,她就气哼哼地在大大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本店小本经营,恕不赊账!
黑板出来之后,赊账的人果然少了。我跟老蔡说:“老板娘真是厉害,把问题放在面上解决,你看,果然没人赊账了吧。”老蔡呵呵地笑笑,说:“她就是会做生意。”
有一次,连着几天吃饭的时候,有两个男学生总要剩一些菜拿一次性饭盒打包,然后再装一大盒免费米饭,估计是害怕小蔡妈妈看见,所以总是等她出去结账的时候再赶紧打包米饭。连着一个星期,还是被小蔡妈妈撞见了,她问怎么要打包那么多米饭,两个男同学很没底气地说晚上可以当夜宵吃。小蔡妈妈脸一横,让他俩坐下,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已经连着一个星期都剩菜带米饭回去了,我只是假装看不见而已。”
男同学脸红了,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一刻,我特想站起来帮他们把钱给付了,但因为刚实习工作,来回车费、房租、餐费,开销不小,剩余的零花钱根本为零,尚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但我还是竖着耳朵听,一旦小蔡妈妈不允许他们再带米饭回去的话,我就说从我的包月里扣。
那边的男同学很沉默,小蔡妈妈也一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问:“那个小赵呢?以前都是你们仨一起来吃饭,现在怎么只剩你们俩了?”
两个男同学面面相觑,不知道她问这个问题的目的。
“你们说,你们每天打包剩菜回去,是不是给小赵吃的?”小蔡妈妈问。
“啊,我们,不是,是夜宵。嗯,那个,是的。”语无伦次中,男同学承认了是给小赵同学带饭。
“之前他不是包月吗?为什么这个星期不来了,需要你们带呢?”
“那个……哎……”两个男同学对视一下,道出实情,“小赵爸爸打工摔伤了,这个月家里没有给他寄生活费,他本来想跟你说一下先赊一段时间的账,等家里周转过来,再补上。但黑板上,这不是写着吗……”说着,他们指了指黑板上的“小本经营恕不赊账”。“三个人来吃两个人的菜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商量出这个办法。对不起啊。”
小蔡妈妈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两个男同学:
“你让小赵明天来,告诉他可以赊账,别吃剩菜。”
“啊,真的啊,太好了,谢谢啊,谢谢小蔡妈妈,谢谢老蔡。”
隔着一小段距离,我都能听出男同学语气中因为感激而有些颤抖的声音。
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小蔡妈妈,一个人坐在柜台前面无表情地数着钱,似乎是在思考明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似乎不想被别人看出她的难处。
第二天再去吃晚饭的时候,两位男同学已经变成了三位,估计有一位就是昨天说的小赵同学。我看了看,黑板依然立在最显眼的位置,但似乎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黑板上依然大大地写着“本店小本经营,恕不赊账”,然而在右下角的位置多了一行小小的字,“如有问题,可找老板娘”。
不知怎的,我笑了起来,整个人暖暖的,昏黄的灯光果然是容易让人觉得温暖。
再看小蔡妈妈,觉得她并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冷漠和刻薄了。
等到隔壁桌男孩要走的时候,小蔡妈妈对小赵说:“那个小赵,你明天把你的学生证给我复印一下,这样的话,大家都放心。”
小赵本来如释重负的脸瞬间尴尬起来,红着脸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说:“好的好的,应该的应该的,谢谢老板娘。”
听到这句话,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虽然感觉不好,仔细想想好像也能接受,这种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不爽。不爽不是指愤怒,也不是指心甘情愿,总归是那种心不甘情不愿但又必须接受的事情,大概都可统称为不爽。
对于这件事我不爽了一小段时间,但后来居然想通了,也理解了。
那时我已经从实习工转成了正式工,但因为身体原因,决定辞职准备考研。把当月工资取出来交了接下来的房租,买了考研的书,经济状况惨淡,杂志发表文章的稿费又没收到,我也面临着要交餐费的问题了。跟爸爸打了一通长电话,爸爸问东问西,我都说很好,全是自己的选择,让他和妈妈不用担心。
挂了电话,忍不住一个人靠在椅子上默默流了一会儿眼泪,大学毕业,二十好几的我再要生活费实在说不出口。
想了很久,决定去找小蔡妈妈赊账。为了让她放心,我准备了身份证,以前的工作证,甚至还带着自己发表的文章以证明不久之后我就会有稿费。那一刻,我特别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但凡一个希望讲究诚信的人,都不会去等别人要求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们早就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让对方减少不必要的担心。
我找到小蔡妈妈,还没有说出长篇大论的腹稿,她立刻就说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就好。
大学生的证件里都会写哪个大学哪个专业,我毕业之后就用回了老家的身份证,并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我想再给她一些东西来证明,小蔡妈妈说不必了。我说:“你找不到我怎么办?”她说:“我干吗要找你?”
考研那段时间吃饭,小蔡总是隔三差五给我端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或紫菜蛋汤或丝瓜肉末汤。我说自己没点这个汤,小蔡说:“别人点了,爸爸水放多了,一个大碗装不了,多出来的就给你了。”
现在想起这些细节,还是觉得很感动,那时只是很木讷地“哦”了一声,权当自己明白了。其实内心是感激的,只是表达不出来,缺乏自信的自己,总不能很饱满很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想起来,那时唯一能表达感谢之情的做法,恐怕就是在老蔡给我炒菜的时候,我从不说:老蔡,给我多放一些肉。
不为难别人,也是一种示好。那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考研结束,我又立刻找了一份工作,等着三月出分数线。老蔡、小蔡妈也会问我成绩,我说还没公布,他们问感觉如何,我说应该考得不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过线。老蔡说:“如果你考到北京,那就不能继续来我家吃饭了啊。”小蔡很失落地问我:“哥哥,你要走了啊?”小蔡妈妈抓着老蔡就是一顿说:“人家考到北京是本事,凭什么让人在你这里吃一辈子饭,除了咱家的人,最好谁也别在这儿吃一辈子,不是好事。五块钱一顿的饭小刘吃了两年,以后就应该吃五十一顿、五百一顿的饭了。人不都是慢慢活得更好的吗?”
老蔡又讪讪地笑,我也不好意思地说:“小蔡妈,不会啦,我就是真的去了北京,回长沙肯定还会来这里吃饭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离分数线公布也越来越近。
一天,同学来找我吃饭,三个人我点了四个菜。四个菜上齐之后,又多了一大碗猪脚汤,又上了一条红烧鱼。这两个菜是大菜,每个菜都要十来块,我从来都不会点的。我着急地问小蔡妈妈:“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啊,吃错了可赔不起。”
小蔡妈妈说:“吃吧,这一天每个人都会加菜,你朋友来了,就给你多加了一个。”
“为什么?”我没懂小蔡妈妈话里的意思。
“今天27号,不是你生日吗?这里过生日的人当天都会加菜的,不只给你加,快吃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话刚问出口,我就想了起来,小蔡妈妈那儿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可身份证复印件不是为了避免我们拖欠餐费吗?谁能想到,小蔡妈妈会把每个人的生日都标记下来。
我叫了几瓶啤酒,喝了几杯有点儿晕,我去敬小蔡妈妈,谢谢她。我这个人喝一杯就上头,一上头就喜欢说心里话,我举着酒杯告诉她一开始我特别讨厌她,觉得她没人情味,后来看见她同意小赵赊账,觉得她还不错。可她又要大家押身份证,又觉得她挺不信任别人的。后来,又有好多好多事,直到今天。
小蔡妈妈听完之后,佯装生气,让我罚酒,等我喝完,她看着我和同学说:“没钱留身份证有什么用,没钱找到你们了,会让你们学生赔钱?收着你们身份证就是觉得你们一个个挺需要人照顾的,一般能把身份证复印件放在我这儿的人,都是老实孩子。”
“哈哈哈,老板娘说我是老实孩子。”我笑着对同学说,其中一个女同学眼眶都红了,我的眼眶也瞬间红了。
一个你以为是陌生人的人,突然用长辈的语气来评价你,回想起这些年,他们对自己的照顾,似乎早就有了家人般的感受。我弯下腰对小蔡说:“谢谢你哦,如果不是当时你答应给哥哥的碗写上名字,哥哥就不会认识你们,也不会来你们家吃饭。”
考研的成绩下来了,英文差了一分,有朋友出主意让我去北京找老师,带着自己发表的小说看看有没有特招的可能性。
我去了北京,特招没有成功,却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是真的要去北京了。临走前,我去老蔡的小饭馆吃了最后一次饭,和他们告别。小蔡哭了,躲在房间不愿意见我。老蔡又开心又失落,小蔡妈妈让老蔡又多给我做了两个菜,说是给我饯行,我没有推脱。小蔡不出来,小蔡妈妈对老蔡说:“死小孩不出来,以后也要学哥哥去北京工作才好。”
吃着饭,小蔡妈妈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还给我,说忘记了,早就应该还我了。我说:“你留着,做个纪念,万一哪天我还要继续赊账呢,哈哈哈。”小蔡妈妈照我脑门儿拍了一下:“别乱说话,你收着吧,我早就背得出你所有的信息了,留着没用。”
一段历史就这么结束了呢。真是好快。
“我走了。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你们的哦。”我挥挥手。
再见,我吃了两年的老蔡小饭馆。再见,那个在我的瓷碗上写名字的小姑娘。再见,特别凶特别计较又特别有人情味的老板娘。谢谢你们给我加的菜。
挥着手,心里想着这些,直到转身不见。
到北京之后工作特别忙,很少有时间回湖南。即使有时间回去,也是直接坐火车回老家郴州,很难在长沙停留。工作到了第三年,我被派到长沙出差录节目,特意抽空回到了当年住的小区,特意带了一些北京的特产去看老蔡全家,心里想着小蔡已经长成大女孩了吧。
到了之后,却发现老蔡的饭馆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服装店。
推开门进去,老板在店里。我说我想找之前店家的老板和老板娘。服装店的老板说他们回老家了。
“不是做得挺好吗?怎么说关就关了?”
老板看看我,笑了,说:“那个店大概关了三年了。那个餐馆早就不赚钱了,他们本来早就打算关店回老家,好像那时有很多孩子交了包月,老板说这些孩子能找到一家便宜的餐馆特别开心。本想能包一个是一个,谁知道那些孩子又到处说这里可以包月,搞得餐馆几乎每个月都赔钱。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商量,那就等当时第一拨包月的孩子大学毕业就收摊。你也是那一拨小孩吗?”
我摇摇头。
我是工作之后再来这里的小孩。
离开老蔡小饭馆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人来人往。
我想,一定会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会过来看一眼。想起那个留着剩菜打包一大盒米饭的自己,想起那个不好意思赊账的自己,想起那个让老板多放一些肉的自己,想起那些难以对亲人开口要生活费的日子,想起那些坐在一个泛着暖色灯光的小饭馆,喝一碗因为老板多放了一些水而变成的汤的日子。
老蔡,谢谢你们哦。
后来
说起来有点儿不争气,到北京头几年吃饭很少请客,后来条件慢慢好起来,开始主动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餐费正好五百块,大家哈哈笑着说好准好准,我突然想起小蔡妈妈说一个人不能总吃五块的饭吧,当有一天一餐五十、一餐五百的时候,就意味着人越来越好了。
回忆突然涌上心头,眼泪就飚了出来。朋友们吓坏了,连说不就是吃了你五百块吗?有必要哭吗?
我连忙摇摇手,咧着嘴笑。没有解释为什么。
每个人也许都有一段被自己标注为灰色的日子,在那样的日子里,一点小小的关心都会暖上一整天,一些小小的善意也会让你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很感激老蔡一家人,我也常常想起“放水太多,所以才给你”的一碗西红柿鸡蛋汤,这不是谎言,这是善意,我相信这样的善意一定打动了很多像我当年一样年轻的孩子,这样的善意让我们带着感恩前进,让我们比别人更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小幸福,也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学着老蔡的样子,撒一些善意的谎,把这份雪中送炭的温暖,送给更多的人。
“火车外面好美,我们下去看看吧。”
“如果你不好好待在火车上,怎么能看见这么多的美景?”
时间会任性地为回忆涂上色彩。
就好像明明是五颜六色的回忆,沉淀、加工、过滤,
就只剩下了白色。
米白的墙,雪白的云,纯白的衬衫和t恤,
乳白的下水管道,灰白的远方……
记忆一旦凝固住了某个时间点,
美好的,就呈现出一片泾渭分明的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