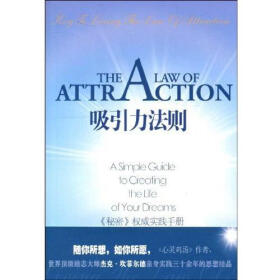代价
“为了适应社会,为了迎战时间,我们投身于一种职业,为之哭为之笑,有人风生水起,有人怀才不遇。我们会放弃一些梦,也懂得了有些梦根本不会实现,那些深夜的痛哭以及离乡背井的挣扎,都是必须付出的青春的代价。”
你还记得吗
一
和小曦哥再见,是在六年之后。
他听说我在厦门见了我们之前共同的领导张老头,也听说我远远地看到张老头便眼含热泪去拥抱。
他带着一股极浓的醋味在微信里问我:那你想见我不?那你看见我会哭不?
六年前,张老头从我的领导岗位离职回福建生小孩,顺便创业。
小曦哥跟着他一同回了福建,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年前小曦哥又独自一人去了上海创业,所以他和张老头,我都有六年未见了。
我看见微信上那个问句,想了想,权当安慰他:我也很想见你,我见到你也一定会忍不住哭起来吧。
他立刻回复说:那好,那我们下周就见一下吧?
小曦哥是我进入传媒行业的第一位领导,也是我大学时同学院的师哥。
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听说有个师哥很出色,长得帅,打篮球棒,是湖南广电最年轻的节目制片人……没想到进入电视台之后,居然被分配到了他的节目组——筹备一档互动类型的闯关答题类节目。
大概的意思就是观众来参与民生新闻的答题,闯关性质,答得越多,奖金越高。
当他跟所有人形容完这个节目之后,大家都觉得超级棒,拥有全宇宙最有竞争力的几个内核——民生新闻的内容、闯关综艺的刺激、上万奖金的诱惑、普通老百姓的互动……每一个元素都能获得超高的收视率。
我们一群大学生没日没夜地跟着小曦哥筹备节目,奋战了好几个月,录了几期样片都没过关,然后台里正式通知:好了,你们的节目研发资金花没了,你们可以解散了。
这个
“噩耗”是一起入职的同事吃午饭时告诉我的,据说团队的人都要分到台里其他节目去,人人自危。
变更岗位其实无所谓,没日没夜地熬着看不到希望,分去一个固定的节目,好歹不用再用
“临时节目组的编导”的身份来介绍自己了,唯一舍不得的是大家彼此的感情。
刚吃过午饭回到台里,小曦哥找我,平时他不怎么爱搭理我,所以我紧张得要命。
他特别谨慎地说:“我决定带你去台里的娱乐资讯节目《娱乐急先锋》。”
我一惊。
那是娱乐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我们团队不是失败了吗?我都做好了被台里打入冷宫的准备,没想到居然能跟着制片人去最好的节目。我偷偷观察了一眼小曦哥,他很冷静,一副从小被叫惯校草的表情。他说:“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
我人生中很少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这句话,那时我知道,如果有人跟你说了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不把你当其他人,而是自己人。
我是小曦哥的自己人?我很兴奋。但是我去做记者了,那他呢?
小曦哥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接着补充了一句:“哦,我是过去接管这个节目的,嗯,也是制片人。”最后补的那句话,得瑟中满是激动的喜悦。
后面的故事惊心又动魄。
在《娱乐急先锋》的日子,每天上班就等着前一天晚上的收视率报表,高了就兴奋五秒,然后立刻投入到更高收视率的制作中。低了,就转身讨论为什么昨天的内容那么差劲。
那时崔永元老师还未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收视率的恶意。
如果没有小曦哥,我也不会被逼成今天这个我吧。
那时,我负责一个选美节目的宣传,就在娱乐节目中开了个五分钟的小版块,每天介绍一位漂亮的女孩直接进入省内每年最大选美比赛的复赛。这个小版块要自己写流程、自己出镜、自己剪辑、自己配音,然后要赶在每天晚上七点直播的时候把节目送到播出机房。
很多人一听,觉得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工作还不到一年,居然就能应付这种强压力的工作节奏,很厉害。
实际情况是:主持人播报完当日的头条之后,就会说:“好了,今天看看我们的记者刘同究竟又给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美女呢?”这时小曦哥就会头戴耳麦很冷静地说:“他的片子还没有剪完,押后几条新闻再播出。”主持人就特别尴尬地对着镜头说:“啊哈,看来今天的女孩太漂亮了,他正在机房做最后的修改,那我们先看两条别的新闻。”
播出别的新闻之后,整个播出机房就会出现小曦哥的咆哮:“你们赶紧让刘同把带子拿过来!再不过来就开除他!”然后我就拿着带子哒哒哒快速地奔进直播机房。
又有人说:“哇,那也挺不错啊,每一次你都能赶上直播。”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直播节目三十分钟,有时候把所有的备播新闻播完之后只剩五分钟了,我的带子才拿过来。眼看就要到节目结束时间了,小曦哥心急火燎地问:“你这个版块还有多长时间。”我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播完这五分钟,还有八分钟……”
我一直没有被开除,我以为是因为我总能在最后关头交上带子,也以为是因为这个版块极其难做,开除了我没有别人能做。
后来才得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有一次在台里,远远地就听到大领导很大声地在办公室呵斥小曦哥,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做的娱乐节目太差劲,要把我开除。
我站在门口不小心听到的时候觉得人生即将全黑了,这时听到小曦哥很认真地说:“这个刘同吧,他大四的时候写过一本小说,十五万字的小说,连写了一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果他都做不好娱乐节目,我觉得其他人也很难做好了。”
我红着眼睛悄悄地离开,那一刻我暗自心想,如果再做不好,就太对不起他对我的信任了。
可第二天一醒来,节目的各种毛病依旧存在,点一点,一个都没有少,个个在那里虎视眈眈。
每次节目播出,小曦哥听见我肤浅的配音说着“这个女孩多美多美”的时候,他都会很生气地吼道:“你当我和观众瞎了吗?”
就在我觉得小曦哥要被我彻底整崩溃的时候,半夜十二点下班的我约见了第二天的拍摄女主角,我先彻底崩溃了。
报名的观众形容女孩长得像玉兰油广告的女主角,而我到了现场,见到了真人,我在心里骂了自己十分钟。现在想起来,这么做特别以貌取人,但那时心里唯一的关注点是:第二天的工作我该怎么交待!!!
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拍摄,临时根本找不到替换的拍摄对象。我坐在那儿,眼神无助地看着女孩,心中绝望地想着,自己将如何被小曦哥放弃。
第二天直播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地拿着节目播出了。
小曦哥眉头皱了起来,说:“今天这个选手如果观众还觉得不够美的话,你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今天这个到底怎样?”
我想了想回答:“你看看观众怎么说的吧。”
电视里,熙熙攘攘的商业步行街,配音简单介绍了一下女主角,然后拿出了一块题板,上面写着:鼻子像刘嘉玲,眼睛像梁咏琪,嘴巴像舒淇,脸型像郑秀文……
接下来所有的镜头都是在女主角的肩膀位置拍摄,一个一个见路人,让他们给选手的五官投票。
小曦哥一开始觉得蛮有意思的,自行脑补了一个刘亦菲的画面。然后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画面里全是路人们的嘴在喋喋不休地对着女选手进行评价。小曦哥眉头又开始紧锁:“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看她的脸?!!”
我说:“快了快了,马上统计数字就出来了。”
题板上出现了多少人投鼻子,多少人投眼睛,多少人投嘴唇……
整个版块时长五分钟,到四分五十秒的时候,配音说:“好的,既然大家评价那么高,我们来看看女孩究竟长得怎样!!!”
一个镜头摇过去,女主角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还没有看清她的脸,配音就出来说:“谢谢大家,明天再见。”
直播室空气凝固了,主持人也凝固了,大家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什么,观众们应该在家里砸电视机吧。小曦哥咬牙切齿地几次想说话,最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我想,他应该看出来我尽力了。
第二天,收视率出来,那个五分钟版块本地收视率破了五,创了一个小新高。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低调。悄悄地进了办公室,准备悄悄地离开。
他看到我,叫住我,说了一句:“节目很烂,想法很好。”
我一时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既然想法很好,为什么节目很烂?又或者为什么节目很烂,想法会好呢?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做法挺过分的,如果换在今天,可能有更妥当的不伤害当事人的方式。之后,我明白了小曦哥那句话,抛开选题本身的质量,节目其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思路做,只要你有你的逻辑,大家就能看得下去。
印象中,我在小曦哥身边好像一直扮演着“讨债鬼”的角色。
又有一次,选美大赛进入了二十强的总决选,二十位女孩的照片挂在巨大的户外广告牌上。我为了测验哪一位女孩有夺冠的可能性,于是在广告牌底下随机采访路过的行人。
也许是当时缺乏经验,每当行人表扬过某个编号的佳丽之后,年轻气盛的我就会把自己当成评委,吐槽该佳丽。比如:“你不知道吧,她笑起来,牙齿很不整齐”、“半身照确实还行,人只有一米五”、“她有男朋友了,而且谈了很多年了”。
要命的是,我又赶在了直播时送播出带,小曦哥没时间审核,直接将节目播出了。
可想而知,每一秒都是在扇做选美活动同事的耳光,每一句点评都是在拆台里的架子。节目刚播完,台领导就冲下来发飙。作为一个能为下属扛事的领导,他只能硬着头皮跟领导说:“我们是觉得,说一些大家听不见的声音,不要老说谁好看谁好看,用这样的方式,有可能观众更想看呢,比如故意说一个姑娘一米五,大家可能就想看她决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一米五。”
小曦哥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我冷不丁绊个跟头,又因为我在背后被人捅一刀。眼看着,当年那个校草渐渐地一岁一枯很难荣。
再后来,我的身体出了些小问题,将近半个后脑勺的头发都掉光了,于是选择了辞职。等到身体好起来,又不好意思再回到小曦哥身边,就去了以前同时段的兄弟节目。小曦哥觉得我是个“叛徒”,从那以后,我们两三年没有联系。
二
再和小曦哥走近是我来了北京之后。
那时公司要制作的节目很多,希望能从各个电视台多挖一些人才,我自然就想到了小曦哥。当时小曦哥在湖南正风生水起,带着团队风风火火地制作新选秀节目。我在电话里跟他聊了聊北京的情况,他简单思考了一下,便答应过来看看。
后来我问:“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来北京的?”
他说:“你傻啊,我说我要过来看看的时候,就基本做决定了。”
也是。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一点儿都不抱希望,应该是直接拒绝,根本无须考虑。
我俩在光线共事了大概有三年。
我们都是没什么朋友的人,固定的生活便是工作、家里,工作、家里。小曦哥稍微比我好一些,他的生活是工作、运动、家里,工作、运动、家里。
有时加班到很晚,他会过来聊几句,但也许因为我是他一手带起来的电视新人,我们聊天也不会太深入,彼此内心总是隐约有些隔阂。
大概是我心里认为他是我的老师,不敢和他成为朋友。而他也觉得我还是小孩,不知道如何走进一个小孩的世界吧。
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公司不同节目的制片人。公司内部各个节目常常会相互比较,这样一来,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微妙了。
同样的嘉宾,我们两个节目都要请,如果都来或都不来,还好。最怕对方选择性地上节目,让我俩总会有些尴尬。
不知不觉中,我和他的师徒关系越来越淡,朋友关系也是,更多的反而是同事之间的竞争关系了。
很长一段时间,远远看着小曦哥和他的团队,我都绕道躲开。
每次遇见,小曦哥都会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的访谈又要请什么幺蛾子博收视率了?”然后他团队的小孩们就会哈哈哈地一起笑起来。
一方面他是我师傅,也是我兄长,我只能笑着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另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去看我的节目,所以干脆躲开。
那种感觉很怪。并不是不喜欢这个人,而是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有压力。
从湖南来北京的时候,小曦哥有一个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劝了她很久,终于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北京。
但有一天我得知小曦哥和女友分手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潜意识里我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小曦哥的感情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他还在办公室,我走过去,说了句:“你和她分手了吗?”小曦哥抬起头,眼睛里都是血丝,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就是个灾星,我一定会被你害死。当初直播节目,几次差点儿出播出事故,现在听你的来了北京,老婆没了,我‘家破人亡’,你要对我负责。”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一起哈哈哈,互相拍着肩膀,大笑起来。
这两个在北京没什么朋友,却希望能独自闯出一方天地的人,因为一件落魄的事,突然拉近了距离。
后来的后来,就如前文写的一样,他和张老头回福建创业,我们鲜有联系。
微信流行之后,我们有了彼此的号码。很少聊天,不是因为没话说,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偶尔会给我点赞,都是我发运动或跑完步的内容。他说:“小子,不错哦,下次一起约着跑马拉松。”
直到六年后,我因为出差来到了厦门,和张老头见面,才知道后来为什么他们创业到一半解散了,也知道小曦哥为什么去了上海。
三
大概三年前的一天,张老头工作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一群人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张老头的脑血管里长了一个瘤。
医生看了之后说只能再活三个月。小曦哥每天陪着张老头,创业的公司也无心再管。
张老头说:“如果人的命真是如此的话,那就信命。”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一定会用福建普通话补充一句说:“我人仄么好,怎么可棱得仄总病。”
张老头不允许小曦哥跟我们透露他的病情。
一方面帮不到忙,另一方面担心打扰彼此的生活。
后来复查的结果出来,瘤是良性的。
医生从鼻腔进入进行手术,很成功。所以我才能在六年之后再见到张老头。
张老头感叹说:“差点儿命都没了,就想着别再拼了,认认真真过自己的生活,那时把公司解散,几个人凑在一起,分了些钱,讨论了每个人未来的发展,小团体就这么散伙了。”
他说得云淡风轻,我哭得一塌糊涂。
张老头安慰我:“别哭啦,一切都仄么好。”
我带着哭腔说:“如果以后你再生病,无论什么病,都要告诉我。”
张老头嘿嘿地笑,也许他在心里狠狠地抽了我一记耳光,这说的是什么话呢。
我想表达的是,对于一个很重要的人,无论如何,哪怕帮不到任何忙,都要知道他的消息,并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小曦哥说周末飞到厦门来,让我和张老头做好准备。
互相通微信、打电话,约好地点见面,紧张得就像要见网友。
远远地看见他戴着棒球帽,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变了些什么。
慢慢地迎上去,本以为自己依然会感动,可心里似乎堵着,什么情感都释放不出来。
我们撞了撞肩,互相抱了抱,就当这六年的未见一笔勾销。居然没有一点儿眼泪,这太不符合剧情,我俩都很尴尬。
几个人坐在当地的小馆子里,我和小曦哥都没怎么看对方。张老头发现了,就问:“你俩怎么了?在我面前总问对方的消息,见面之后怎么又不看对方呢?”
我嘿嘿地笑,小曦哥也是。
我们打开一瓶酒,各自倒了一满杯,什么话都不说,直接干了。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只是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只想赶紧喝醉、掏掏心窝。
他和我一样,起了几个头儿,好像都不对,只能举起酒杯两个人再干一杯。
一杯一杯下肚,小曦哥的脸开始泛红。
他决定要说些什么,我放下杯子,终于敢正视他了。
他比以前胖了一些,也有可能是壮了。
他认真说的第一段话是:“刘同,你给张总寄了一本书,让我转交的,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记得。”
他接着说:“你只寄了一本给他,你并没有寄给我。”
……气氛瞬间僵到冰点。
幸好我们都喝了酒,我想起了不给他寄书的原因——以前每次提到我的作品时,小曦哥总是会评价:“刘同的书写的都是些啥,我根本看不懂。我真是不能理解他的读者,一定很需要耐性吧。”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接着说:“哈哈哈,是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所以这才是我很感谢他们的原因吧。”
我本想立刻说明为什么会害怕给他寄书,又突然想起十几年前进入湖南台的时候,台领导认为我很糟糕要把我开除,小曦哥说的那段话:“这个刘同吧,他大四的时候写过一本小说,十五万字的小说,连写了一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果他都做不好娱乐节目,我觉得其他人也很难做好了。”
我突然就明白了眼前这个兄长。
他总是在我背后维护我的尊严,却又总是当着我的面开一些他认为无伤大雅的玩笑。
他接着说:“这一晃好多年,看到你今天的样子,我觉得一切真的很好啊。你还记得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下班之后带你们去ktv喝酒吗?整个团队,放开了喝。那时你年纪最小,大家喝开心了,就让你跳个舞。你二话不说,把外套一脱,就走到房间中间跳起来。”
哈哈哈,我记起来了。
那时大家都很开心,好像如果我能够真的跳起舞,同事们就会更开心。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欢快地在ktv跳了起来。
头一两次,跳了十几秒后,自己就笑场了。小曦哥会很严肃地说:“你笑场是你没有自信,你坚持跳完,哪怕跳得不好,大家也会尊重你,因为你很投入。”
鬼知道那个时候,一个全湖南广电最年轻的娱乐节目制片人,为何要跟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娱乐新闻记者,在一个所有人喝到烂醉的ktv里,聊一个关于如何跳舞才能获得尊重的问题。
不明白,那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
他说了,很认真。
我听了,也很认真。
以至于后来有段时间,我天天在家里对着镜子跳舞。
扒了一些快歌的舞蹈动作,练习了全套。我知道我未来在舞蹈界不会有什么发展,我只是希望以后小曦哥再让我跳舞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失望。
后来,我果然没让他失望。
到了今天,每年公司要开年会,同事们总是想让我扮演各种造型,我总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答应出演。
这些
“豁得出去”的精神,都来源于在长沙ktv喝醉之后的一次谈话。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小曦哥喝了酒之后,反复用这句话开头。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乘张总的车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五点钟出发的,等刘德华演唱会快结束了才到。”
“那你记得吗?那天在车上,我们俩吵了三个小时的架,而且话说得很难听,另外一位同事坐在前面被我们吓得全身发抖。”
“哈哈哈。”是我。
“你还记得吗?张总刚来的时候,你来找我,很神秘地跟我说,要来一个新的领导,要联合我一起把新领导干掉。”
“哈哈哈。”又是我。
“你还记不记得,张老头连着半年穿同一件外套,没办法我们就陪他去买了两件替换的。有一天,他穿了一件特别潮的衣服来公司,外面是网眼格子,泛着蓝光,商标印在背后,特别好看。后来发现是张总把我们给他买的衣服穿反了。”
“哈哈哈。”还是我。
“那你还记得吗?”轮到我了。
“有一次在张总家开会,我和你意见不合,吵得很凶,你站起来拿起凳子就来砸我。张总那时才八十四斤啊,他居然冲出来救我……”轮到张老头哈哈哈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那时我要做一场陕西卫视的演唱会,要找本土艺人演唱歌曲。你给我推荐了一个新人,说这个新人特别厉害,演了电影《投名状》,你说他是除了刘德华李连杰金城武之外的男四号,然后我就无比相信你。后来节目录完,要跟电视台一一汇报艺人的情况,同事看完了整部《投名状》,看见李连杰死的时候,这个人出来了两秒,就再也不见了。你那次害死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敏的情况你知道吗?”小敏是小曦哥来北京前准备结婚却最后分手的女朋友。
小曦哥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嫁到国外去了,自己在负责一个服装品牌。她和我妈关系很好,每次她和现任吵架还会跟我妈抱怨。她现在挺好的,起码比跟着我好。”
我突然就想起多年前,他哭丧着脸对我说:“你就是个灾星,我一定会被你害死。当初直播节目,几次差点儿出播出事故,现在听你的来了北京,老婆没了,我‘家破人亡’,你要对我负责。”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瓶又一瓶,带着一些醉意,却又不想结束。
吃完晚饭,又找了个酒吧,去完酒吧又换了夜宵大排档,一直聊到夜里三点。
张老头不能喝酒,只能听,就一直陪着我们坐到三点。
好多事我都忘记了,可是他还一直记得。
有些朋友你多年未见,你以为你只是失去了一个朋友,其实你是失去了很多的自己,他们带着很多对你的回忆、你的生活轨迹,听他们说说过去,你才更清楚,为何你成为今天的你。
小曦哥第二天晚上的飞机,我下午去送他,找了一个机场边的咖啡厅。
坐在那儿,两个人又开始尴尬,好像又回到了昨天刚见面的状态。我说:“要不,咱们趁你上飞机前再喝几杯吧。”
他说:“好的。”
蓄水池里是水。
蓄水池里是回忆。
满了,就让它流进下水道。
腾出空间来盛新的回忆。
或者,一直留在那儿,与水龙头两两相望。
直到蒸发看不见,直到生锈打不开。
后来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见一些贵人。
给你机会,带你成长,无论你犯了怎样的错误,他都会尽力帮你去解决。
小曦哥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带着我入行,给我机会,容忍我很多错误,又被我带入了北漂生活,帮我记住了很多我遗忘的往事。
那个我曾经听说很厉害的师哥,那个会打篮球、很帅、我很崇拜的制片人,十几年后和我坐在厦门机场旁边的咖啡厅里,我们干了两杯酒,续上了以前的回忆。
我知道我们不会再失去联系,哪怕我俩这一辈子都是这种只有喝了几杯酒才说得出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