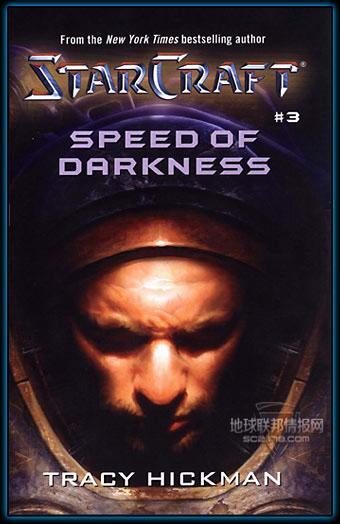“为什么?为什么?”
推瑟尔无助地来回看着时间计量表与这个时空技师,他的眼神和声音里透露出困惑的挫折感。
哈兰抬起头来。他只有一句话要说。“为了诺羽!”
推瑟尔说道,“那个你带来永恒时空的女人?”
哈兰苦笑。
推瑟尔说道,“她和这整件事有什么关连?伟大的时间之父啊,我完全不懂你,孩子。”
“有什么需要懂的吗?”哈兰自怜地说道。“你为什么要故意装傻?我有个女人。我和她在一起感到幸福,她也一样。我们一点都不伤害任何人。她在新的现实里完全不存在。她成为任何人又有什么关系?”
推瑟尔不晓得要如何回应。
哈兰大喊。“但永恒时空有自己的法规,不是吗?我全都知道。私通行为必须经过允许;私通行为必须经过计算;申请私通者要有地位;私通行为是一种狡猾的运作。当这项计划结束之后,你们打算对诺羽作什么?一个将即将失事的火箭座位吗?或是一位计算师社区当中的女主人?我想,现在现在你们根本不会想再作任何安排了。”
他将心中绝望的郁闷倾泄而出,但推瑟尔却立刻奔向通讯面板。它的传讯功能已经恢复了。
计算师对着通讯面板大喊,不容对方有质疑与询问的空间。“这里是推瑟尔。任何人都不准进入这里。没有人能进来,没有人。你听清楚了吗?……好好看守。全时理事会的成员也不准进来。特别是全时理事会的成员。”
他面向哈兰,茫茫然地说道,“他们会执行我的命令,因为我是理事会中最老最资深的委员,而且因为我是脾气古怪的老人。他们会听我的命令,因为我是脾气古怪的老人。”他陷入自己的沈思好一会儿。然后他说道,“你认为我的脾气古怪吗?”他像猴子般地迅速晃着自己的头。
哈兰心想︰时间之父呀,这个人疯了。这件冲击让他疯掉了。
他后退了一步,骇于对方可能的疯狂举动而后退。然后他很快地稳住自己。就算这个人疯了,但他还是个虚弱的老人,更用不着说,这种疯狂的情况很快就会结束。
很快?为什么不是立刻结束?究竟是什么延迟了永恒时空的终结?
推瑟尔以谄媚的语气说道(他的手中没有香烟;也没有试着去抽取一只),“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我的脾气古怪吗?我想是的。太古怪了,所以你不想回答。如果你认为我是个朋友,而不是满脑子胡思乱想,行为完全无法预料的古怪老头,那你早该开诚布公地和我讲出你心中的疑惑。但你显然不这样作。”
哈兰皱起眉头。原来对方以为哈兰疯了。原来如此!他生气地说道,“我的行为是正确的。我的神志很正常。”
推瑟尔说道,“我告诉过你,那个女孩很安全,你知道的。”
“我在不久之前傻傻地相信了你。现在,我再不会愚蠢地相信,理事会竟会公正对待一个时空技师。”
“谁告诉你理事会知道这件事?”
“芬吉晓得,而且他也向理事会作过报告了。”
“你又是如何得知芬吉的报告?”
“我用神经鞭威胁芬吉,让他吐露出这一切。”
“就是这同一把神经鞭吗?”推瑟尔指着计数器上那已被熔掉的握把。
“是的。”
“忙碌的鞭子。”然后,他的语气变得严厉,“你知道为什么芬吉不自行处理,而将这件事通报到理事会来呢?”
“因为他恨我,他想让我失去所有的地位。他也想要诺羽。”
推瑟尔说道,“你太天真了!如果他真想要那个女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安排妥当。一个时空技师根本无法违抗他的意图。那个人恨的是我我我我,孩子。”(没有香烟。一向烟不离手的他,目前的模样看来有些不太自然。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斑驳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你?”
“这还牵涉到所谓的理事会政治生态,孩子。不是每一个计算师都可以进入理事会。芬吉想要这个职位。芬吉是个有野心的人,而且极端渴望这个位置。我阻挡他进入理事会,因为我认为他的个性并不恰当。时间之父啊,在接到报告之前,我从未料到我对他的判断居然如此正确……听好,孩子。他晓得你是我的手下。他见到我将担任观察师的你带走,并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时空技师;他见到你一直帮我工作。他要如何才能反将我一军,摧毁我的影响力呢?只要他能证明,我宠爱的时空技师竟然犯下违抗永恒时空的重罪时,他就能够顺势打击我。那将逼使我自全时理事会中辞职,而你认为,接下来的递补者将会是谁?”
他将手指习惯性地移到唇边,却因指间的空无一物而感到茫然。
哈兰心想︰他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过心里却一点也平静不下来。他办不到。但是,现在现在一直净扯这些无聊的事作什么?永恒时空即将就要结束了。
不过他随即感到一阵苦恼︰为什么还没结束?为什么?推瑟尔说道,“前一阵子,当我同意让你到芬吉那里出任务时,我早就怀疑会有危险。不过玛兰松的回忆录的确说到,你在最后一个月曾由于不知名的原因而离开。很幸运地,芬吉的确拙劣地扮演好这个角色。”
“什么样的拙劣角色?”哈兰无力地问道。他并不真的关心这回事,但推瑟尔不断地讲着,让他觉得配合对方的言谈,比关上自己的耳朵要来得容易。
推瑟尔说道,“芬吉送来这份报告的标题是︰《关于时空技师安德鲁.哈兰违反专业的行为》。
你在里头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忠实的时空组员,冷静,公正,毫不偏颇。他想让理事会自行判断,然后让他们愤怒的矛头指向我。对他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他并不晓得你真正的重要性。只要是任何和你有关的报告,都将二话不说地转送到我的手上来,除非和玛兰松计划有关,否则你的事情绝不可能带到委员会上来公开讨论。”
“你从未和我提过这点。”
“我能怎么办?我担心让你知道过多内幕,可能会危害到我们手头上的计划。我曾给了你很多次机会,让你把你的问题带来给我。”
很多次机会?哈兰毫不相信而扭曲嘴形,但随后,他想到推瑟尔在通讯面板的疲惫脸孔,问着哈兰是否有话要对他讲。那是昨天的事。仅仅是昨天的事。”
哈兰摇着头,不过脸却转向另一旁。
推瑟尔柔和地说道,“我收到报告,马上就知道他处心积虑地想要激怒你,逼得你作出——某些轻率不当的举动。”
哈兰看着他。“你也知道这回事?”
“你吃惊吗?我认识芬吉很久了。我很早之前就晓得他的个性。我是个很老的家伙了,孩子。
我当然非常清楚。不过,一个计算师还是可以使用其它方式来检查。我们有些东西是从一般时间内所剔除的工具,而且不会公开摆在永恒时空的博物馆内,只有委员会的成员才知道这些管制物品的存在。”
于是哈兰想到,那些管制品当中也包括100,000世纪所放置的时间障碍。
“从他的报告与我的认知,我很容易就推算出事情的发生经过。”
哈兰回想起多年前,他和芬吉刚开始相处的那些日子。当时推瑟尔应该就曾在芬吉面前,对他这年轻的观察师表现出反常的兴趣。芬吉当然不会晓得玛兰松计划,必然认定推瑟尔对他另有阴谋。“你有没有见过资深计算师推瑟尔?”他回忆起芬吉曾这么样地问过他,哈兰甚至可以精确地记得对方不安的语气。早在那个时候,芬吉一定会怀疑哈兰是推瑟尔派来卧底的间谍。于是他的敌意和恨意早在当时便已萌生。
推瑟尔继续说着,“要是你来找我——”
“来找你你你你?”哈兰大喊。“那么委员会的其他人怎么办?”
“别理其他人,只有我知道。”
“你没告诉其他人?”哈兰语带嘲讽。
“我没说过。”
哈兰心中感到一阵燥热。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彷彿都能令他窒息。愚蠢与无聊的唠叨!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永恒时空还没结束?为什么这里所依存的现实现在依然能够保持?时间之父啊……究竟哪里出了错究竟哪里出了错?
推瑟尔说道,“你不相信我?”
哈兰大喊,“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他们跑来看我,不是吗?就在那次早餐会报里?如果没见过芬吉的报告,那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想过来看看,我这个违反永恒时空法律的怪家伙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只不过他们还得再等个一天。再过一天,计划结束,明天他们就可以向我进行制裁。” 落霞文学网
“我的孩子,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想要看你,仅仅因为他们也是人。理事会的委员也是一般人。因为根据玛兰松回忆录的记载,他们不该出现在搭乘时空壶作时间之旅的场景中。
正由于回忆录中从未提及,于是他们也无法直接与库柏交谈。但他们还是有好奇心。时间之父呀,孩子,难道你看不出他们的好奇心吗?你是在这项计划中,他们那些人唯一能够接近的相关人士,所以他们全都跑过来盯着你看。”
“我不相信。”
“这是真的。”
哈兰说道,“是吗?在我们用餐中,申纳委员谈到一个人见到他自己的诡论。他显然知道我进入482世纪的非法之旅,我那回差点真的碰见我自己。那是他嘲讽我的方式,将他的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上。”
推瑟尔说道,“申纳?你担心申纳知道你的事?你晓得他为何有那般可悲的外貌吗?他的故乡时间是803世纪,当时的文化是在所有历史上,人类外形最不能符合一切美感的年代。
他们在青少年之后,便要除去身上的一切毛发。
“你知道这对人类连续性的意义为何吗?当然你会知道。这种奇特的外形,将他们与他们的祖先以及后裔全都区隔开来。从803世纪召募而来的时空组员自然相同,他们与我们的外貌差异太大,因此他们在永恒时空里的成员很少。申纳是里头唯一一个能坐上理事会委员座位的人。
“你晓得这会怎么影响他?当然你会晓得他心中充满着不安全感。你能够想象,一个理事会的委员居然是如此不安的人吗?申纳必须静静地在会议上听着别人谈论,将他故乡体毛去除习惯给消除掉的讨论。消除了这种现实,他将会成为所有人类世代中具有这种外貌特征的极少数份子。而且这项变革行动,将来的确非常可能发生。
“于是他在哲学中找到心里的避风港。藉由交谈的领导权,以不合常理的骇世观点,来为他的外在表征作一种补偿。他的『一个人遇见自己』的吊诡就是个例子。我告诉过你,他用这点来预测玛兰松计划的失败,这是由于他想藉此嘲讽理事会,而不是针对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推瑟尔愈说火气愈大。在他言谈中所扬起的愤怒,一时之间似乎让他忘了身处何方,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他转过身去,出现了哈兰非常熟悉的伶俐动作。他让一只香烟从他的袖子口袋自动滑出,流畅地点燃了香烟。
但他很快地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看着时空技师,将话题带回哈兰在此前的最后一句话,彷彿突然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他说道,“什么意思,你说你差点碰见你自己?”
哈兰简短地回答,“你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
他们之间维持了一阵沈默,这也正好让彼此的火气逐渐降温下来。
推瑟尔说道,“是这样吗?要是你真的碰见你自己呢?”
“我没有。”
推瑟尔不理会他的回答。“总是会发生随机的空间空间。在无穷尽的现实中,并没有所谓的决定性可言。假设在玛兰松的现实中,在前一道时间循环的圆——”
“那道圆会无限地轮回吗?”哈兰问道。
“你认为只会循环两次吗?你认为『二』会是个神秘数字吗?这是个在有限物理时间之内的无限循环。就像你可以一直不停地重用笔画出一个圆的圆周,但却只围住一个有限的面积。
在前一个圆的循环之中,你并未遇见自己。这一次的循环,统计上的变易让你能够遇见自己。
现实必须自行改变,以防止你和你自己的相遇,因此在这新的现实之中,库柏并未被你送回24世纪,不过——”
哈兰高声说道,“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你想说什么?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别烦我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我要告诉你,你做错了。我还要让你了解,你做错了什么。”
“我没错。就算我真的错了,事情也早就结束了!”
“还没结束。再听我说几句。”推瑟尔耐着性子,极力地安抚对方。“你会拥有那个女孩。我保证过。我现在还是向你作同样的保证。她一点都不会受到伤害。你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向你保证。”
哈兰看着他说道,“已经太晚了。你的保证又有什么用?”
“还不晚。情势还能修补。只要有你的帮助,我们还能够成功。我必须靠你的帮助。所以,您必须了解你做错了。我试着要向你解释,你必须要弥补你所做的错误。”
哈兰舔着干燥的嘴唇,心里想道︰他真的真的疯了。他无法接受事实——此外,理事会知道这项计划的失败吗?可能吗?可能吗?情况有可能反转过来吗?莫非时间能够暂时中止或反转吗?他说道,“你将我锁在控制室里,让我在里头完全无能为力,一直要待到事情结束。”
“你说过你担心自己会出差错;这会让你无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是我对你的一种威胁手段。”
“我只把它解读成字面上的意义。原谅我。我需要你的帮忙。”
又来到这项结论。哈兰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他疯了吗?哈兰疯了吗?在这种情况下,疯狂还有任何意义吗?任何事还有任何意义吗?理事会需要他的帮助。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答应他任何的要求。诺羽。计算师的职位。不答应又能如何?但假如他提供协助并修补成功之后,他们又将对他如何?他不愿意再次受到愚弄了。
“不!”他回答。
“你会拥有诺羽。”
“你的意思是,当危机解除之后,理事会还同意破坏永恒时空的法律吗?我才不信。”他心中的理智告诉他,这场危机根本不可能解决。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理事会绝对不会知道这回事。”
“你自己你自己愿意破坏规定吗?你本人就是个标准的永恒组员。一当危机解除,你将遵守规矩行事。你不可能违背这一切。”
推瑟尔的双颊涨红。在他老迈的脸上,原有的精明与力量此时全部枯竭,留下来的只剩下怪异的哀伤。
“我会遵守自己的话,违反所有的规定,”推瑟尔说道,“为了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原因。我不清楚永恒时空在消失之前,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几个月。但为了让你相信我,我已经用了这么多时间,所以我不在乎再耗点时间,告诉你真正的原因。你可以好好地听我说吗?拜托。”
哈兰有些迟疑。然后,他已笃定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挽回这一切,于是他无奈地说道,“说吧。”
我听别人说(推瑟尔开始自述)我生下来就相当老成。我听别人说,我从长牙就开始使用微型复杂计算器。我听别人说,我睡觉时会将手放在睡衣特别缝制的手持式计算机上不断地敲动。我听别人说,我的大脑是由许多力场继电器的电路并联而成,我血液中的血球是一个个悬浮的微型时空分析表。
所有这些故事最后都传到我的耳里,而我想我该为此感到飘飘然。或许我自己也该相信真有这回事。一个老人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听来非常愚蠢,但那至少可以让日子过得轻松快活些。
你很难相信吗?我居然还会希望让日子过得轻松快活?但这就是我,资深计算师推瑟尔,全时理事会里的资深委员。
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抽烟的原因。想不到吧?我一定会有原因才这样作,你该知道的。实值上说来,永恒时空是个不吸烟的社会,而大部分一般时间中社会也是如此。我常常想到这种解释,这是我对永恒时空表达叛逆的一种方式。用这种行为,来代替另一件失败的严重叛逆……
不,没关系。掉个几滴眼泪不会让我更难受,而那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了,相信我。我已经很久不再想这件事了。那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回忆。
当然,事情和女人有关,就跟你一样。不是巧合。如果你停下来好好想想,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一个永恒组员,必须将自己埋首在一大群多孔箔片所构成的报表堆里头工作,所以必须出卖自己的幸福家庭生活,以防止受到私人情绪的影响。这是永恒时空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预防措施的原因之一。明显地,在某些时候,这也同样让某些永恒组员狡黠地去拼命钻漏洞。
我回想到我的女人。或许,我这样作看来很傻。在那段物理时间内,我已经记不起其它的事物。我的旧同僚现在都已成了记录册当中的名字;我当时所主导过的变革——除了一项之外——对我而言都仅仅算是储存在复杂计算器存储器中的字符罢了。然而,我还是清清楚楚地记着她。或许,你能体会这种感觉。
我按部就班地提出申请,让她成为我的情妇;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我升等成为见习计算师,于是她就派属给了我。她是这个世纪的女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575世纪。当然,我直到任务指派之后才看到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女孩。她的外表算不上漂亮,但那个时候,我虽然年轻(是的,我也曾经年轻过,别理那堆谣言)却也称不上英俊。我们的个性相合,她和我,如果我是个一般时间中的男人,我一定很乐意让她成为我的妻子。我这样和她谈过很多次。我相信这样说会令她感到高兴。我晓得这是事实。即使是拥有情妇或是通过计算之后的允许,很少永恒组员能像我这样幸运。
在那现实中,她会在年轻即过世,当然,在其它可能的现实中,她的类比人物也不会存在。
刚开始,我以哲学化的立场迎接这种情况。毕竟,仅仅拥有的短暂生命的她,才有可能让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如此才不致于破坏任何一种可能发生的现实。
当时,我为着她的短命而感到高兴。只有在刚开始。当然,只有在一开始。现在我为过去这种想法而深深感到羞耻。
我在时空分析表所容许的时间内,尽可能地与她在一起。我挤出生活中的每一分钟,放弃必要的用餐与睡眠时间,毫不知耻地推托工作。她的可爱,超乎我所能预期的程度,于是我恋爱了。我鲁钝地终于体会这一点。我的爱情经验相当浅薄,而且是透过观察一般时间中的社会,所得来的一种不稳固基础。无论如何,随着我的体认加深,我知道我陷入爱河了。
获得心灵和身体的双重幸福之后,一个人会想要获得更多。想到她即将来临的死亡,让我从原本所感到的方便,转变成为一场恐怖的灾害。我对她作了生命规划。我并未透过生命规划部门而私自进行。我自己作的。我想,这一点或许会令你感到讶异吧。但那不过是项轻微的违纪行为,和我即将犯下的罪孽相比,跟本算不上一回事。
是的,这就是我,拉班.推瑟尔,资深计算师推瑟尔。
有三次,在物理时间计算下的三次,我执行了一些简单的行为,在现实中对她产生了些许修改。当然,我知道这种出于私人动机的变革,是不可能得到理事会所批准的。然而,我认为我对她的死亡有责任,因此我要让她在临死之前的日子里,和我在一起的生活能过得更好。
你会知道,这就是我的动机。
她怀孕了。虽然我应该采取行动,但我没有。我作了她的生命规划,修改了她和我的部分关系,所以我晓得,她会怀孕是高机率的自然结果。你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即使经过审慎的预防,一般时间中的女人,偶尔还是会怀了永恒组员的孩子。这并不是前所未闻的事。然而,由于永恒组员不允许拥有小孩,因此这类怀孕的意外事件,总是能够以毫无痛苦与安全的方式结束。方法实在太多了。
我的生命规划中显示,她将在生产之前就死去,所以我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她很高兴怀有我的孩子,而我也希望她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好心情。所以每当她告诉我,自己感受到肚子里头有个小生命的鼓动,我都是默默微笑地看着她。
但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小孩提早出生。
我早猜到你会露出这种表情。我有小孩。我有一个真正的小孩。或许,你不曾听过任何一位永恒组员说过这句话。这不是操守不良的轻微犯罪。这可是非常严重的违纪重刑;但是,这还算不上什么。
我从未料到这种事。我从未计算过新生儿的出生,或其它相关的问题处理。
我慌张地跑回去,重新检查我的生命规划,发现小孩的出生事件,的确出现在当中的一个替代解里头,不过那是一条我所忽略的极小机率路径分叉。一个专业的生命规划师或许不会将它忽略,但我因过度自信而犯下了这项错误。
我该怎么办?我不能杀死这个孩子。他的母亲只剩下两个星期的生命。我想,就让孩子一直伴随着她。两个星期的幸福日子,并不是价值昂贵的礼物。
一如预期,母亲过世了,连她的去逝时间和方式一如预计。我利用着时空计划书里所容许的全部时间,坐在她的房间里,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事,痛苦万分地看着死亡的降临。在我的臂弯里,我抱着我们两人的孩子。
——是的,我让孩子活下来。你为什么流泪?你也想谴责我吗?你无法体会,一群由原子构成的小生命,静静地躺在你怀抱里的感觉为何。就算谣言是真的,我的神经系统可能是复杂计算器,我的血液可能是时空计划书,但我却完完全全晓得那种感觉。
我让它活了下来。在这件事上,我也犯了罪。我将小孩安置在一个适当的机构,我按着一般时间的顺序,为他支付了必要的费用,并看着这个小男孩长大。
就这样过了两个物理年。我定期地去检查孩子的生命规划(到了这个时刻,我早不把违规犯禁当一回事了),也很高兴地发现到,在那场现实当中看不出任何负面的象征,有害效应的发生机率只有0.0001。孩子开始学习走路,某些词汇的咬字发音不正确。没有人教他要叫我“爸爸”。我不知道育儿中心的一般时间者对我的角色是否存有怀疑。但他们只不过拿了我的钱,没多说一句话。
两年之后,有项对575世纪的现实变革被确立了下来,并由全时理事会决定且交付施行。
我,当时正好被任命为助理计算师,奉派主持了这项工作。这是第一次由我全权负责的变革。
当然,在我感到骄傲的同意,恐惧感也油然而生。我的儿子是这场现实中的入侵者。他在新的现实不该拥有任何的类比人。想到他可能由于这场现实变革而消失无纵,令我感到一阵悲伤。
我全权负责这场变革,我要求自己工作上的完美无缺。这是我的第一次表现。不过,我还是屈从于自己私心的诱惑。我已经背负了多项罪名,已是个毫无罪恶感的惯犯了。我为我自己的儿子在新的现实中,得出了生命规划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廿四小时内,我不眠不休地待在办公室里检查,希望能在这里头发现错误。
结果竟毫无错误。
隔天,我用了第一阶逼近法,完成了一份时空计划书,但我把现实变革的执行时间延后。然后我进入了一般时间,到我儿子出生后的三十多年的未来时间点。
他已经卅四岁,和我自己当时的年纪相同。我向他自我介绍,利用我对他母亲的认识,让他相信我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完全不晓得自己父亲是谁,也完全不记得婴儿时期我对他的每次探访。
他是个航空工程师。575世纪特别擅长于六七项不同的航空运输科技(和当前的现实一样),而我的孩子在他所属的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成功,并满意于自己的生活现况。他和一位迷恋他的女孩结婚,但他们不会拥有孩子。即使在我的孩子并不存在的现实中,那个女孩一辈子也不会结婚。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我知道这样才不会对现实产生严重的危害效应。若非如此,我根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让我的孩子活下来。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而是利用一切,让孩子能在不危害现实的状况下,快乐地过完一生。
我当天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客气地和他交谈,礼貌地微笑。在时空计划书所允许的限期将届,我冷静地和他道别。但在我的外表下,我紧紧地记住他的一举一动,将他的一切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我想在这场现实里多活一秒钟,因为到了明天(我们物理时间的明天),这个现实便不存在了。
我也多么希望能再最后一次去造访我的妻子,在她生活过的那段一般时间内。但我过去已经用光了我能拥有的最后一秒钟。我甚至不敢再进入一般时间去偷偷看她。
我回到了永恒时空,度过了那恐怖的最后一夜,心里头不断悔恨着即将面临的事实。隔天早晨,我递交出我的计算结果,然后变革就在我的建议之下开始执行。
推瑟尔的声音愈来愈低,几乎降成了一道道的耳语。他沈默不语,弯腰坐着,眼睛朝下望着双膝之间的地板,手指不断地紧扣与放离。
哈兰静静地等着老人的下一句话。发现对方陷入长思之后,他清清自己的喉咙。他觉得自己同情这个人,即使他犯下这么多罪行之后,还是对他抱着深深的怜悯同情。他问道,“就这样了?”
推瑟尔低声说道,“不,最悲惨的——最为悲惨的——我孩子的类比依然存在。在新的现实中,他确实存在——他是个从四岁起,下半身便麻痺瘫痪的患者,过了四十二年的卧床生活。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无法为他安排在900世纪所开发出来的神经重建治疗技术,甚至无法安排让他毫无痛苦地提前结束人生。
“新的现实依然存在。我的孩子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纪当中的适当位置。是我我我我让他度过了这样新的人生。是由我的推导与复杂计算器确定了他的新人生,是由我下了命令而造就了这场现实。为了他和他的母亲,我做出数不清的犯罪行为。但最后的结果,即使我完全不理会我对永恒时空的任一信条,对我而言,我的最大罪恶,就是造就出他这样的人生。”
哈兰不晓得该如何回答。
推瑟尔说道,“所以你该知道,为什么我能体会你的事,为什么我会让你拥有那个女孩。你的事并不会危害到永恒时空,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对我罪孽犯行的赎罪。”
于是哈兰相信了他。这么一刻,他全心全意地相信了他!哈兰低着头,握拳击打自己的头部。新的绝望之情又缓缓地布满全身。
他抛弃了永恒时空,失去了诺羽——当他原本有能够同时拯救永恒时空与拥有诺羽的时候,他竟然选择了参孙式的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