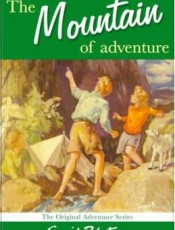野天鹅
弗洛说,要警惕那些白奴贩子。她说他们是这样操作的:一个老女人,像当妈的或者是当外婆的,在你坐公交车或者火车的时候跟你交朋友。她会给你糖果吃,其实那是毒品。很快你就口水横流、神志不清,完全没法为自己说话了。哦,救命啊,女人说,我的女儿(孙女)病倒啦,谁来帮帮我把她抱出去呼吸点清新空气,让她好起来吧。然后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走来,假装是个陌生人,来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在下一站,一起推推搡搡地把你带下火车或者公交车,那就是这个世界见你最后一眼的时候了。他们会把你送到囚禁白奴的地方囚禁你(你已经中了毒,被绑着运到这里,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处于屈辱和绝望之中了,喝醉的男人将你蹂躏个遍,还注入了极可怕的病毒,你的头脑已经被毒品摧毁,你的头发和牙齿都往下掉。三年后你就到了这个境地。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想回家,可能都记不起来家了,要是记得,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所以他们把你扔到街上去。
弗洛拿了十块钱,放进小布袋里,那个小布袋是弗洛给露丝缝的,就缝在露丝的腰带间。另外一件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露丝的钱包会被偷。
小心点啊,弗洛说,看到穿得像牧师的人都留个心眼。他们是最坏的。白奴贩子最爱假装牧师,小偷也是。
露丝说她分不清哪个是假装的哪个不是。
弗洛之前在多伦多工作过。她在联合车站一家咖啡馆工作。就是在那里,她学到了如今知晓的一切。那些时候,她从来没有见过阳光,除非是在她放假的时候。但是她见到了很多别的事。她见过一个男人用刀子划开另外一个男人的肚子,他就拉开他的衬衫,利落地划了一刀,仿佛那是个西瓜不是肚子。那肚子的主人就低头往下看,满脸惊讶,没有时间反抗。弗洛暗示说,在多伦多,这都不算什么。她见过两个坏女人——弗洛管妓女叫“坏女人”,两个词语连起来用,就像羽毛球也叫“坏明顿”(badminton)一样,她们打架了,有个男人对着她们大笑,其他男人也停下来笑,朝她们扔鸡蛋,她们的拳头往对方头发上猛砸一通。最后警察来把她们带走了,带走的时候她们还大吼大叫个不停。
她还见过一个死于痉挛的孩子。他的脸就像墨水一样黑。
“不过我不怕,”露丝挑衅地说,“不是还有警察吗?”
“哦,警察!他是第一个骗你的人!”
她不相信弗洛说的关于性方面的话。想想那些送葬者吧。
一个穿着整洁的小个子秃头男人有时候会到店里来,带着抚慰的神色跟弗洛说话。
“我只要一包糖果。可能几包口香糖就可以了。一两块巧克力棒。能麻烦你帮我包一下吗?”
弗洛用一种嘲讽的礼貌语调告诉他“没问题”。她拿结实的白色纸张把它们包好,像几份礼物似的。他则慢慢挑选,一边哼着歌,聊着天,然后闲站一会儿。他可能会问弗洛感觉怎么样。如果露丝在,也会问露丝感觉怎么样。
“你脸色苍白。年轻女孩们需要点新鲜空气啊。”他会对弗洛说,“你干活太卖力了。你这辈子都在卖力干活呢。”
“咱们下等人就是没法休息啊。”弗洛会同意地说。
他走出去之后,弗洛会匆匆跑到窗户去看。就在那,一辆破旧的黑色灵车,紫色的帘子放下来。
“他今天就会去追她们!”灵车慢慢开走,就像葬礼的速度那样慢慢开走时,弗洛会这么说。
那小个子男人就是个送葬者,不过他已经退休了。那灵车其实也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子接过了送葬的工作,买了一辆新车。于是他就开着这辆旧灵车跑遍乡村,找女人玩。弗洛说。露丝不相信这事。弗洛说他给她们口香糖和糖果。露丝说他很可能是自己吃了呀。弗洛说她见过,她听说过。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会把窗户拉下来,唱歌,唱给自己听,也唱给跟在后面看不见的人们听。
她的眉毛像雪堆
她的喉咙像天鹅
弗洛学着他唱。他会温柔地赶上那些岔道上走着的女人,或者在乡村的十字路口上休息。他会拿出所有的赞美、礼貌,还有巧克力棒,载她们一程。当然,听说每一个被问到的女人都拒绝了他。他从来没有打扰到任何人,只是礼貌地继续开车。他还会光顾别人家里,如果丈夫在家,他就会像平常人一样坐在那里聊天。妻子们说,反正他做过的事情就是这些了,但是弗洛不相信。
“有些女人被带进他的灵车里了,”她说,“有不少。”她喜欢猜测那灵车里面是什么。奢华。
墙壁、屋顶和地板都是奢华的。淡紫色,窗帘的颜色,深色丁香花的颜色。
全都胡说八道,露丝想。谁能相信呢,那个年龄的男人?
露丝要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多伦多了。她之前去过,不过是跟弗洛在一起,远在她父亲去世之前。她们带上了自己的三明治,在火车上的小摊上买了牛奶。是酸的。酸的巧克力牛奶。露丝一直在小口小口地抿,不愿意相信她渴望良久的东西居然如此令她失望。弗洛闻了闻,然后翻遍火车上下,终于找到了那个穿着红色夹克衫的老男人,他没牙,一个托盘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她让他自己喝喝那巧克力牛奶。她让旁边的人闻闻。他只好免费给了她一些姜汁啤酒。还有点热乎。
“我让他知道,”他走了之后,弗洛环顾四周说,“你得让他们知道。”
有个女人表示同意,但是大多数人都望向窗外。露丝喝下了那瓶热乎乎的姜汁啤酒。在火车上,要么是这样,要么就是会发生小摊贩的那件事,要么呢,就是弗洛跟那个表示同意的女人熟络了起来,她们聊到对方来自哪里,为什么去多伦多,还聊到露丝脸色这么差是因为早上便秘,或者是因为喝了点巧克力奶,所以到火车的厕所里吐了。她整天都在害怕多伦多的人们会闻到她大衣上呕吐的味道。
这一次旅途开始前,弗洛对列车员说:“看着点她啊,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然后她环顾四周大笑,表示这只是开开玩笑。再接着她就得下车了。那位列车员好像没什么听笑话的需要,更不把露丝放在心上,也不打算“看着点”什么人。除了检查车票,他也没有跟露丝说过什么。露丝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很快就心情雀跃了,她轻快地把那个倦怠的自己丢掉,就像把一切抛在脑后一样。她对那些市镇的感情渐渐淡去,渐渐感到陌生。一个女人穿着睡衣站在她的后门前,不在乎车上的其他人有没有看见她。他们往南边行进,开出那雪域,迎接一个早春,去看更柔和的风景。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后院里种植桃树。
露丝在脑子里整理她到多伦多的购物清单。首先,买弗洛的东西。她静脉曲张,需要一些特殊的长袜。一种用来黏合壶把手的特殊水泥。还有一整套多米诺骨牌。
她自己想买个手臂和腿用的除毛器,如果可能的话还买一些充气垫,据说可以瘦臀和大腿的充气垫。她觉得西汉拉提的药房里可能是有除毛器的,不过弗洛的朋友在那个店里,她买了染发剂、减肥药和避孕套,那朋友就跟她讲了关于这事的一切。说到充气垫,你可以邮寄,不过得跟邮局的人说明,而且弗洛也认识邮局里的人。露丝还打算买些镯子,还有安哥拉山羊毛衣。她对银镯子和深蓝色的安哥拉山羊毛衣满心期待。她觉得这些服饰可以让她变个人,可以让她变得安详、苗条、头发柔顺、腋下干燥、神采奕奕。
买这些东西的钱,以及这次旅途的钱,是露丝写《明日世界的艺术和科学》这篇论文赢来的奖金。让她吃惊的是,弗洛问她能不能读这篇文章,而她读的时候评价说,他们肯定想过要给露丝颁发一个“吃透词典”奖。然后她不好意思地说:“有意思。”
她会在塞拉·麦肯尼家过夜。塞拉·麦肯尼是她父亲的表亲。她嫁给了一位酒店经理,就觉得在这世间有了地位。然而有一天,酒店经理回到家,坐在餐厅两张椅子的地板上说:“我再也不想离开这个房子了。”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就是决定不再离开这个房子了,他真的没离开过,直到他死去。这让塞拉·麦肯尼感到奇怪又紧张。每到八点她就要锁住房门。她还很小气。晚餐通常是燕麦粥加葡萄干。她的房子漆黑、狭窄,闻起来像个银行。
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上了火车。在布兰特福德,一个男人问,是否介意他坐在她旁边。
“外面比你想象的要冷。”他说。他拿出一份报纸给她看。她说不用,谢谢。
为了不让他感到她粗鲁,她说,外面的确更冷一些。她继续看窗外这个早春的清晨。这里已经看不见雪了。这里的树和灌木丛似乎比家里的要更苍白些。甚至阳光看上去都不一样。就像地中海岸,就像加州山谷,跟家里都不一样。
“窗户可真脏,总觉得他们能打理打理的,”那个男人说,“你常坐火车出门吗?”
她说不是的。
窗外的田地里淌着水。他点了点头,说今年这样的景象很常见。
“下了很大的白雪。”
她注意到他说的是“白雪”,蛮有诗意的说法。家里的人们都会说雪。
“有一天我经历了件不一样的事。我在村外开车。实际上我正开车去看我的一位教民,是个得了心脏毛病的女士——”
她快速地看了看他的领子。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衬衫,打着领带,深蓝色的套装。
“哦,对了,”他说,“我是联合教会的牧师。但是我并不经常穿我的服装。布道的时候才会穿上。我今天休息。
“好了,我刚才说到,我开车经过乡村,看到一些加拿大雁在池塘里,我又看了一眼,跟它们在一起的还有些天鹅。有很大一群天鹅。那景象多美妙啊。它们应该是正在春天的迁徙之中,我想,它们正去往北方。多壮观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露丝没法对这些野天鹅产生什么赞赏之情,因为她害怕这个对话会引向对自然的讨论,然后会说到神,牧师通常会觉得有义务这么做。但是他没有,他说完天鹅就停下来了。
他大概是五六十岁,露丝想。他个头小,精神矍铄,长着一张红润的方脸,他的额头前整齐地梳着灰白头发的清晰波浪。当她意识到他不会提到神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出一些感激来。
她说,那一定是美妙的景象啊。
“那甚至都不算一个真正的池塘,就是那片田地恰好有些水,那有水是全凭运气,就这么淌下来,我也恰好是在那个时候开车经过。就是运气。水是从伊利湖的东部末端下来的,我觉得。但是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看见。”
她的身子往窗户转过去一点,他回去看他的报纸。她一直保持微笑,这样看上去不至于粗鲁,不至于显得她完全拒绝对话。早上的确冷,她从挂钩上取下了自己的大衣。一进火车她就把这大衣挂在火车上,现在她将它盖住了身体,就像盖着条毛毯一样。那牧师坐下来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钱包放在地板上了,给他挪点位置。他将报纸的不同部分分开,慢悠悠地,以一种显摆的姿态摇晃着它,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是牧师看报的方式。他把现在不想看的部分都甩一边去。报纸的一角碰到了她的腿,就在那件大衣的边上。
她想了一会儿,是报纸碰着了她。然后她对自己说:如果碰到她的是手怎么办?这是她能想到的事情。她有的时候会看男人的手,看他们前臂的汗毛,看他们正集中精力看的文件。她会想象一切他们能做的事情。那些愚蠢的男人也不例外。比如那个把面包送到弗洛的店铺的流动销售员。他的举动熟练而自信,面对面包车,他已经练就了一套悠然又警觉的工作方式。但皮带上方的便便大腹让她心生不悦。还有一次她观察学校里的一个法国老师。真的,不是个法国人,他的名字是麦克拉伦,但是露丝觉得教法文已经擦去了他本来的面貌,让他看着就跟法国人一样了。他身手敏捷,面色发黄,有着瘦削的肩膀、钩子鼻和犹豫的眼神。
她看见他在那不紧不慢的欢愉里徜徉,驻守在这自我沉迷之中。她非常希望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关注对象。若是这样,她的心会怦怦作响、心满意足,随后累得损兵折将、偃旗息鼓。
如果是一只手呢?如果它真是一只手可怎么办?她微微转动,尽量往窗户那边靠。她的想象力似乎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现实,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现实。她觉得情形危急。她把注意力放在了那条腿上,放在那条长袜盖住的那小片皮肤上。她简直没法去看。她是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吗?还是没有?她又转了一下身子。她的两腿一直都是,现在也是,紧紧地并拢着。是。那是一只手。那是一只手的压力。
请不要这样。她想这么说。她把那语句在脑子里变了变,想把它们说出来,但是无法送出她的唇间。为什么?是尴尬吗,是害怕别人可能听到吗?他们身边全都是人,座位都是满的。
不仅仅是这样。
她最终还是去看他了,不是抬头去看,而是小心翼翼地扭头去看。他已经斜靠着座椅,闭上了他的眼睛。消失在报纸下面的,是他深蓝色套装的袖子。他已经将报纸重新放好,于是也盖住了露丝的大衣。他的手放在下面,只是放那儿,就像是睡觉的时候伸出去的一样。
现在,露丝可以移一移报纸,把大衣拿走。如果他不是在睡觉的话,他就得把手缩回去了。
如果他在睡觉,那么她可能会小声地说,抱歉,然后把他的手稳稳地放在他自己的膝盖上面。这种明显又无误的解决办法,她并没有想到。于是她又得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她并不欢迎,或者说暂时还不欢迎这位牧师的手。这让她感到不适、愤懑,感到一丝厌恶,感到行动受限,必须小心翼翼。如果他坚持说手没有放在那儿,她也没法坚持说,那手就是放在了那。在忙碌的一天开始前,他躺在那里,带着愉悦而健康的脸庞,看上去毫无恶意、值得信任,这叫她怎么说他对此事有责任呢?如果她父亲还活着,他会比她父亲年纪更大,这是个受人尊敬的男人,他会欣赏自然,会对野天鹅感到欣喜。如果她真的说了请不要这样,她敢肯定他不会在意这句话,就像忽略她身上的某种笨拙和无礼一样。
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好奇。比任何情欲更加不离不弃、更加专横跋扈。这是一种自我的情欲,它会让你后退、等待,等待太久,几乎赌上一切,就为了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几英里的旅途上,那只手开始了它最优雅、最怯懦的按压和勘探。没睡着。如果说他睡着了,他的手并没有。她的的确确感觉到了恶心。她感到一阵眩晕的、错乱的作呕。她想到的是肉体:层叠的肉体、粉红的口鼻、肥大的舌头、粗钝的手指,都在慢慢地、悄悄地、懒懒地摩挲着,寻着安慰。她想象着发情的猫儿就着木围栏的顶部来回摩擦,哀嚎着表达那痛苦的埋怨。那样的痛痒、推撞、挤压,如此可怜、如此幼稚。吸水的纸巾、兴奋的内膜、煎熬的神经、羞辱的味道;耻。
一切都开始了。他的手,她不想去拉他的手,她也不想挤回去,他那顽固的、坚韧的手,毕竟能让植物沙沙作响,能让小溪淙淙流淌,也能唤醒偷欢的极乐世界。
无论如何,她还是不要。她还是不要这样。拿开吧,她对着窗外说。停下来吧,求你了,她对着树桩和谷仓说。那手移上了她的腿,越过了她的长袜,来到她露出的皮肤上,然后又移得更高,在她的吊带之下,到达了她的内裤和肚子下方的那个部分。她的两腿仍然是合上的,并拢在一起。两腿如果并在一起,她就可以认为清白,就可以什么都不承认了。她还觉得自己能放下这心思一会儿。没什么事要发生,没什么事情。她的双腿永远不会张开。
但是它们张开了。张开了。火车经过登达斯的尼亚加拉悬崖,他们低头去看那冰河期前的山谷,看小山银灰的碎石,当他们的火车滑过安大略湖的岸边时,她会缓慢地、安静地、确定地做出这个宣告的姿态,这举动或许令人失望,正如会让那只手的主人感到满足一样。他没有睁开眼,他的脸没有转动,但是他的手指不会犹豫,有力而谨慎地工作着。侵略吧,欢迎吧,阳光照耀在湖面上,尽情铺洒;伯灵顿那几英里开外的果园,光秃秃的,骚动着呀。
这是耻辱,这是乞讨。但又有什么害处呢,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会这样对自己说,有什么害处呢,当我们驾着贪婪的冰凉波浪时,越坏越好呢,我们得到了贪婪的许可。陌生人的手、根类蔬菜、简陋的厨房工具,人们常拿这些来讲笑话;这些看上去人畜无害的东西争先恐后地向世界宣告它的无辜,有油嘴滑舌的,有忠厚老实的。她小心呼吸着。她无法相信这些。
她是受害者,也是同谋者,火车经过格拉斯科的果酱工厂,经过炼油厂那巨大的如脉搏般跳动的输油管。他们滑进了郊区,在那儿,床单和毛巾用来擦去那些私密的污渍,它们垂落在晾衣绳上,色眯眯的;同样是在那儿,连孩子们都在校园里玩着下流的游戏,停在铁道十字路口的司机一定正在欢快地将拇指插进那握起的双手里。看看现在,景色这么好,动作却这么怪。展览中心的大门和高塔出现在眼前,着了色的穹顶和柱子在她眼皮下玫瑰色的天空中惊异地飘浮着。你甚至可以看到一群鸟儿——一群野天鹅,在这大大的穹顶之下觉醒、爆破,然后向天空进发。
她咬了咬舌边。很快,列车员就穿过火车,叫醒旅客,警告他们该到现实中来了。
在漆黑的车站下,联合教会牧师清醒过来,睁开眼睛,把报纸叠起来,然后问要不要帮忙弄她的大衣。他自我满足于这殷勤,又显得满不在乎。不用,露丝说,她舌头还痛着。他在她前头,快速地走出了火车。她在车站也没看见他。此生再没见过他。但是关于他的记忆总是出现,可以这么说,年复一年,在这之后,这记忆随时可以溜进一个关键的瞬间,干扰到丈夫或者情人出现的时刻。是什么让他出现的?她不明白。他的率真、他的傲慢,他面容的毫不英俊,甚至是他那普普通通的成人男子模样?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她看到他甚至都没她想象的高,他的脸红扑扑地发着光,这是他的糙、他的任性和他的孩子气。
他是一个牧师,真的吗,还是他自己编的?弗洛提到过那些不是牧师却穿得像牧师的人。她说的可不是穿得不像牧师,但其实真的是牧师的人啊。或者说,更奇怪的那种,不是真的牧师,假装是,但穿得跟他们不是似的。她亲身遇到的那件事,是一件讨厌的事。露丝穿过联合车站,感觉到那装着十块钱的小袋子在她身上摩擦着,她知道她整天都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她的皮肤会在这个提示器上如此摩擦着。
即便如此,她脑子里也一直想着弗洛传递的信息。因为她在联合车站,她记得弗洛在这里的咖啡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叫梅维斯的女孩也在这里工作,在礼品店里。梅维斯的眼皮上有个疣子,似乎要变成麦粒肿的样子,不过最后没有,这疣子不见了。可能她做了去除手术,弗洛没问。去除它之后,她的样子很好看。她长得很像那个时候的一个电影女明星。那个明星叫弗兰西斯·法默。
弗兰西斯·法默。露丝从来没有听说过她。
是这名字。梅维斯去买了一顶大大的帽子,垂在她一只眼睛前,还有一条完全用蕾丝做成的连衣裙。她周末的时候去乔治亚湾,去那儿的一个旅游胜地。她是用弗洛伦斯·法默这个名字订票的。其实她想告诉大家,她是另外一个人,是弗兰西斯·法默,她管自己叫弗洛伦斯是因为她在度假,不想被人认出来。她有一个黑色的珍珠母做的烟斗。她会被抓起来的,弗洛说。就凭这胆儿。
露丝差点就要去那礼品店,去看梅维斯是不是仍然在那儿,看自己能不能认出她来。她想,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会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去挑战它,去摆脱它,独自踏上那段荒谬的旅程,以脱胎换骨的身份。